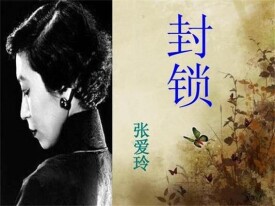共找到9條詞條名為封鎖的結果 展開
封鎖
張愛玲創作短篇小說
《封鎖》是現代作家張愛玲創作的短篇小說,發表於1943年11月上海《天地》雜誌第二期,收入1944年8月上海雜誌社《傳奇》,現收錄於小說集《傾城之戀》。
該小說講述了因日軍搜查,平時正常行駛的電車要封鎖,呂宗楨為躲避討厭的親戚,而與陌生女人吳翠遠調情的故事。作者通過兩個都市人封鎖時期邂逅的寓言,在亂世中察覺都市人的隔膜和孤獨,在她筆下的男性世界對女性進行內省式解剖。
戰時的上海,封鎖鈴聲一響,電車成為一個相對靜止、封閉的空間。華茂銀行的會計師呂宗楨為了躲避討厭的年輕人——太太姨表妹的兒子,坐到素不相識的吳翠遠旁邊,並不得不做出調情的樣子。這個場景讓那年輕人知趣走開,但呂宗楨又不得不延續與翠遠的搭訕。面對一個男人突如其來的言行,翠遠自然是震驚而排斥的。呂宗楨閑聊的話題與情緒,在吳翠遠的意料之中,無非是公事的繁忙、生活的疲憊,對家庭尤其是對妻子的厭倦。在呂宗楨一步步的攻陷下,吳翠遠內心的快樂戰勝了原來的審慎與拒絕。亂世的封閉電車上,吳翠遠逐漸忘記現實的寡淡,伸手觸摸一個理想而浪漫的夢境。最後,“封鎖”解除,人們的行動都回歸正常,呂宗楨也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吳翠遠這才明白,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
民國32年(1943年)的上海已經成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孤島”,人們戰戰兢兢地生存著。上海由於高度殖民化,中西文化混雜,出現了電車、咖啡館、電影院等現代事物。因而封鎖的底色就是戰爭背景和都市文明。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每天正常行駛的電車才會封鎖,因而才有封鎖后的故事。戰爭時期,《封鎖》這類反映男女基本愛情慾求的題材並不是敏感題材,因而得以發表。
吳翠遠:大學的英文助教。她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女孩,頭髮、長相、裝束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樣。在家裡她是一個好女兒,在學校她是一個好學生。大學畢了業,翠遠就在母校服務,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但翠遠不快樂,她已厭倦了這一角色,卻無法改變自己。這種模稜兩可的生命狀態,使得翠遠面臨了生活與情感的尷尬:既不甘心像貧寒人家的女孩匆匆嫁人,又無法自我奮鬥到出人頭地,而她的相貌也不足以使她遭遇一場傳奇的愛情。
呂宗楨:庸碌、老實的銀行會計師。他遵太太旨意,穿著西裝戴著玳瑁邊眼鏡,外表和觀念都已被社會的秩序束縛得齊齊整整,沒有空虛,即使是在“封鎖”剛剛來臨時,坐在電車上的他,仍然能立即從手中的報紙上找到填滿可怕空虛的辦法。
主題思想
張愛玲在《封鎖》中通過男性和女性的互看達到了對女性自身的內省,表現了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這些女性雖是時代的新女性,她們生活在都市中,吃穿用度都跟新潮流,很多受過大學教育,但她們無意識中還是被中國傳統的男權思想所掌控,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男性的附庸。呂宗楨對吳翠遠的看是從單純男性感官上出發。在談及終身大事時,他還自私地推卸責任既說要替她安排好,又想重蹈三妻四妾的舊路讓她做外室。而吳翠遠作為一名受過大學教育,並在大學工作的現代女性,一方面她討厭父母渴望她找個有錢女婿趕緊嫁掉的虛偽和庸俗。另一方面,她不自主地受家人想法控制,想嫁給呂宗楨這個有婦之夫氣一氣他們。“擱淺”的電車讓荒誕的偶然調情成為愛情,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張愛玲對愛情的真實性的消解和嘲諷,也可以看到張愛玲對女性精神深入的解剖和自省意識,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意義和象徵意義。
藝術特色
象徵隱喻
《封鎖》以封鎖為名,它所說的是個因時空切斷而成的故事。在這個封鎖的特殊時空里,兩個主人公的特殊愛情隨之上演。他們的境遇與時空的相互映證,使這一時空呈現出濃厚的象徵意味。在這個人工造成的時空中,作者開始了特別的敘事。平日內心深處忍耐的事在這寂靜里膨脹了,於是被“封鎖”在電車中的已婚男人呂宗楨和未婚小姐吳翠遠,暫時背離日常的生活軌道,暫時“封鎖”對親人的情感。他們從心不在焉的聊天逐步發展到隱秘的情感交流,甚至談婚論嫁。隨著封鎖的結束,兩個在封鎖期間互訴衷腸的戀人轉眼間形同陌路。這一特殊的時空恰是一個整體的象徵:人生的真實處境是一種無形的封鎖,它封鎖了人的真實情感,而現實生活中的有形封鎖卻為情感封鎖創造了一個真空環境。在這個超越時空的時刻,它使人性解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無形的封鎖,為封鎖的情感提供一個還原的機會。
意象
小說中,電車屬於一個公共場域,文明、敞開是其特徵,因封鎖而成為一片安全區域后,它被賦予了一種隱秘性的質素,那就是對於人物內心的揭露。諸如小說男主人公宗楨對翠遠傾訴自己婚姻的不幸、妻子學歷低且不體諒、工作的不如意等。由此可知,電車作為上海城市的縮影,作家再現了上海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荒涼之景。這座孤島如烏殼蟲的巢穴一般,而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就是一個個烏殼蟲,淹沒在雜碎的日常瑣事中,來不及思考,也不願承受因思考而帶來的痛楚。當整座城市的人都互相不信任、不同情、不關懷的時候,這座城市就生成了荒涼的底蘊,生活其中的人必然變得冷漠自私。
敘事
從故事的開端:電車被“封鎖”引起了生活常態的斷裂,到故事的發展:車上人的不同表現,再到故事的高潮:呂、吳二人的交談及心理活動,最後到故事的結局“封鎖”開放,大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常態。這種“常態-非常態-常態”的情節轉換過程,構成了一個圓形的敘事結構。
張愛玲在小說中運用了無焦點的第三人稱敘事,全知全能的視角洞悉所有的環境、事件以及人物的心理,並將它們呈現給讀者。作者一會兒成了宗楨:“在宗楨的眼中,她的臉像一朵淡淡幾筆的白描牡丹花,額角上兩三根吹亂的短髮便是風中的花蕊”。一會兒又成了翠遠:“翠遠皮包里有紅鉛筆,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來。她的電話號碼,他理該記得”。不斷變換的視角,使讀者得以明白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
張愛玲善用比喻和擬物擬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說中已經見識過了。譬如這篇《封鎖》,將電車軌喻作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覺讓人發瘋,然而開電車的人卻“不發瘋”。又說,“這龐大的城市在陽光里盹著了,重重地把頭擱在人們的肩上,口涎順著人們的衣服緩緩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壓住了每一個人。”“生命像聖經”,因為翻譯來翻譯去的緣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無法想出這樣誇張卻又無比貼切的句子。
小說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寫世態的,在寂靜中突然唱起歌來的乞丐,百無聊耐的電車司機,公事房裡一同回來的幾個人,一對長得頗像兄妹的夫婦(妻子總擔心那條薰魚會弄髒丈夫的西褲),手裡搓核桃的老頭子,孜孜修改骨骼圖的醫科學生……
電車的外部是死靜的,電車內卻有些嘈雜,就在這既死靜又嘈雜的背景下,徐徐展開了呂宗楨和吳翠遠的、短暫的“愛情故事”。
相信大多數男女都幻想過艷遇,在行進的列車或汽車中,和一個陌生的異性在封閉的空間里,幾乎零距離地靠在一起。但事實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著機會與一個年齡相仿,長相也還過得去的異性坐在一起的機率幾近於零。萬一真遇到這樣一個機會,你也很可能因為膽怯而與他/她失之交臂。也許你只是滿足於裸露的手臂有意無意間短暫的相觸,佯睡時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腦袋。你可能在心裡猜測了種種有關他/她背景的可能,卻連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一個年過三十的男人曾這樣向大家描述他的“艷遇”:“她坐在我旁邊,我們一共呆了六個鐘頭。我一輩子也沒有和一個美女挨得這麼近,我們距離不超過十厘米地廝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產生了錯覺,以為這種狀態將會永遠保持下去。所以臨下車的時候她頭也不回地絕塵而去,實在令我有些傷心欲絕。”但我想這是大多數“艷遇”的必然結局。
說回正題。張愛玲為呂宗楨和吳翠遠設計了一切造成他們“艷遇”的前提,先是“封鎖”,然後是呂宗楨的姨侄(呂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話,不得已坐到了吳翠遠的身邊)。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統統叫作偶然,就象“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緣,“封鎖”又為什麼不能“促成”一段艷遇?張愛玲大概是習慣了要把人們擱在極端的情況下來考驗他們的人性。
如果換個環境,吳翠遠很明顯不是呂宗楨喜歡的類型,因為在呂看來,“她的整個的人像擠出來的牙膏,沒有款式。”而呂宗楨也不是英俊小生,何況還有家室。無論如何這兩人也不會走到一起。在近處找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被越來越多的人勉強擠在了一起。而突然間與陌生人如此親近的場面,很容易激發起男女之間別樣而微妙的情感。往遠處找原因,則可以歸咎於呂宗楨對他太太的憎恨——她總是要求西裝筆挺的他在麵食攤上買包子回家,而她那該死的侄子,已經開始打他十三歲女兒的主意。至於翠遠,則是帶了反叛的情緒,誰叫家裡人總叫她找個有錢的女婿,所以這次偏找個沒錢還有太太的男人賭氣做小給家裡看。
諸如此類的艷遇,並不具有我們期待中的香艷。別說男女主人公都貌不驚人,連調情所用的方式也極其俗套——
“翠遠暗道:‘來了!他太太一點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別的女人的同情。’宗楨遲疑了一會,方才吞吞吐吐,萬分為難地說道:“我太太——一點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這樣極其勉強與不和諧的調情,居然也因為某種不能預測的因素,被迫發展到了令雙方談婚論嫁的地步。呂宗楨欲擒故縱地說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話,而翠遠居然假戲真做地哭起來,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幾乎“把眼淚唾到他臉上”。結局自然更為不堪,呂宗楨閃入人群,當作一切沒有發生過,翠遠終於醒悟過來,“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我看《生活在別處》的時候,覺得昆德拉是殘酷的,因為他給浪漫的詩人小伙雅羅米爾,安排了一個極其醜陋的紅髮姑娘作為他的性伴侶。現在看《封鎖》,覺得張愛玲更殘酷,她先叫人們生出一點希望,覺得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轉眼間就將它象肥皂泡一樣捅破,空留給人一個尷尬的念想。
作家蔣方舟:《封鎖》當中,我非常神奇地感受到小說是關於時間的魔法,因為小說里的封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但是張愛玲當時寫車裡的人、車外的人,包括車裡面的男人,甚至還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艷遇。當時我看這個小說的時候就覺得,小說真的是時間的一個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