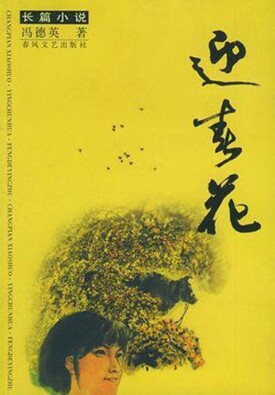共找到10條詞條名為迎春花的結果 展開
迎春花
馮德英所著小說
《迎春花》,是馮德英“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系列小說之一,是繼《苦菜花》之後的又一力作。
1959年9月1日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
本書出版50多年來翻譯成10種文字暢銷1000萬冊。
多災多難的文學經典,此次拂去歷史塵垢,重現原貌,原汁,原味《迎春花》。小說描寫了山東半島地區人民鬥爭的生活情景,謳歌膠東人民革命戰爭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堅貞不逾的熱烈情懷,絕對不容錯過。
寫在新版“三花”前面 主要人物表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
《苦菜花》是我的處女作,是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不僅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為了這本書的創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醞釀、構思、練習鑽研,到一九五五年寫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軍隊的緊張工作的業餘時間和節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給北京解放軍總政文化部,並附上一封給該部陳沂部長的信,大意說,我是某部隊的一個十九歲的排級幹部,共青團員,利用工作之餘,寫了一本小說稿子,自知水平很低,達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關部門的指教……“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很快來了信,稱我寄去的稿子和給陳沂部長的信,都已轉到他們手裡,他們會及時把意見告訴我……然而,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這怪不得編輯部,因為反胡風引發的肅反運動,文藝界是重災區,一切正常業務工作都要停下來為政治運動讓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編輯部的熱情支持幫助下,在大張旗鼓的反右運動前夕,很順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於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軍文藝社自己編輯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由天津畫家張德育作的彩色插圖,而之前該社的“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輯的書,都是交給地方的有關出版社出版;之後,為了慶祝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從全國範圍精選一批文學作品出版,我趁機對入選的《苦菜花》作了些枝節性的修飾,並把應約發表過的一篇談該書創作情況的文章,收作後記,此後出版的各種本子,包括外文譯本,都是根據這個版本來的,直到“文革”之前,沒有再修訂過。“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迫於當時的形勢,再版時又做了些刪節;隨著政治形勢的進一步好轉,很快又恢復了原來的版本,也就是讀者現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寫作過程則簡單多了,在處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熱情的推動下,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我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於一九五九年春寫完四十五萬字的小說《迎春花》,上海的文學雜誌《收穫》一期全文登出,新華書店征訂要一百萬冊,因為紙張緊缺,暫時只能印出四十萬冊。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該書在男女兩性關係的描寫上,有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失於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評者更進一步認為,《苦菜花》也存在這個問題,值得作者警惕!於是,我在有關領導的指示下,對《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減少了五萬字,於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結束不久重新出書時,又對這方面的描寫進行了一次修刪,以期男女關係的描述更“乾淨”;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原來就不贊成這種“乾淨”的同志,反對修改,編輯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這個版本重新出書,我也同意了。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廣大讀者有自己的鑒別能力,孰對孰非,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當然,事情的進展並不總是天遂入願一帆風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藝革命旗手”江青點名批評寫了壞小說《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無情地批判,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調和論、革命戰爭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的三株大毒草,成為禁書。
世上的事有時是很難預測安危福禍的。《山菊花》的出世過程,即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脫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這長達十八年的時間裡,安危多舛,可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依”,充滿戲劇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時,曾明言超不過前“兩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單位主管文宣的空軍政治部王靜敏副主任,閱完書稿后,感動得淚下,讚賞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沒有多久,隨著反對國際現代修正主義氣候的升溫,國內的階級鬥爭的氛圍也日益濃烈。編輯們最終得出結論,這樣的稿子現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選擇了寧不出,也不改,書稿擱在那裡。但書雖然沒有出,炮製這株大毒草的罪責卻一點也沒有減輕,將手稿交出去批判,連王靜敏主任也逃脫不了干係。我極感悲慘,《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運,可它倆總是出生了,發行遍及全國,國外也有翻譯,也算風光了好幾年;而這個《山菊花》,還沒見面於世,便被批判鬥爭得體無完膚,連“壽”都沒有,就和它的“兩花”姐姐一起“正寢”了,豈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爆發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從貴陽空軍五七幹校返回北京等待“複查”落實政策的日子裡,單位里的一位秘書同志告訴我,機關堆放雜物的屋子裡,有一包像是稿子的東西,一直沒人問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見到那熟悉的白布舊包裹,我的心顫抖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奪眶而出……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蒼護佑,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謳歌膠東人民革命戰爭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堅貞不渝的熾烈情愛的書稿,竟能在無情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鐵掌中逃生?竟能矇混在亂紙堆里蓋著厚厚的塵埃倖存下來?轉念一想,這部《山菊花》稿子,當初還幸虧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鬥,否則留在我自己家裡,全家被掃地出門去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誰還會顧及帶上這已經惹了禍的“惹禍精”?那樣一來,驚恐萬狀的家人,也會將它付之一炬或扔進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會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東人民出版社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的兩個版本的《山菊花》了。這可真應了那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老話。
每個作家的創作道路是不會完全相同的。這是因為,作者為什麼要寫——創作的動機,寫什麼——創作的題材,怎麼寫——創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閱歷、個性愛好、立場觀點、周圍環境密切相關。而這些方面,很難是人人相同的。
2007年王冀邢執導的24集電視劇《迎春花》
人們習慣於把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統稱為“三花”,認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實並非如此,這三部長篇小說相互之間的人物關係、故事情節,都沒有直接的聯繫和瓜葛,是獨立成書的。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共同點,三部小說都是描寫山東半島膠東地區人民鬥爭生活的,時代的連貫性——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結合緊密,書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來吧!本書為《迎春花》,是馮德英繼《苦菜花》之後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