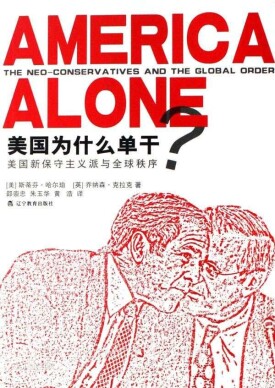新保守主義
新保守主義
新保徠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是政治思想、動向及運動的一種,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是從先前的自由派觀點轉向保守目標和方法的美國意識形態。
在己故總統羅納德·威爾遜·里根及喬治·沃克·布希執政期間,均推崇“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之所以稱之為“新”,是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當時提出這種主義的具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背景者,不少均首度接觸保守主義;第二,新保守主義較為曲解現時的保守社會政治思維,這種主義是從不少二戰後的知識根源中導出,包括文藝批判及社會科學。
保守主義是20世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派的意識形態。70年代以來,隨著西歐福利國家運動和美國“偉大社會”運動受挫,中右勢力赫然崛起,從70年代末開始保守派先後在英、美、西德等西方工業大國上台執政,在法、意、奧、瑞典等國也有相當進展,形成1848年革命以來最強勁的保守主義運動。其意識形態也因此而迅速擴大影響,成為8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義在西方社會淵源深遠,古希臘的柏拉圖、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近代的霍布斯等大思想家均有程度不等的保守色彩。但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政治哲學和政治運動的保守主義,卻遲至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才形成。那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以暴力和恐怖為手段的社會激變,對歐洲以至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衝擊,並引起各種政治力量的不同反應。保守主義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首先奠定其思想基礎的是英國政論家和議會活動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
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后,人民群眾所表現出來的巨大作用,使資產階級內部的一些保守分子產生了很大的擔心和恐懼。伯克於1790年出版了《法國革命感想錄》(也譯為《法國革命論》),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提出了一套系統的保守主義觀點。這被公認為保守主義誕生的標誌。但伯克從未使用過保守主義一詞。保守主義來源於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法國保王派創造的。這個術語迅速為其它反對法國革命的政治集團所採納,美國共和派從1830年開始自命為“保守分子”,英國托利黨也於同年得到“保守黨”的稱號。
首先,保守主義反映一種守舊拒新的社會心理。著名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休·塞西爾說:“謹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種未經自己的經驗測試、也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業已測試並發現是令人滿意的事情。他寧可選擇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東西,也不選擇未經測試的新東西,儘管那種東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這種經驗主義傾向使保守主義一向貶低理論的作用,因而自身也從未形成嚴整統一的學說體系。其哲學基礎是:承認人的本性是惡的,是有缺陷的,必須通過法律和宗教對這些加以限制,否則,人的邪惡本質就會通過戰爭、暴力和掠奪等表現出來。故在哲學上,保守主義深受基督教原罪教義的影響,確認人類本性和理智有難以葯救的缺陷,社會弊病只可減輕而無法根除。因此保守主義總是懷疑政治活動的功能,反對徹底改造社會的任何企圖,特別是未經檢驗的烏托邦理想。節制政治的觀念是它區別於其它政治思潮的分水嶺。自由主義雖然也提倡節制政治,其出發點和目標卻不同,它所鼓吹的人權、進步和理性等抽象概念都是保守主義不能接受的。
其次,保守主義的社會觀是一種“機體論”。在對待社會變革的問題上,保守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有機體,它所依賴的是傳統、習慣、法律和秩序;對社會變革必須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它把人類共同體理解為生物一般的有機組織,其中各局部之間、各局部和整體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賴關係,局部不可離開整體而獨立生存。同時,各局部的地位也不同,如大腦和心臟在人體中的作用就超過手足和毛髮。這種觀念的現實含義是:社會問題是複雜的,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社會的整體或公共利益應高於個人和集團利益,等級和階級差別乃自然秩序所定,因此所以社會成員均應服從命運、各司其職。所以,在處理個人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上,保守主義強調國家和社會對個人的重要性,認為一個人只有成為家庭、集體、國家和社會的一部分,才有存在的意義

弗里德曼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守舊拒新的保守態度主要表現為安於現狀,不願看到任何形式的劇變,無論急速前進還是大步倒退。因此一般說來,保守和反動不宜簡單地等同起來。此外,保守態度也並不意味著其思想內容一成不變。首先,不同時代的社會現狀和傳統大不一樣,如自由放任在19世紀是新生事物,到了20世紀就變為妨礙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傳統,現代自由主義反而呼籲國家干預以對抗威脅個人自由的壟斷組織,因而當代放任主義者不再屬於自由派而屬於保守派。其次,西方保守派是有執政能力的強大政治勢力,他們出於競爭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時常變換政綱,以吸引各階層的廣大選民,與自由派和社會黨人進行競爭。當代保守主義者甚至高唱改革,當然這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以變求保,以溫和改革取代激進改革,或者說對別人的改革進行改革。
以上保守主義的特點只是概而論之,某些保守主義派別和理論家每每表現出更極端的論點和主張,甚至混跡於反動陣營。這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正常現象,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徵和作用。新保守主義最為鮮明的特徵是“反國家主義”即反對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他們對現代自由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進行了猛烈批評,認為政府已經超載,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讓市場經濟自己在那裡運行。實際上,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闡發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原則。

九一一事件
濫觴於美國殖民時期加爾文教義中的“選民”思想也為新保守派繼承。他們對“選民”的闡釋,結合北美大陸的特殊環境,催生了美國具有“領導世界”的使命觀:即美國是上帝選擇的特殊國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命運負有特殊責任。
正是這種理論使一些美國人認為,美國可以為實現使命而不擇手段,主張輸出美式民主、在國際競爭中佔領“道德高地”。新保守派還認為,實力是美國擔當世界領導的先決條件。盟國之所以緊隨,是因為可以搭車;非盟國之所以不敢挑戰,是出於對美國實力的恐懼。對那些不自量力者,美國應靠“拳頭”而不是靠“舌頭”說話。

埃德蒙·伯克

德·梅斯特爾
自伯克之後,保守主義在19世紀發展為三個不同學派。法國的正統主義,也稱拉丁派,屬於保守主義的極右翼。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兩位法國貴族德·梅斯特爾(JosephdeMaistrel753一1821)和德·波納德(LouisdeBonald11753—1840)。他們實際上是封建貴族的代表。這一派發揮伯克的神權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指責1789年大革命毀滅精神生活和社會秩序,造成無政府狀態,並嚴厲批判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利傾向。他們要求恢復革命前“黃金時代”的政治制度,即統一的世界性基督教會和絕對王權相結合的封建專制。正統主義在“神聖同盟”統治歐洲的年代盛極一時,但其專制主義立場完全違背歷史潮流,同時也與溫和派保守黨人不合拍,因而自1848年歐洲革命后便漸趨衷落。不過它在後來的法國保守主義傳統中仍有一定影響,20世紀20和30年代夏爾·莫臘和莫里斯·巴雷斯領導的“法蘭西行動”就是其後繼者。

諾瓦利斯
其主要代表除伯克外,還有威廉·科貝特(1763—1835)、羅伯特·塞西爾·索爾茲伯里侯爵(R·C·Salisbbry1830—1903)、亨利·梅因(H·Main1822—1885)、威廉·萊基(1838—1903)、詹姆斯·斯蒂芬爵士(1829—1894)等。此外,本傑明·孔斯坦(1767—1830)、德·托克維爾(1805—1859)等比較保守的法國自由主義者也與他們有相通之處。這一派的價值觀有強烈的貴族主義色彩,但不像前兩派那樣絕對化,而比較靈活、實際。他們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保守派,主要旗幟為個人自由、法治和議會民主,主張以妥協、溫和的手段調解社會衝突。他們厭惡近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民主,卻又避免直接對抗,並能採取主動行動竭力將其納入自己的軌道,防止其走向極端。本傑明·迪斯雷利(1804—1881)領導的“托利黨民主”運動就是一個突出例證。英國溫和派影響最大、最持久,是早期保守主義的主流。
複雜思潮

威廉·科貝特
第一階段
20世紀初到二戰前後為第一階段。此時西方政治秩序正發生迅速而劇烈的變化,保守派遇到明顯挫折。他們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現是對消逝的舊傳統的悲嘆、對國家干預的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抵觸、對民主運動和革命風潮的恐懼和對強有力的傑出人物即精英人物的強烈呼喚,但沒有形成明確的政治綱領。這一時期主要有兩派人物:一是精英派和專家治國派。以義大利的莫斯卡(G·Mossca1858一1941)和帕累托(V·Pareto1848一1923)為代表的精英派認為,人類社會永遠存在有文化教養的傑出人物和愚昧無知的民眾。學者、政治家、藝術家和企業的管理人物是傑出人物,而保持精英的素質和領導權是拯救西方的惟一途徑。以美國的伯納姆(J·Burnham1905—)和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1908—)為代表的專家治國派則根據現代工業社會的新變化認為,西方各工業國都進入管理社會,出現了新的管理階級和作為社會主體的技術專家,他們是社會的真正領導者,議會民主行將滅亡。二是以英國的保守黨政治家塞西爾為首的保守主義,塞西爾對伯克的保守主義作了新闡發。
第二階段
從二戰前後到70年代初為第二階段,此時保守派處境進一步惡化。這一時期,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盛行時期。與此相應,正是新保守主義潛心研究、醞釀和提出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批判,構建理論體系的時期。當代許多新保守主義者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觀點、嶄露頭角的。由於部分歐洲保守分子曾同情、支持甚至參加法西斯運動,保守派在戰後聲名狼籍,以至於除英國之外的其它歐洲保守主義黨派均被迫改換了招牌。與此同時,福利國家運動橫掃西方世界,保守派為大勢所趨在福利建設方面與申左翼競爭,在理論上主要表現為哈羅德·麥克米倫(1894—1987)的“中間道路”。這種思想現實可行並有所建樹,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卻喪失了獨立價值。在此期間,美國湧現一批以歐文·克里斯托爾和丹尼爾·貝爾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預示著保守主義的復甦。然而其思想並未完全越出“中間道路”的軌範,因而尚不具備改變政局的力量。
第三階段

帕累托

里根
下面的兩個事例清楚地顯示,新保守主義已經在美國政壇得勢。其一,美國總統布希在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講話中說,“你們是我們國家最優秀的一些大腦”,“我的政府錄用了你們當中的二十來個人”;其二,美國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沒有忘記》唱道:你們總說美國人愛到處找岔兒打架,九一一之後我要說,哥兒們,就應該這樣……前者表明,新保守主義已經進入美國的權力中心,後者表明,美國公眾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著新保守主義的思路走。

布希
新保守主義認為,政權性質比任何國際組織和國際安排都重要得多,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過去來自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體制,今天來自“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覺得“恐怖主義”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歡稱“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時期之所以反對跟蘇聯搞緩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專制主義的軟弱和對“反文化”的寬容。九一一事件之後,他們又一再強調,民主國家面對的暴政是各式各樣的,所以“要有憂患意識”,隨時準備回擊惡勢力的挑戰。由此可見,布希的“善與惡的戰爭”和布萊爾的“傳播自由才是對安全最好的保證”,正是新保守主義在最高政治層面的反映。他們厭煩國際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識”,認為捍衛和平與安全的最佳途徑是改變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推進自由民主的傳播。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個大目標上,美歐是一致的,但歐洲人傾向於通過經濟社會的發展去促進,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則主張藉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義總是從民主和專制對立的角度觀察問題。例如人們通常說,聯合國實行的是國際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迄今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民主”,因為專制國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願的。基於這種認識,新保守主義者對聯合國內的投票歷來不以為然。如果有誰批評美國一方面為國內政治中的制衡而驕傲,另一方面卻反對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他們就會以同樣的邏輯斷然反駁:讓誰制衡?讓專制統治者嗎?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還指責歐洲國家姑息專制政權,正在重犯“綏靖”的錯誤。
談起美國及其價值觀,新保守主義者毫不吞吞吐吐。諾曼·波多拉茲說:“美國並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國家,但跟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總的來說一向是副好心腸。”湯娒·多納利聲稱:“美國的價值觀適用於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世俗宗教。美國是運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們舉例說,二戰之後的西歐復興、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平息巴爾幹的戰亂、剷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無一不是在美國主導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沒有美國,誰去處理巴以衝突這個腫瘤,誰去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呢?一副捨我其誰的口氣。
克里斯托認為,“靠國際的標準、法律和談判構築美妙的多邊世界”是極端危險的,美國應當把自己的力量與其世界使命聯繫起來,“要麼美國領導,要麼陷入混亂,世界別無選擇……美國應當干預(國際事務),否則,世界的形勢就會惡化,而且很快。”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例外的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所以應當增強軍力,剷除那些“邪惡政權”,並且警惕任何國家出來與之作對。
新保守主義痛恨專制,但並不是主張遇有專制就動槍動炮,它主張“選擇”。其標準用勞倫斯·卡皮蘭的話來說是兩條:第一,這個專制政權的垮台能夠引起地區規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於推進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那麼,對於不符合這兩條標準的其他專制政權呢?他們準備把道德大旗暫時捲起來,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現實政治”:可能的話“遏制”它們,必要的話拉為盟友。美國在里根時代就是這樣做的,今天則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釋。一個新保守主義者爽快地表示:“我並不一味反對國家利益。”
據報道,《洛杉磯時報》一位記者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書,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猶太裔,所以“內心深處始終縈繞著對大屠殺的記憶”,他們最擔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某一天遭到攻擊而無從還手,從而帶來“文明”世界的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保守主義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

撒切爾
新保守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資產階級思索和解決重大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難兄難弟,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它們都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及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故它們在許多問題上吸收、採納對方的主張十分正常。
新保守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在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中,主要涉及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政策問題,如:如何看待自由市場的競爭和發展?政府要不要干預,如何干預?要不要實行社會福利政策?儘管它們的觀點不同,但本質上又是一致的,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使現代自由主義主張的國有化,實際上是私有制的一種變化而已;無論現代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干預,還是新保守主義主張自由競爭,最終都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它們都不可能、也不會完全否認或者拋棄個人自由。
兩個信條
新保守主義者的抱負主要在國際政治方面。不過,他們既反對老共和黨人的“現實政治”,抱怨他們對外結盟時不問政權性質;又反對民主黨人的傳統國際主義,認為他們想依靠國際組織和經濟發展去推動民主是“天真”,他們看重的是“強力”。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要有兩條:其一,自由民主跟專制水火不容,民主國家應挺身反對暴政;其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義認為,政權性質比任何國際組織和國際安排都重要得多,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過去來自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體制,今天來自“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覺得“恐怖主義”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歡稱“激進的伊斯蘭”)。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時期之所以反對跟蘇聯搞緩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專制主義的軟弱和對“反文化”的寬容。九一一事件之後,他們又一再強調,民主國家面對的暴政是各式各樣的,所以“要有憂患意識”,隨時準備回擊惡勢力的挑戰。由此可見,布希的“善與惡的戰爭”和布萊爾的“傳播自由才是對安全最好的保證”,正是新保守主義在最高政治層面的反映。
“歷史的終結”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義者,他說:“新保守主義者絲毫不想維護現存事物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是建立在等級、傳統和對人類天性的悲觀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厭煩國際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識”,認為捍衛和平與安全的最佳途徑是改變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推進自由民主的傳播。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個大目標上,美歐是一致的,但歐洲人傾向於通過經濟社會的發展去促進,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則主張藉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義總是從民主和專制對立的角度觀察問題。例如人們通常說,聯合國實行的是國際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迄今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民主”,因為專制國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願的。基於這種認識,新保守主義者對聯合國內的投票歷來不以為然。如果有誰批評美國一方面為國內政治中的制衡而驕傲,另一方面卻反對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他們就會以同樣的邏輯斷然反駁:讓誰制衡?讓專制統治者嗎?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還指責歐洲國家姑息專制政權,正在重犯“綏靖”的錯誤。
談起美國及其價值觀,新保守主義者毫不吞吞吐吐。諾曼·波多拉茲說:“美國並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國家,但跟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總的來說一向是副好心腸。”湯娒·多納利聲稱:“美國的價值觀適用於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世俗宗教。美國是運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們舉例說,二戰之後的西歐復興、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來平息巴爾幹的戰亂、剷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無一不是在美國主導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沒有美國,誰去處理巴以衝突這個腫瘤,誰去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呢?一副捨我其誰的口氣。
克里斯托認為,“靠國際的標準、法律和談判構築美妙的多邊世界”是極端危險的,美國應當把自己的力量與其世界使命聯繫起來,“要麼美國領導,要麼陷入混亂,世界別無選擇……美國應當干預(國際事務),否則,世界的形勢就會惡化,而且很快。”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例外的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所以應當增強軍力,剷除那些“邪惡政權”,並且警惕任何國家出來與之作對。
新保守主義痛恨專制,但並不是主張遇有專制就動槍動炮,它主張“選擇”。其標準用勞倫斯·卡皮蘭的話來說是兩條:第一,這個專制政權的垮台能夠引起地區規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於推進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那麼,對於不符合這兩條標準的其他專制政權呢?他們準備把道德大旗暫時捲起來,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現實政治”:可能的話“遏制”它們,必要的話拉為盟友。美國在里根時代就是這樣做的,今天則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釋。一個新保守主義者爽快地表示:“我並不一味反對國家利益。”
據報道,《洛杉磯時報》一位記者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書,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猶太裔,所以“內心深處始終縈繞著對大屠殺的記憶”,他們最擔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某一天遭到攻擊而無從還手,從而帶來“文明”世界的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保守主義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懼”。
兩位鼻祖
新保守主義並非幾個鷹派人物的一時衝動所致,它有其嚴肅的思想理論基礎。據認為,新保守主義有兩位思想鼻祖,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利奧·施特勞斯(1899——1973),軍事思想方面是1997年去世的戰略專家阿伯特·沃爾特泰爾。
施特勞斯出生於德國黑森州一個正統的猶太家庭,三十年代為逃避納粹的迫害而流亡巴黎、倫敦、紐約,戰後定居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二十多年,最有名的著作是《論暴政》。據介紹,施特勞斯畢生研究的是希臘古典哲學及宗教,跟當代並無直接關係,他也沒有關於國際關係的論著,但是他的哲學思想深刻影響了新保守主義者。西方報刊廣泛報道的是他的以下思想:
施特勞斯認為,道德價值具有不變性,存在一種“自然法”,即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有不變的標準,它適用於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但是,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陷入了相對主義,現代化又造成了對道德價值的拋棄和對理性和文明的歐洲價值的拋棄。善惡的相對主義不敢承認歐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優越,導致對暴政束手無策:“當我們被帶到同暴政——一種超過過去最厲害的思想家最大膽的狂想也無法想象的暴政——面對面對峙的境地,我們的政治科學無法識別它。”(《論暴政》)
施特勞斯認為,人類對“完美社會”的嚮往,最終導致了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他親身經歷過軟弱的魏瑪共和國,目睹了納粹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清晰地看到了邪惡的可怕,這些個人經驗深刻地影響了他日後的政治哲學思想。他終生關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這個重大課題,他指出,如果民主政體軟弱,拒絕反對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暴政,就沒有任何站住腳的可能性。他認為,社會制度有好壞之分,政治上的考慮不應當剝奪對一個政權的價值判斷;美國的民主政體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發展而言,人類還沒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個好的制度有權利乃至義務去反對壞的制度,即使要動用武力,“為了使西方民主政體處在安全之中,應當使全球都實現民主。”
施特勞斯哲學思想的傳人、同樣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阿倫·布魯姆猛烈抨擊了西方六十年代的“社會文化革命”,認為它直接導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確”。他指出,在“政治正確”下,似乎任何事物都有價值,各種文化彼此彼此,無所謂優劣,“無論什麼都成了文化,毒品文化、搖滾文化、街頭鬥毆文化,不一而足,不得有任何的歧視。文化的失敗也成了一種文化”。
“政治正確”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蔑視”,某些大學生及教授甚至完全準備接受常常是侵犯自由的非西方文化,而對西方文化持嚴厲的批評態度。布魯姆堅信:“古希臘人實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會是人類所設想的最好的社會。”
阿伯特·沃爾特泰爾是數學家,曾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等大學任教,擔任過里德公司研究員、國防部顧問,是美國核戰略的制定人之一。
他最早對“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戰略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種戰略既不道德(大量殺害平民),又沒有效力,因為任何有理智的國家領導人——至少美國總統——是不會做出會帶來“各自自殺”後果的決定的。他因此提出一個替代戰略——“逐步反應”或曰“逐步升級威懾”,後為美國政府及北約所採納。按照這種戰略思想,要準備打有限戰爭,必要時使用戰術核武器和能夠攻擊敵方軍事設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沃爾特泰爾激烈反對跟蘇聯達成軍備控制協議,認為這將阻礙美國工藝技術的進步。後來,里根總統聽取了他的意見,隨後拋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前幾年,美國朝野激烈批評過去同蘇聯達成的反導條約,最終廢除了它。在這場大辯論中,批評反導條約最激烈的大都是沃爾特泰爾的門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