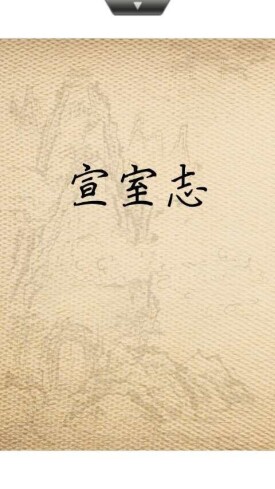宣室志
宣室志
《宣室志》,唐代中國傳奇小說集,共十卷。在《崇文書目》、《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中均有著錄,共11卷。明代抄本、《稗海》本均為10卷,附補遺1卷,110多條。蓋南宋時從《太平廣記》中輯出,《叢書集成》本即用此本排印。今有版張永欽﹑侯志明點校《宣室志獨異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除《補遺》外,尚有輯佚65條,是目前較好的本子。
中唐志怪小說,張讀撰。張讀的外祖父牛僧孺撰有《玄怪錄》,祖父張薦亦有小說《靈怪集》(今佚)。張讀撰《宣室志》,蓋受其祖輩影響。西漢文帝曾在宣室召見賈誼問鬼神之事。張讀將小說取名《宣室志》,題旨也是張皇鬼神。集中所記皆為唐朝佛道神仙、鬼怪靈異、因果報應之事。《宣室志》中載有大量有關僧人、寺廟、夜叉、佛經故事,並宣揚佛教不殺生。這說明佛教在中唐的社會生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影響著人們的信仰和精神風貌,可為韓愈的《諫佛骨表》重要性做一佐證。從另一角度來說,佛教的普及也為《宣室志》提供了大量素材。
與六朝志怪小說相比,《宣室志》有明顯的發展,書中有許多結構完整、情節曲折、注意到人物性格心理狀態刻劃的作品。同時,語言洗鍊、明快,很有特色。往往三言兩語就把人物與故事寫的很生動很感人。《諫佛骨表》、《裴少尹》等篇或曲折離奇,或細膩情濃,深得傳奇手法之精髓。較六朝志怪有明顯的發展,本書又注重刻畫人物形象,特別是神仙鬼怪形象,描寫的繪聲繪色,對後世文學如《聊齋志異》等產生一定的影響。
張讀(834或835~882後),字聖用,一作聖朋。深州陸澤(今河北深州西)人。系張薦之孫,張鷟玄孫,牛僧孺外孫。宣宗大中六年(852)進士,時年十九歲,宣歙觀察使鄭薰召為幕府。乾符五年(878),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時稱得士。中和初年(881)為吏部侍郎,選牒精允。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台。約卒於光啟二、三年間。著有《建中西狩錄》,十卷,今佚。
第01篇 尹君
第02篇 僧契虛
第03篇十仙子
第03篇 章全素
第04篇 尹真人
第06篇房建
第07篇李賀
第08篇侯道華
第09篇閭丘子
第10篇袁隱居
第11篇程逸人
第12篇駱玄素
第13篇俞叟
第14篇石旻
第15篇楊居士
第16篇馮漸
第17篇王先生
第18篇周生
第19篇惠照
第20篇唐休璟門僧
第21篇韋皋
第22篇辛七師
第23篇廣陵大師
第24篇鑒師
第25篇李德裕
第26篇抱玉師
第27篇佛陀薩
第28篇趙蕃
第29篇十光佛
第30篇道嚴
第31篇雞卵
第32篇許文度
第33篇商居士
第34篇寧勉
第35篇悟真寺僧
第36篇師夜光
第37篇李生(一)
第38篇鄭生
第39篇樊宗諒
第40篇王洞微
第41篇叱金像
第42篇迎光王
第43篇彭偃
第44篇李師道(一)
第45篇王涯
第46篇溫造
第47篇李宗閔
第48篇柳公濟
第49篇劉遵古
第50篇聖畫
第51篇李生(二)
第52篇婁師德
第53篇楊炎
第54篇竇參
第55篇貞盧猶子
第56篇鄭光
第57篇張詵
第58篇侯生
第59篇太白老僧
第60篇開業寺
第61篇淮南軍卒
第62篇元載張謂
第63篇陳袁生
第64篇太原小吏
第65篇村人陳翁
第66篇崔澤
第67篇韓愈(一)
第68篇李逢吉
第69篇李回
第70篇郄元位
第71篇夏陽趙尉
第72篇盧嗣宗
第73篇高生
第74篇鄭德懋
第75篇李林甫(一)
第76篇竇裕
第77篇潯陽李生
第78篇陸喬
第79篇郭翥
第80篇利俗坊民
第81篇太原部將
第82篇成公逵
第83篇董觀(一)
第84篇吳任生
第85篇胡氵急
第86篇辛神邕
第87篇唐燕士
第88篇梁璟
第89篇崔御史
第90篇曹唐
第91篇邢群
第92篇李重
第93篇王坤
第94篇楊慎矜
第95篇江南吳生
第96篇朱峴女
第97篇陳越石
第98篇鄭氏女
第99篇廬江民
第100篇謝翱
第101篇僧法長
第102篇鄭生
第103篇清江郡叟
第104篇東萊客
第105篇交城裡人
第106篇崔
第107篇張秀才
第108篇河東街吏
第109篇獨孤彥
第110篇盧郁
第111篇竹季貞
第112篇郄惠連
第113篇劉憲
第114篇張汶
第115篇崔君
第116篇劉溉
第117篇樊欽賁
第118篇姜師度
第119篇鄔載
第120篇韓愈(二)
第121篇裴度
第122篇張惟清
第123篇王璠
第124篇柳光
第125篇李師道(二)
第126篇蕭氏子
第127篇東陽郡山
第128篇智空
第129篇百丈泓
第130篇楊詢美従子
第131篇韋思玄
第132篇李員
第133篇虞鄉道士
第134篇呂生
第135篇嚴生
第136篇玉清三寶
第137篇三寶村
第138篇玉龍膏
第139篇地下肉芝
第140篇盧虔
第141篇江夏従事
第142篇竇寬
第143篇吳偃
第144篇董觀(二)
第145篇鄧珪
第146篇劉皂
第147篇梁生
第148篇趙生
第149篇興慶池龍
第150篇蕭昕
第151篇任頊
第152篇盧元裕
第153篇李修
第154篇盧君暢
第155篇法喜寺
第156篇龍廟
第157篇李徵
第158篇河內崔守
第159篇唐玄宗龍馬
第160篇王薰
第161篇郭釗
第162篇趙叟
第163篇韓生
第164篇李甲
第165篇王縉
第166篇王含
第167篇晉陽民家
第168篇唐玄宗
第169篇陳岩
第170篇王長史
第171篇張鋋
第172篇楊叟
第173篇林景玄
第174篇祁縣民
第175篇李林甫
第176篇李揆(一)
第177篇裴少尹
第178篇計真
第179篇尹瑗
第180篇韋氏子
第181篇興福寺
第182篇李林甫(三)
第183篇韋於春
第184篇無畏師
第185篇利州李錄事
第186篇睢陽鳳
第187篇鄴郡人
第188篇周氏子
第189篇呂生妻
第190篇韋氏子
第191篇韓愈(三)
第192篇柳宗元
第193篇柳沂
第194篇劉成
第195篇李揆(二)
第196篇石憲
第197篇王叟
第198篇韋君
第一篇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詵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發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
北門従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后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
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斟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於人,遂止其事。
第二篇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為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采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
嘗一日,有道士喬君,貌清瘦,須鬢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后當邀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捀即犒於商山而饋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原游稚川,當有捀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
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捀子饋焉。僅數月,遇捀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游稚川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游稚川。路幾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能游稚川,死不悔。”
於是捀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捀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裡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峰迥拔,石徑危,契虛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近,何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余,縱且百里余。捀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捀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橐,自山頂而縋,捀子命契虛暝目坐橐中。僅半日,捀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
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捀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捀子曰:“此僧何為者,豈非人間人乎?”捀子曰:“此僧常願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幾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捀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捀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捀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為誰何瞬目乎?”捀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為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耳。”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捀子即面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悸背汗,毛髮盡勁。又見一人卧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捀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
契虛因問捀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屍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屍,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
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啄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歡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第三篇十仙子
唐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於玄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第四篇章全素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従道士學煉丹,遂葺爐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煉丹卒不成。其後寓游荊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顇,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飢,流徒荊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煉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為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詞拒之曰:“汝,佣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為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為誕妄,詬罵曰:“吾學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佣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佯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簀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簀,而全素屍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后一日,蔣生見葯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燼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余化為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
第五篇尹真人
犍為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余,其上鏨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而緘鎖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雲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啟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
大曆中,有青河崔君為犍為守。崔君素以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詣之,且命破鎖。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遣教曰:‘啟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従。
於是命破其鎖,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為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
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寤。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憨,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為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為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椽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壽矣。’”於是聽崔君還。后二年果卒。
第六篇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従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后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獨游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為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嘆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
第七篇李賀
陝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従小奉親命,能詩書,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恨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人仙之君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第八篇侯道華
河中永樂縣道凈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數。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葯院中,葯成,疑功未究,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玄死,門徒周悟仙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仙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灑掃隸役,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眾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啖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枝垂,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明日昧爽,眾晨起,道華房中亡所見,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脫雙履案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視之,中留一道詩云:
“帖裹大還丹,多年色不移。主
前宵盜吃卻,今日碧空飛。知
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古
他年煉得葯,留著與內芝。齋
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為遲。主
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知
下列細字,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葯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匹,並賜御衣,修飾廊殿,賜名“升仙院。”
第九篇閭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丘子嘿然有慚色。后數歲,閭丘子病死。
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燕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燕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至。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挽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
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燕遊濛陽郡久之。
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后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
第十篇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第十一篇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為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従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游閩越,竟不知所在。
第十二篇駱玄素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跡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岩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葯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余,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余,其屍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
第十三篇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饑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為禮,甚怏怏。因寓於逆旅。月余,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於荊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饑寒色,甚不平。今夕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壞垣,無床榻茵褥。致敝席於地,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栗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従道士學卻老之術。有志未就,自晦跡於此,僅十年,而荊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於羈旅,得無動於心耶令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資,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計,紫綬金腰帶,挽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貲之,無使為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仆馬,可致一匹一仆,縑二百匹,以遺之。”紫衣又僂而揖。於是卻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啟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司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仆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后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
第十四篇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跡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為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雲,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旻謂文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葯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蹤,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為伍乎。”先是雷生有微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廖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膻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曰:“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
第十五篇楊居士
南海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后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啟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嘆,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眾妓,皆雲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嘆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第十六篇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后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穎,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
第十七篇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即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綃巾,衣褐衣,隱幾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發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為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嘆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畫地,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灑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為娛耳。”於是持帚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即馳馬而去。
第十八篇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后將抵洛谷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游月宮事,因相與嘆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知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明,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箸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
第十九篇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
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游,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后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后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后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循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葯,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葯,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台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闃無所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原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従吾師,為物外之游。”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第二十篇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之,原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替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従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疏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輟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即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余,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為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為哉。”
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為,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數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適。
第二十一篇韋皋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所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眾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第二十二篇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窯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跡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窯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煉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窯,又見一辛七在焉。歷七窯,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為“辛七師”。
第二十三篇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為食。日衣弊襲,盛暑不脫,由是蚤蟣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鬥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常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斗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大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汝齪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后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群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焉。
第二十四篇鑒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余。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我廬於靈岩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游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岩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后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岩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游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群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鑒師,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第二十五篇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無睹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巫相張公従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騭固不誣也。”后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第二十六篇抱玉師
抱五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後年九十卒,時方大暑,而其屍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師有之,真佛矣。”
第二十七篇佛陀薩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常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者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資膳裘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群僧。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為吾塔瘞其屍。”果而卒。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屍而瘞焉。后月余,或視其首,發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戶,竟不開焉。
第二十八篇趙蕃
唐國子祭酒趙蕃,大和七年為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善即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為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群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遍院宇,無影響蹤跡。后數日,蕃出為袁州刺史。
第二十九篇十光佛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標冠。有識者雲,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費,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群僧相顧驚嘆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
第三十篇道嚴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實歷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人匿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漬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詞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師見之,無得慓然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質甚異,豐首巨准,嚴目呀口,體狀魁碩,長數丈。道嚴一見,背汗如沃。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圖於西軒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