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
夏濟安
夏濟安(1916—1965),評論家。原名夏澍元。江蘇吳縣人。弟弟夏志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34年進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學習,1937年轉學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今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畢業后相繼在光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香港新亞書院任教。1950年由香港去台灣,任台灣大學外語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夏濟安少年時期先後在蘇州中學、江灣立達學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松江二中)、上海中學求學。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今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畢業,曾任教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外語系和香港新亞書院。1950年來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為早期小說作家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葉維廉等人的啟蒙老師,1956年與吳魯芹、劉守宜等創辦《文學雜誌》併兼任主編,在雜誌上主張“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與其弟夏志清對當代文學的貢獻十分深遠。1959年赴美,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美國奧克蘭,1975年夏志清曾出版其遺著《夏濟安日記》,載錄的是夏先生在1945年1月到9月全部的日記。夏濟安的中文著作還有《夏濟安選集》、《現代英文選評註》等;英文著作有《Gate of Darkness》,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評論集。
夏志清是其親弟。
1956年創辦《文學雜誌》。《文學雜誌》於1956年9 月由台大外文系主任夏濟安教授及吳魯芹和劉守宜創辦。其初衷正如創刊號《致讀者》所言:“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我們雖然身處動亂的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家,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人的時代精神的人。我們並非不講求文字的美麗。不過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從該刊隨後四年中出版的內容來看,它在鼓勵寫實文學的同時,更傾向於十九世紀西方批判現實主義,它介紹了西方現代文學潮流,發表了大量台灣作家創作或翻譯的現代主義作品。

夏濟安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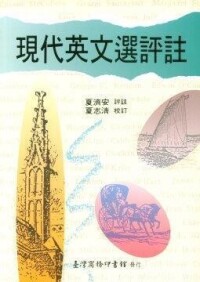
現代英語選評註
1959年7 月,夏濟安離台赴美,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並從事研究工作。后因腦溢血而英年早逝於病逝美國。《文學雜誌》不久便停刊。《文學雜誌》提倡寫實路線,對文學擺脫政治化、庸俗化的道路起了引導作用;同時,它對中西文學理論和作品的評價,也推動了台灣文學素質的提高,提升了純文學的地位。《文學雜誌》能廣納各種風格的作品,投稿者眾多,這無疑對活躍文壇,推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作品有《夏濟安選集》、《夏濟安日記》、《黑暗的閘門》,譯作有《名家散文選讀》、《莫斯科的寒夜》。夏濟安對英美文學有著精湛研究,尤其是國際公認的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專家。其中英文著譯甚多。所選注的《現代英文選評註》至今暢銷海峽兩岸。
“武俠小說這門東西,大有可為,因為從來沒有人好好寫過。”在金庸寫武俠小說之前,夏濟安先生就有這樣的意願了,“將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一定想法子寫武俠小說。”後來,夏濟安讀罷《射鵰英雄傳》,心涼了,“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餘國去了。”
• 吳魯芹言:
• “濟安之‘趣’與一般耍貧嘴說俏皮話就自以為是風趣,別人也以其人有風趣視之,實在是大異其趣的。他首先口齒就不伶俐,要想在說俏皮話或者刻薄話上爭勝,本錢就不夠,而且也不屑為之的。我們不是學究冬烘,但有時也憂慮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把尖刻冷傲之語,看作是幽默與風趣,曾經是我們引以為憂的世風。濟安之 ‘趣’,是從他為人之‘真’產生的。大約當今之世,真面目,真性情,愈來愈少了。不帶幾分假,就很夠有趣,何況他妙語如珠之外,在動作上和辦事務的風格上,又常會奇峰突起,出人意料?”
• 金庸在《天龍八部》後記中言:
• “陳先生(指陳世驤)告訴我,夏濟安先生也喜歡我的武俠小說。有一次他在書鋪中見到一張聖誕卡,上面繪著四個人,夏先生覺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龍八部》中所寫的 ‘四大惡人’,就買了下來,寫上我的名字,寫了幾句讚賞的話,想寄給我。但是我們從未見過面,他托陳先生轉寄。陳先生隨手放在雜物之中,後來就找不到了。夏濟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幾次提到我的武俠小說,頗有溢美之辭。我和他的緣分更淺,始終沒能見到他一面,連這張聖誕卡片也沒收到。我閱讀《夏濟安日記》等作品的時候,常常惋惜,這樣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終究是緣慳一面。”
• 白先勇在《驀然回首》言:
•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
• 劉紹銘言:
• “他的去世標記我生命上的一個轉悷點;我這樣敬愛他,我至少得試寫一部小說奉獻在他的靈前。他知道我寫成了一部像樣的小說,一定比知道我被聘哈佛大學當教授更為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