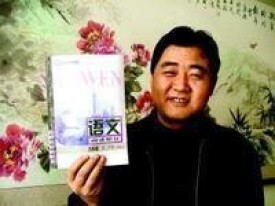季棟樑
作家
季棟樑,出版散文集《和木頭說話》、《人口手》、《從會漏的路上回來》,長篇小說《我的從前在說話》。
1989年,起任靈武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200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作品先後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散文?海外版》、《散文選刊》、《小小說選刊》等轉載,併入選中國文學年度排行榜、年度最佳詩歌、最佳散文、最佳小說、最佳小小說等各種選本。《覺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曾獲中國文學獎。《和木頭說話》入圍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生命的節日》和《夏日原野上的追趕》分別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截止目前已經發表文學作品200餘萬字,小說《覺得有人推了我一把》獲中國作家獎,小說《和木頭說話》入圍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被譽為寧夏文學界的“新三棵樹”之一。2006年所著的短篇小說《奔跑的風景》在當年8月入選中國原創小說8月推薦榜。這是2006年寧夏作家在全國文壇取得的又一成就。2007年1月25日,在“百花迎春”首屆寧夏文藝界迎春聯歡會,季棟樑獲得“鎮北堡西部影城文學藝術獎”、2006年度寧夏“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
《生命的節日》——季棟樑
那個七月已經遠去了。然而,它已經成為我生命的節日。
對於莘莘學子來說,七月,意義重大,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坐標。許多人因為這樣一個坐標,將徹底改變自己人生的軌跡。尤其是我們,生活在西海固這片貧瘠的土地上,七月真正是一個鯉魚跳龍門的日子。
一進入七月,一種賭徒的真正感覺襲擊了我。我就如同一個把所有賭資都押上的賭徒,等待著開牌。那種痛苦的折磨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渴望著太陽和雨水的滋潤,尤其像我這樣的賭徒已經不止一次在七月輸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更讓我感到痛苦恐懼的是在我所有的七月中,父親也經歷著同樣的甚至更為深刻的痛苦的折磨。
一年一度輸贏揭曉的日子如約而來。和許多父親一樣,我的父親一大早將我叫起來。他沒有言語,只是用那種目光籠罩著我。這目光凝滯而沉重,彷彿將我置於一潭黏稠的汁液中,使我喘不過氣來。父親從他貼胸的衣袋裡摸出十元錢來,在他遞給我錢的時候,有些遲鈍,手有些顫抖。而我接過那帶著父親體溫與汗味的十元錢時,手顫抖得更加厲害。我努力表現得自信一些,結果越是要表現得自信,手就越發地顫抖,像深秋里的樹葉一樣,以至連我的身體也抖起來。我是遁逃似的離開了那雙眼睛。雖然我知道那雙眼睛是善良的仁慈的寬厚的,但我內心無法排除對這雙眼睛的恐懼……我再也輸不起了。
我一步一步走向學校,內心的恐懼正在加劇。經過村廟的時候,我不由得走來走去,跪在了那泥像之前,我想沒有人比我更加虔誠,沒有人比我叩的頭更響。
第一年的七月,好容易挨到了“開牌”的日子,父親遞給我十元錢對我說如果中了,就打十元錢的酒回來,沒有中,別糟蹋錢。父親的話總是這樣的直接。可因為僅僅差了兩分我沒有給父親打上酒,我帶著家人渴望花掉的十元錢回來了。父親沒有責備我,然而他越是不責備我,我內心的痛苦就越沉重。到了新學期開學的時候,父親對我說再去念吧,差兩分一年咋都弄夠了,我那時候在生產隊哪一年不比別人多掙個三五百工分?我無法對父親講學習和勞動的不同,我只有努力學習。
第二年七月的“開牌”,我又輸了十二分。當我再次把錢放在父親當面的時候,父親火了,他對著我吼道:狗日的鼻涕淌到眼窩裡——倒來了,你給我回來打牛後半截去,老子沒有錢供你享福。是的,在家鄉那樣焦苦的地方,誰不認為讀書就是享受呢?我想對父親說如果讀書真正可以叫做享受的話,那麼我寧願受苦。可是我說不出那樣的話來。父親一輩子好強,他是多麼希望能夠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面,來打點種田以外的事啊。要批房地基,他跑了多少趟,沒有批下來,可是有人偏偏一批就是兩處。這對於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打擊是沉重的,這讓他充分認識到了種田人的可悲與無奈,人家無非就是有一個在縣裡開車的兒子。然而我們弟兄硬是一個個不爭氣,大哥二哥相繼種了田,希望便寄托在我的身上,可我偏偏如此不出息。我期待著新學期的開學,可是又怕這個日子的到來。然而日子並不因為我內心矛盾而就推遲。開學了,父親說再讀!父親依然沒有多餘的話。可那每個字都像石頭一樣,把地能砸出個坑來。他親自送我到四十餘里以外的鄉里上學。父親走在我的前面,拉著驢,馱著我的鋪蓋,他的步履顯得有些疲勞,甚至是麻木,那已經駝了的背越發弓得厲害,彷彿背負的東西越來越多了,非要這樣將背弓起來似的。他已經是年過花甲之人,應該是歇緩享福的年齡了。
看著父親的背影,我忽然失去了賭的慾望,我為什麼要繼續賭下去呢?怎樣不是活一輩子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學不都輸了個精光回來了么?我鼓足勇氣說:“爹,算了,我不念了。”父親回過頭來看看我,他的目光里不再有那種凝重,反而兇惡起來,彷彿被激怒的老虎,一甩手,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臉上。之後便默默無言,繼續走自己的路了。我的臉火辣辣地疼痛,可是我心裡卻踏實了,我想至少父親對我發怒了。
第三年的七月,不爭氣的我又輸了,我捏著那十元錢在一個山樑上坐了許久,最後我一狠心走進了供銷社,打了十元錢的酒。當我看著那晶瑩的液體帶著醇烈的芳香汩汩地流進瓶子,我的眼淚卻來了。我順著小路往回走,二十二歲的身體卻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沉重與疲憊。在與村子相對的山樑上,我遠遠地就看見父親像一隻老鷹,蹴在大門口,他手裡長長的煙鍋不停地噴出煙來,像一列鑽出隧道的火車。父親站了起來,他伸了一個非常舒展的懶腰,身體像蜷縮了一個春天的花朵盡情地舒展開來,兩隻長長的胳膊伸了伸,還上下起伏了幾下,那是一種飛翔的姿勢呀!父親真像一隻要飛起來的老鷹。我想我手中的酒瓶在夕陽的餘暉里一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這光芒一定照亮了父親的眼睛,父親一定聞到了代表著喜慶與快樂的酒香。
在父親的注視下走完一段上坡下坡的路,我感到渾身的不自在,兩條腿彷彿給什麼絆著一般,不足一里路,我卻走了十幾分鐘,走出一身大汗來。剛剛走到大門口,父親就對著院子喊:“紅紅,快把涼水給你哥哥端出來。端上兩大碗!”
我再也忍不住鬱結的悲傷,一放聲就哭了出來,兩腿再也支撐不住,撲通一聲坐在地上。
我說我沒考上!
父親一揚手裡的長煙鍋,打在那兩瓶酒上,酒瓶碎得十分徹底,酒像月光一樣灑了一地,醇烈的酒香瀰漫開來。
妹妹正端著水出來,由於驚嚇,碗掉在地上碎了。
父親一轉身走向山頂。夕陽將父親的身影扯得很長。我默默地跟在父親的身後,我想父親會轉過身來給我一煙鍋,兩煙鍋……甚至更多,我渴望這樣。然而,父親沒有。到了山頂,父親又裝了一鍋煙,吸了一鍋又一鍋,最後父親說做官中狀元都是出在祖墳里,咱墳里沒埋下。
我對父親說:“爹,你再給我一年時間!”
父親抬起頭看看沒說什麼,他只是抽著煙凝望著天空。
開學了,父親再次拉著毛驢馱著鋪蓋送我上學,一路上我們沒有說一句話,可是我卻聽到了更多的語言無法表達的話語。父親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背駝得愈發厲害了,讓我想起門台上那棵旱了多年的彎脖榆樹來。我的淚一直流到了學校。
後來,我終於用那十元錢打回酒來了,那是一種非常廉價的散酒,用黑缸盛著,有一斤的勺子,有半斤的勺子。因此買那種酒叫打。可是即使再廉價它也是酒啊。它代表著喜慶與歡樂,它就是節日。除非過年婚娶能喝到酒外,再是很難喝到酒的。用家鄉人的話說酒是有閑錢的人喝的。家鄉人沒有閑錢。家鄉人的錢比家鄉人還忙。
父親醉了,把我也弄得醉意朦朧。他拉著我的手直叫我兄弟。這讓我想起他拉著我家的那頭老牛叫兄弟的情景。我想我不是個好兒子,我讓他跟著我受了四年的折磨,如果我第一年就考上,我的父親或許不會醉成這個樣子,更不會喊我兄弟的。
父親要為我舉辦村子里最豐盛的宴席,我說算了,這幾年把家裡拖累的。可父親說這是啥事,這事能輕易讓過去?這是咱祖祖輩輩最大的節日,砸鍋賣鐵也得過大了。
從考上大學到畢業,我一直奔波於塵世之中,往來於凡俗之間,忙著娶妻生子,忙著房子、兒子、票子以及多彩的人情禮儀,幾乎擠不出什麼閑錢來買名貴的酒。後來我終於擠出點閑錢來買了上好的酒,送回鄉下。可是父親聽說這酒一瓶就四百多元時說酒沒有貴賤,只有心情有貴賤。我點點頭,父親沒有文化,更不是哲人,可是他說出的話常常讓我要思考許久許久……
那瓶酒至今還放在家裡的棗木老櫃中,因為父親自己喝覺得沒意思,拿出來招待人卻又覺得太奢侈。
魯迅文學獎 提名1次
2004 ·魯迅文學獎 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