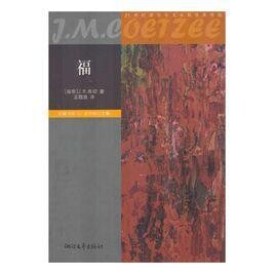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福的結果 展開
- 漢語漢字
- 一種春聯
- 南非作家庫切於1986年創作的長篇小說
- 單機遊戲《軒轅劍伍:一劍凌雲山海情》角色
福
南非作家庫切於1986年創作的長篇小說
《福》是南非作家庫切於1986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以主人公蘇珊作為個體對事件的親身經歷,一種小歷史去反撥那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宏大歷史。在對大歷史的反撥方面,該書做出了極有價值的探索。這種探索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歷史本身的多面性和複雜性,同時也展現一條解構歷史的路徑。

其他版本的《福》
《魯賓遜漂流》歐洲典基礎改。歐洲“”稱號丹尼爾·笛福根據當時一名英國水手的真實故事所撰寫的《魯賓遜漂流記》一經出版便大受歡迎,成為歐洲文學的經典之作。只是針對童年的一次追憶,庫切1986年出版的《福》,顯然是一部利用童年經驗創作的作品。這種靠追憶、整理碎片來構成一部藝術作品的情況並不少見,而且對於大師來說,那既是一個現成的資源(它就一直放在那兒,隨時聽任你的召喚),又是一個不用費勁兒就能獲取的結實材料(打開回憶之門,沒有比這更可靠和輕鬆的事兒了)。只不過,庫切這一次利用的是童年的一次閱讀,就是兒時庫切讀過最多,也是最著迷的一部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庫切通過完成對童年的追憶,以及對碎片的整理工作,表達了一個成年人對兒時的一種緬懷。他所做的只不過是一種追憶,一種對自我負責的追憶。將這種追憶的過程展開來看,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福》。把創作小說說成一種追憶,牽強得幾乎需要解釋。如果沒有庫切童年對這部18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著迷以及後來的不斷的認識,怎麼會有這部《福》呢?從這角度理解,正是兩者發生衝突,進而有了火花,這就是這部小說創作的過程及產物。
蘇珊·巴頓
《福》的敘述者蘇珊·巴頓,是一個冒險家,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笛福的“羅克塞娜”的性格特徵,她對魯賓遜男權意識領導權的挑戰是有意的,她的出現也是對傳統的帝國主義敘事體及權威的挑戰。蘇珊尋找被綁架的女兒的過程中,遇到船難,漂落到荒島,被一個全身赤裸的歐洲男子魯賓遜·克魯索和黑人啞巴星期五所救。蘇珊返回英國后決定寫出並出版她的這段經歷。由於她自己沒有很強的寫作能力,就找到了作家福,但福篡改了蘇珊·巴頓講述的內容,把蘇珊的所見所聞改編成可讀性很強的小說,從這裡可以知道小說是如何產生的。蘇珊·巴頓本人卻想把在男人記載的文檔里被刻意抹去的女性經歷重現於世人面前,她自己荒島生活的經歷正是這種生活的體現,也是她努力想讓世人知道的一段經歷。而福卻把她引以為自豪的經歷壓縮為她流浪生活的一個小插曲,把重心放在探討挖掘蘇珊荒島之前的生活之上,蘇珊非常氣憤。蘇珊為自主而抗爭,為爭奪作為女性的話語權利而抗爭,她努力把自己從男人為女人設置的規範中解放出來,她決定走自認為適合的道路,不落到男人的牢籠里。因此她這樣告訴福:“我選擇不告訴你我在船難之前的生活經歷,因為我沒有欠包括你在內的任何人一個解釋,一個關於我為什麼擁有故事的原因的解釋。我選擇去講我、克魯索和星期五在小島上發生的故事。我是一個自由的女人,我有自由去講我願意講的故事。”
然而同時,蘇珊·巴頓又是一個十分複雜且自相矛盾的人。儘管她不斷地抗爭,但迫於許多現實的壓力,又不得不進行妥協。福建議把蘇珊隔離於故事之外,在另外一個地方講述她的故事(尋找女兒的故事)。蘇珊·巴頓感覺到她堅持的敘述以及她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自由人的事實都不翼而飛了。蘇珊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用起了男子的名字。在英國,她用了魯賓遜·克魯索的名字,聲稱是他的妻子,目的就是為了擁有魯賓遜的物質財產的權力(在回英國的船上,魯賓遜·克魯索已經死了)。後來,蘇珊和福還為了誰擁有故事的所有權而鬥爭。
魯賓遜·克魯索
只要探索式研究一下,就可以在文本上找到這樣的關係——“魯賓遜”的故事原型來源一個蘇格蘭水手,他消極地在荒島上獨自生存了四年零四個月;笛福筆下的“魯賓遜”是一個18世紀英國的冒險家和實幹家,他在孤島上靠堅挺的毅力拚搏了28年;到了庫切這裡,“魯賓遜”是一個少言寡語基本喪失了人類機能的一個偷生者——他不願冒險,甚至不願意離開孤島,漸漸開始適應並幻想這座孤島上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庫切的“魯賓遜”是一個十足的現代版的“魯賓遜”,換句話說,他具備了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味。三個形象所貫穿的基本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時代出於不同的目的,有了三種截然不同的三個人。在庫切的《福》里,甚至將這一經典化的英雄形象完全顛覆,或者說抹煞了。《福》中的“魯賓遜”沉默寡言,對於“魯賓遜”的解釋已經不是孤獨和荒涼可以解釋的了,他對待來到孤島的“蘇珊·巴頓”的反應,幾乎可以說他已經喪失了正常人的心思和念頭。
其實,庫切筆下的魯賓遜不敢在島上生火或在山上揮舞帽子跳舞,倒不是因為害怕海盜或食人族,而是因為他安於現狀,頑固不化,不想被解救。魯賓遜除了異想天開以外,並不能講出事實的真相,沒有任何文字為依託,沒有用筆記錄下隻言片語,他總是抱著這樣的態度:“沒有一件我忘記的事情是值得記憶的。”這就與帝國的權威敘事形成強烈的反差。敘事體、文字摘錄使帝國的真理變為現實,它需要常常去敘述、回憶,才能在歷史上留下痕迹,而魯賓遜放棄了這種權利,他希望他的島上故事隨著離開荒島的那一刻而沉寂。
魯賓遜其實是帝國主義男性的代表,他象徵著統治、征服的能力已經被顛覆,而顯得女性化,甚至連人類基本的兩性慾望都喪失了。蘇珊曾問過星期五:“如果你的主人真的希望成為一個殖民者,並且要留下一塊殖民地,難道他就沒想過要留下自己的後代嗎?”蘇珊和魯賓遜之間是性別的對立,魯賓遜·克魯索這位殖民者軟弱無能,啟蒙理性的虛構本質已經暴露無疑,他還喪失了敘事權威,這意味著帝國、男性權威受到威脅。魯賓遜在返迴文明世界的途中病逝,荒島生活的真相落到了蘇珊和星期五的身上,而星期五的不能言語導致魯賓遜的話語權力完完全全控制在了蘇珊·巴頓的手中。蘇珊以克魯索夫人的名義,向英文世界的人們傳達了他們的荒島生活經歷。蘇珊可以隨意增減甚至誇大魯賓遜的故事,魯賓遜的經歷到底是真相還是虛構?就不得而知了。這對男性敘事佔據權威的西方世界來說真的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和挑戰,以至於後來出現了作家福,他又蓄意改變了蘇珊的敘述,使話語權力得到了分流,故事也就離事情的真相和現實越來越遠了,甚至讓人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構的,而真相完完全全只掌握在一個人的手中,那就是啞巴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是庫切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設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是個黑人奴隸,曾經是野蠻的食人族的一員,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而且又是個啞巴。魯賓遜·克魯索和蘇珊·巴頓的出現使星期五認識到所謂的文明人的世界是怎樣的,而星期五的無言是沉默?是震驚?還是無言的對抗?星期五本身就是一個謎,特別是他的那些奇怪的肢體動作。
星期五的出現使文本呈現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模式,白人與黑人的對立,文明人與他們所奴役的野蠻人之間的對立。庫切的小說呈現的黑人與白人的關係是一種既敵又友的關係,甚至是敵友難分的,縱然庫切並不願意見到黑白對立的情況。蘇珊·巴頓的出現其實起了一種弱化作用,用來調和兩者之間的關係。庫切被認為是反種族隔離的作家,因為他向來同情弱者。星期五的無言和無知是一個黑人形象對白人世界進行反抗,星期五的無舌是白人敘事下的一道陰影,他的沉默是無以言傳的文字的敵人。
在《福》中,主人公作為敘事者是一名女性(要知道,女性在《魯賓遜漂流記》這部18世紀英國標榜成功男人的小說中所沒有的),庫切在書中用主人公“蘇珊·巴頓”的話解釋了這一“衝突”:“但是哪裡能沒有女人呢?”即使孤島也如此,庫切的意思是,沒有女人的世界就是沒有人類,沒有人性,沒有人味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別說生存,就算是呼吸都難。
西方傳統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理性的產物,整個歷史的發展是以一種不斷進化的模式進行,即由進步取代落後,文明戰勝野蠻。而現代語言學表明:語言是不確定的,語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其意義取決於上下文之間的語境。因此,語言不再像傳統所說的像一扇透明的窗戶,能客觀真實地再現現實;自然,以這種語言為媒介的歷史表述也是不客觀的、不公正的。這恰好表明了殖民者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是通過霸權話語實現的,從而揭露了作為官方權威的殖民版本的虛構性。庫切在《福》中利用了語言的這一功能重新謀劃了歷史,以反抗歷史的權威機制。在後殖民語境下,伴隨傳統的顛覆,對中心的解構以及對邏各斯等啟蒙觀點的質疑,任何事物不再被賦予唯一的一種意義,相反,它們具有各種各樣的闡釋的可能。笛福小說《魯賓遜漂流記》講述的是白人男性克魯索流落到美洲沿岸的荒島,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戰勝困難,最後在小島上生存下來並建立了相應的殖民體系的故事。薩義德更把《魯賓遜漂流記》作為當代現實主義小說的原型,並認為:“這部小說並非偶然地講述了一個歐洲人在一塊遙遠的、非歐洲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封地。”“那個小說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創建者,他為基督教和英國而統治和擁有這片土地。的確,是一種很明顯的海外擴張的意識形態使魯賓遜做到了他所做的事——這種意識形態在風格上與形式上直接與為巨大殖民帝國奠定基礎的16世紀與17世紀探險航行的敘述相聯繫。而在笛福之後的主要小說,甚至笛福自己後來的小說似乎都為了激動人心的海外擴張的圖景而作。”小說通過克魯索努力奮鬥最終成功的經歷,宣揚了殖民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也是一部反映歐洲殖民思想的作品。
在《福》里,后殖民主義和西方融合得更加完整。《福》公開地袒露了殖民主義,同時也關注著帝國主義和啟蒙精神。就蘇珊和星期五來說,一個是殖民者的後裔、白人女性,一個是被殖民者的後裔、黑人男性。蘇珊和星期五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他們兩個其實是互為他者的。蘇珊代表西方文明,代表白人世界,她的自我是不允許星期五這個他者——代表了純粹的非洲原始文明,與大自然、與祖先最接近的文明——的存在的。於是,蘇珊想盡一切辦法,想同化星期五,使他接受歐洲的文明,成為和她一樣的文明人。蘇珊用啟蒙思想,教星期五識字,認英文,試圖讓他開口說話,發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星期五看到蘇珊描繪出的非洲的景物時,他的眼神是空洞的,渺茫的,也是陌生的,絲毫沒有見到熟悉景物的那種興奮。也許是星期五心目中關於非洲的看法跟蘇珊的完全不一樣,只是蘇珊把自我的看法強加到星期五的身上,而星期五隻是以沉默來作出是否要被同化的兩難抉擇。
在《福》中,蘇珊和星期五之間的不能溝通,反映出自我與他者的不能交流,交流的不可能性很快會成為交流的不受歡迎。在庫切的《福》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是可疑的,蘇珊對星期五的態度是矛盾的,蘇珊既對星期五的理解能力感到失望,對他對現代文明的無知感到遺憾;但同時,蘇珊又發現,星期五的肢體語言、舞蹈、音樂十分玄妙,她想努力探尋星期五為白人世界所不知的秘密。在蘇珊排斥星期五的時候,又覺得喜歡星期五,甚至想引誘他,蘇珊就是這樣在排斥和欣賞之間跳躍。在《福》中,在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界限有時又是模糊的、不明確的。
另外,庫切把《福》的結尾安排得比較魔幻,比較超現實,他安排了一個死亡的畫面:在福的家中找到了福和蘇珊的屍體以及笛福的著作。這個結尾解構了著作的所有權和真相,而且將啟蒙思想也瓦解了。庫切也許在暗示南非的整個文明都停滯不前了,南非的白人領導者一直都不停地強調自己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一直捍衛這種思想觀念並把它強加於黑人身上。“在這種啟蒙、教化的思想體系下,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十分尷尬,教化的結果,就像星期五本能的聲音從他嘴裡被根除了一樣,連同他的舌頭,什麼都給破壞掉了。”其實自我在影響、同化他者的過程中,也受到他者的影響;在現實中,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黑人和白人應該是相依為命的。庫切的小說《福》充滿了神秘性,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它跟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一樣,用的是第一人稱,但又從一個女性敘述者的角度,講述了魯賓遜、星期五和蘇珊的故事。但在故事的最後一部分,那個充滿後現代意味的尾聲中,敘述者跳出了框架之外(結尾沒用引號來敘事,因此不是蘇珊向福講述的),以一個不知名的“我”,進入蘇珊、星期五和福的世界里,打破一切敘述主體的幻象。星期五的口中流淌著無言的溪流,是他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解放。《福》消失在它敘述的“洞”中,消失在星期五無舌的口中。
庫切的作品素來以南非社會、黑白膚色、殖民歷史、種族隔離、政治暴力等話題為主,《福》雖然並未針對南非的現存問題,但隱含著內在的焦慮。他選擇改寫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其實是對白人男性敘事的不確定,對帝國敘事的不確定。庫切考慮到其他性別,其他種族,其他膚色的人群可能對既定的敘事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有可能去解構這種以白人男性為中心的敘事方法。庫切以後現代主義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南非白人的焦慮和不安。
標題
正如庫切所說的:小說的本質與創作過程這個問題也可以被稱作為“誰在寫”的問題。小說標題“福”(Foe)是笛福(Defoe)去掉前綴“De”而來。從字面意義來看,“Foe”的原意為“敵人”、“仇敵”之意。“Defoe”一詞可以理解為“解構敵人”或者“剝下敵人的偽裝”之意。同時,在目耳曼語中,“De”放在姓氏前是尊貴的象徵。據史料記載,笛福本姓“Foe”,後來為表示自己的尊貴,在自己姓名前加了“De”改姓為“Defoe”。庫切在他的小說《福》中,讓笛福(Defoe)恢復自己的真實姓氏福(Foe),這就使讀者會產生許多疑問:如果說《魯賓遜漂流記》中,作者的創作意圖是對殖民主義的歌頌,那麼,《福》中,作者的真正意圖是什麼?由作者為福恢復真實性氏的微妙變化,可以真正認識到作者在這裡也是“解構、質疑笛福的創作意圖”,對魯賓遜這個所謂的英雄進行質疑,讓讀者參與到作品中來,以自己的思維去認識庫切。
《福》對《魯賓遜漂流記》的重寫
但是,《福》通過對《魯賓遜漂流記》的重寫,質疑了文本中所體現的殖民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在《魯賓遜漂流記》的基礎上,庫切加入了一位白人女性蘇珊·巴頓,並對這部經典進行了重新敘述。小說講述的是蘇珊,巴頓為了尋找被英國奴隸販子拐賣到巴西的女兒,途中遇難,飄落到荒島並遇到克魯索和星期五。後來他們被過往的船隻所救,克魯索卻因精力衰竭而死於船上。回到英國后,蘇珊希望藉助作家福的力量真實地敘述荒島故事,而作家福卻為了取悅出版商和讀者,讓故事能賣個好價錢,篡改了蘇珊講述的故事,並把蘇珊·巴頓這一重要故事人物完全取消。福和蘇珊對於爭奪故事講述權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行為,它與創作者的目的、意圖,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而這也說明了,庫切在《福》中展現的是作者是完全不可靠的,而歷史的記述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主觀的。
西方傳統的思維模式是以主體為中心的主客二分,在這一思維模式下,物質世界被分為一系列二元對立的關係如自我與他者、白人與黑人、男人與女人。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永遠佔據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位置,他們理性、文明、高等,而與之相對立的他者——被殖民者則是非理性、野蠻、低等的。這種殖民主義的二元對立的意識滲透於各種殖民主義敘事中,致使人們相信西方永遠處於中心地位而東方則永遠處於依附和順從的地位。在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中,魯賓遜是一個理性、精明能幹、充滿活力的、在困難面前百折不撓的開拓者的正面形象,星期五是他忠實、順從的奴僕,星期五隻是作為魯賓遜的對立面而存在,是服務於魯賓遜的。然而,在《福》中,庫切筆下的魯賓遜卻是一個沮喪,容易厭煩,沒有精神動力的頹廢者。這就意味著以魯賓遜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受到威脅並趨於衰弱。這就從內部解構了以西方白人為中心的二元對立關係模式。
《福》中對星期五的形象也進行了改寫,《魯賓遜漂流記》中的星期五是由魯賓遜從食人生番手中救下來的,不僅是他的生命,就連他的名字都是由魯賓遜賦予的。他是一個忠實的奴僕,對主人言聽計從,百依百順,為了和主人在一起,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他皈依主人的宗教,努力學習主人的語言。一句話,他是殖民者眼中最理想的“選民”。而在《福》中,星期五不但被割掉了舌頭,還被閹割了,不但失去了被話語殖民的可能,還使殖民者失去了繼續壓迫自己下一代的可能。他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對殖民統治進行反抗。
結構
從細節到結構,庫切都胸有成竹地一步步設下“陰謀”。《福》分成了四段式結構,這在其他藝術形式上越來越多見(《太陽照常升起》不就是嘛,打亂敘事時間,怎麼來勁怎麼安排,全聽藝術家的安排)。不生硬、流暢的技術探索一直是庫切願意做的,在他所有作品中這種探索和嘗試一直進行著。庫切在《福》中的四段式,沒有在時間上下手腳,而是打破了敘事角度,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交替進行,到了最後結尾,甚至第一人稱保留但敘事者換了——一個從未出現過的人,出現在小說結尾,用不大的篇幅來審視和總結全篇。這種形式上的探索,好像是對一件事進行終審般的立體式描述。時間不會停歇,攝影師輾轉角度來拍攝事件發生的變化,給了讀者以全方位的感受。
《華盛頓郵報》:一本有點兒不可思議的書……具有奇妙的庇意和無法抵禦的穿透力。
《紐約時報》:對於作者的才智、想象力和技巧而言,《福》是其能力和爐火純青的證明……文字明晰精確,景物描述在虛指中又帶有特定涵容。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