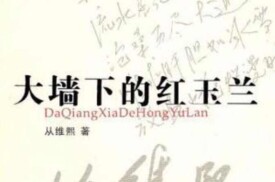大牆下的紅玉蘭
中國當代作家從維熙的代表作品
《大牆下的紅玉蘭》是從維熙創作的中篇小說,首發於1979年《收穫》雜誌第二期。
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原省公安局勞改處處長葛翎,蒙冤入獄,與林彪、“四人幫”一夥的倒行逆施進行無畏的抗爭,最後血灑大牆的悲劇故事。小說通篇洋溢著激奮、慷慨、壯美的情調,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色彩。這部作品將藝術筆觸首次伸向社會主義國家牢獄的大牆之內,以突破題材禁區的勇氣,開闢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一個新的領域——“大牆文學”。
“四人幫”即將覆滅的前夕,在黃河畔的勞改監獄里來了一個“新犯人”葛翎。他剛邁進監獄的鐵門,就遭到“造反起家”的勞改農場“政委”章龍喜指使的由“死緩”減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馬玉麟的折磨:葛翎剛放下行李,馬玉麟不顧葛翎七十里步行的勞累,更不顧葛翎腿腕的傷口正在滴血,硬把葛翎送往風雪漫天的黃河岸邊的工地上。
到了工地,犯人班長馬玉麟故意讓壯得像公牛一樣的流氓頭子俞大龍與頭髮白了的葛翎一起抬二百多斤重的泥兜,爬七八米高的斜坡。葛翎強忍著痛苦抬到了堤上,以至壓斷了桑木扁擔。此刻,因拋鐵餅失手而傷人的體育學院學生、勞改隊統計員高欣挺身而出,嚴懲了俞大龍。俞大龍正要反撲,勞改農場場長路威騎馬來到了工地。路威是葛翎的老戰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兩人結下了戰鬥友誼。戰爭結束后,他們一同轉業到某省公安局。路威到工地一看,老犯人馬玉麟與流氓頭子俞大龍正折磨葛翎。他氣憤之極,使用手銬把馬玉麟與俞大龍銬上送走;又派人把葛翎背進工地帳篷里。在帳篷里,葛翎陳述了他的遭遇。“文化大革命”初期,老共產黨員、省公安局勞改處處長葛翎就以“走資派”的罪名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在幹校里,他因不滿“宗教式”的低頭弓腰的“早請示”,被血洗公檢法的武鬥專家秦副局長批鬥懲處。後來,葛翎因筆記本上抄引了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不要把毛澤東看成神秘的,或者是無法學習的一個領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與“還鄉團”,投入監獄,成了既無刑期又無法律手續的“犯人”。葛翎講過他的不幸遭遇后,路威兩眼噙淚,激動地說:“讓共產黨員來蹲共產黨的監獄……這到底是誰專誰的政?!”而後,路威決定送葛翎到農場醫務所去就醫。
在大雪紛飛的路上,葛翎騎在馬上,路威拉著馬韁繩。他們在談話中,披露出老犯人馬玉麟原來是三十年前葛翎領導下的工作團鎮壓的冀東昌黎縣馬家寨惡霸地主馬百壽的兒子。當時,土改工作團為歡慶翻身演戲之際,馬玉麟率領還鄉團殺回馬家寨。工作團與敵人交火后,邊打邊退。葛翎擔心舞台上毛主席的相片落入敵人手裡,冒著槍林彈雨爬上舞台摘下領袖像,不幸被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葛翎始終護著胸前衣里藏的毛主席像。正當馬玉麟要對葛翎剖膛挖肝之際,八路軍騎兵打進馬家寨。馬玉麟倉皇中打了葛翎一槍,子彈打在左腿腕上。現在葛翎腿上滴血的傷口,就是當年馬玉麟的一顆子彈給留下的“紀念”。
他倆正在漫天風雪的路上走著,迎面遇到了來探望高欣的正準備出國比賽的體操運動員周莉。周莉急切地向路威打聽她的男朋友高欣的情況。路威向周莉介紹了高欣的近況。他們三人正向前走著,老罪犯馬王麟和俞大龍走來,說章龍喜把高欣禁閉起來而放了他倆人。路威一怒之下,命令馬玉麟與俞大龍滾回監房,等候處理。
鍛工出身的路威怒不可遏,質問章龍喜,為何禁閉高欣而放了馬玉麟與俞大龍。章龍喜大施淫威,想勸降路威。路威知道章龍喜背後有造反發家的秦副局長的支持。於是,他去找農場黨總支,想利用集體力量來對付章龍喜之流。後來,在黨總支會議上,決定禁閉馬玉麟與俞大龍,釋放高欣。路成親自解除了高欣的禁閉,告訴高欣,他的女朋友周莉來看望他了。歸來的路上,高欣懇求路威不要讓他見周莉,以免影響周莉的前途。他們剛走到招待所的窗下,周莉突然出現在他們的眼前。隨後,在路威的精心安排下,周莉與高欣整整會見了兩個小時。
入夜,葛翎怎麼也睡不著。他一眼看見老反革命分子馬玉麟竟然睡在他的身旁。過去用麻繩沾著冷水打過他的還鄉團、紅眼隊的階級敵人,如今又在工地上折磨他。這真是人妖顛倒,歷史倒退。葛翎越想越難入睡,於是走出監房。正巧,與周莉會面的高欣從鐵門外回來。高欣把周莉拍攝的紀念周總理活動的照片拿給葛翎看。他倆商議,在清明節來到之時,做個花圈,以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葛翎與高欣分手后回到監房,一看,他身旁睡的馬王麟不見了。葛翎斷定他與高欣的談話被馬玉麟偷聽去了,這傢伙肯定是去告密。葛翎忙返身出屋,直奔鐵門。果然,馬玉麟正請求門警給他開門。葛翎急中生智,告訴門警:“馬王麟是神經病。”門警才把馬王麟趕走。在他們回監房的拐彎處,葛翎當著這個三十年前的對頭冤家的面,曆數馬家罪惡史,並警告馬王麟,如果繼續作惡,將來新賬老賬一齊算,人民不會饒恕他。馬玉麟當面態度很虔誠。但葛翎一想,這個反動傢伙是不會停止罪惡活動的。於是,他就去找高欣,設法轉移那疊照片。正當葛翎去找高欣之時,馬王麟寫了告密紙條投放引監房外的檢舉箱里。
章龍喜得到馬玉麟的告密紙條后,如獲至寶。他先到汽車站追周莉,汽車已開動了。周莉與路威正告別,章龍喜問那女孩是誰,路威說是他的侄女。章龍喜威脅路威。路威不聽章龍喜的狂吠,轉身到監房給馬玉麟和俞大龍戴上狼牙銬,送入禁閉室。章龍喜為了得到照片,在眾多犯人面前對高欣搜身,又去高欣的統計室挖地三尺,但一無所獲。此時,路威正在看望葛翎,葛翎機智地把炕洞里所藏的照片交給路威轉移出去。當章龍喜來搜查葛翎時,又撲了個空。被激怒了的章龍喜去禁閉室找馬玉麟。馬玉鱗一口咬定他親眼看見過照片,並告訴章龍喜清明節“他們要弄花圈”。馬玉麟還附在章龍喜的耳邊獻計。章龍喜得到了“妙計”后,高興得手都抖起來。
一整天,葛翎琢磨該怎麼為悼念周總理而製作花圈。他猛然看見大牆外有一棵幾米高的大玉蘭樹。他想:給周總理做花圈的紙讓章龍喜收走了,摘下玉蘭花來仿花圈倒是好辦法。葛翎與高欣合計去摘玉蘭花,但摘花必須上大牆;上大牆,警衛有權開槍。左思右想,兩人決定夜間冒險摘取玉蘭花。為了保護高欣,葛翎自己強忍著腿上傷口的疼痛,架梯子攀登上大牆。當葛翎正上去摘玉蘭花時,警衛小戰士欲要喊他,突然出現在警衛眼前的章龍喜激動地說:“別喊他,讓他上。”並威逼小戰士開槍。小戰士無奈把槍機抬高,章龍喜在戰士開槍時猛向下按了一下槍機,正好對準葛翎。槍響了,葛翎抱著兩枝潔白的玉蘭花,從高梯上跌落下來。高欣機敏地張開雙臂,抱住了跌下來的葛翎。然而,葛翎閉上了雙眼。他的熱血染紅了緊握著的兩枝玉蘭花。
兩天之後,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長來到河濱農場處理“反革命事件”。大牆外,章龍喜當了總支書記;大牆內,高欣關了禁閉,俞大龍當了犯人班長,馬玉麟提前釋放。當秦副局長帶人逮捕路威時,路威早已懷揣那兩枝紅色的玉蘭花,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車,到黨中央告狀去了。
創作源起
1957年,從維熙因為發表文章、小說批評官僚主義作風而在“反右”風暴中被下放農村強制勞動。在農村勞動改造期間,他又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對三面紅旗的不滿。結果被當成“極右分子”處理,1960年,與妻子一起被送進監獄勞動教養。從那以後,他輾轉於北京、天津、山西的多所勞改農場之間,以勞改犯身份接受改造,直到1976年才結束勞改生涯。近20年的“大牆”生活中,從維熙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如蒙冤入獄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品格高尚的革命青年,執行政策的勞改幹部,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渣滓等。在監獄里,他遇到過舅舅和外甥兩人,解放戰爭時期,舅舅是國民黨軍官,外甥是解放軍,1957年“反右”以後,外甥被打成右派,送進勞改隊,與早已是勞改犯的舅舅住在一個監房。這種歷史性的巧合給了從維熙很大刺激,並形成了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的初步構思和框架。當他有條件寫作時,他回顧大牆生涯中遇到過的人和事,感到沒有比監獄更能本質地體現那段人妖顛倒的歷史歲月縮影的地方了。於是,他開始創作《大牆下的紅玉蘭》。
人物、情節原型
對於小說主人公葛翎的設置,從維熙是從瀋陽市公安局副局長劉麗英的經歷中得到的靈感。“文革”期間,劉麗英被送進監獄,造反派曾找了死刑犯來看管折磨她。馬玉麟、俞大龍也是從維熙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提煉出來的。1968年,從維熙在茶淀農場與刑事犯編成一組,當時的組長平克賢是昔日八大胡同的老鴇,專門負責管理像從維熙這樣的“右派”。路威的原型是從維熙在茶淀農場改造時的主管隊長劉隊長。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劉隊長曾主動安排從維熙去相鄰的女隊看望妻子,並破例允許他在那裡留宿一晚。高欣和周莉的原型來源於從維熙的畫家朋友、曾與他一起在京郊勞動的王復羊和崔振國的愛情故事,而從維熙與妻子張滬的感情經歷也是小說中高欣、周莉之間堅貞不渝的愛情的生活依據。另外,從維熙聽說他的一位同窗在“文革”曾不顧勞改單位的禁令在衣服上掛了小白花紀念周總理,結果遭到輪番批鬥。從維熙從這件事出發構思了葛翎為悼念總理而冒著生命危險摘玉蘭花的情節。
葛翎
襟懷坦白、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員,在戰爭歲月為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曾任省公安局預審科長、勞改處處長。在大搞現代迷信的年代,他堅持真理,寧願被斗坐監,也要公開抵制錯誤的潮流。入獄后,他目光銳利、敏感機智,面對馬玉麟、俞大龍的瘋狂報復,他毫不膽怯,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壓倒一切頑敵的勇氣沉著地抗爭著。
高欣
眉宇之間略帶幾分書卷氣的體院學生,工人家庭出身,崇高無私,機智果敢,見義勇為。他失手傷人,“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長認為他砸死的是“黑八類”的後代,無需承擔法律責任。但他卻主動投案自首,結果激怒了秦副局長,被判無期徒刑。在工地上,他眼見老罪犯馬玉麟勾結流氓頭子整治新犯人葛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馬玉麟
血債累累的老犯人,身材高大,兇相畢露,人面獸心。三十年前,他是血債累累的還鄉團頭子,而葛翎領導下的工作團鎮壓了他的父親、惡霸地主馬百壽。解放后,他因罪惡昭著被判無期徒刑。在黑白顛倒的歲月里,他竟成了監房的班長、專政機關依靠的對象。為報殺父之仇,他向章龍喜獻出殺害革命幹部的毒計。
路威
勞改農場場長,體魄強壯,鍛工出身,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多次立功,在戰場上與葛翎結下深厚友誼,複員后又一起轉業到省公安局。他為人光明磊落,嫉惡如仇,對葛翎、高欣倍加關懷。
章龍喜
五短身材,只有“三塊豆腐高”,是個在“文革”中造反有功的“刀筆小吏”,在秦副局長的卵翼下成了勞改農場的政委。他為人狡猾,刁鑽,凶狂,對葛翎百般刁難,唆使罪犯整治這位老幹部。
周莉
高欣的女朋友,體操運動員,為人單純善良,心靈像雪一樣潔白,熱情而聰明,對愛情忠貞不渝。正準備出國比賽的她千里迢迢來監獄探望高欣,完全不畏懼這樣的行為將為自己的前途帶來怎樣的影響。
泰副局長
在“文革”初期,靠血洗省公檢法單位起家的武鬥專家。他外表並不猙獰,嘴角總是帶著眯眯微笑,很像個文質彬的書生,但在武鬥場上卻以手黑出名,常常笑著把匕首戮進對方胸膛。他雖有秀才之相,卻不學無術,很少看書看報,但接受“中央首長”的指示卻一絲不苟。
主題思想
小說以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情節為框架,敘述了主人公葛翎在同林彪、“四人幫”一夥的倒行逆施英勇抗爭、血灑大牆的悲劇故事。雖然小說的情節充滿了悲劇色彩,然而,通篇小說卻洋溢著激奮、慷概、壯美的情調。這主要得益於作者在揭穿林彪、“四人幫”一夥及其爪牙製造冤獄、迫害人民的同時,著力反映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們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鬥爭。寒冬的大渠堤上,葛翎拖著疲憊、傷疼之軀,硬是將沉重的泥兜抬上了高坡,這個“寧叫扁擔折,不能腰弓曲”的烈火冶鍊的金子般的漢子,不僅獲得了良心未泯的勞改罪犯們真誠的歡呼,也深深震憾了讀者的心靈,使人們從中感受到了勇士的不屈不撓。高欣正氣慷然地將迫害葛翎、進行赤裸裸階級報復的流氓頭子從大堤上扔進渠底,充分顯示了正義的力量。而葛翎為了悼念周總理,不惜犧牲,鮮血染紅潔白玉蘭花的壯舉,更顯示了這名老共產黨員的強烈愛憎和鬥爭意志,也顯示了這名老共產黨員反抗邪惡的英勇氣概。作者在反映大牆內正義同邪惡英勇鬥爭的同時,也反映了人民在大牆外同邪惡的英勇鬥爭。勞改場場長路威無所畏懼地與“四人幫”的爪牙們進行面對面的鬥爭;體操運動員周莉冒著風險探監,向大牆之內的高欣獻上了純潔的愛情。雖然小說沒有正面描寫清明時節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怒斥“四人幫”的活動,但農場黨總支多數委員頂著“四人幫”爪牙的淫威,同意禁閉迫害葛翎的罪犯馬玉麟、俞大龍等情節,也顯示了大牆外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廣大革命人民同邪惡的鬥爭。大牆內外的這些鬥爭使讀者感受到,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浮雲終將遮不住太陽,“日蝕”一旦過去,大地一定還會沐浴著燦爛輝煌的陽光。
藝術特點
結構特點
小說貫穿作品的主線是以葛翎為中心展開的與馬玉麒、章龍喜、秦副局長等人的鬥爭,這條主線從時間上縱貫了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兩個不同的時代,通過葛翎與馬玉麒地位的掉換,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幫”的反革命本質和社會主義江山岌岌可危的現實,從而深化了主題。與主線緊密交織的副線是高欣與周莉的愛情。他們的愛情猶如冒著春寒怒放的報春花,給人們帶來春天的信息。作品通過周莉千里迢迢來農場探望高欣時帶來的一疊照片,巧妙地而自然地把大牆內的鬥爭與北京人民悼念總理的運動聯繫在一起,讓讀者感觸到時代脈搏的跳動。這條愛情線索從結構上突破了“大牆內”這個狹隘的空間,展示了一幅相當寬闊的時代畫面,使作品的思想顯得更加豐厚、深沉。
對比手法
作者在寫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時,採用了強烈對比的藝術手法。作品中的人物營壘分明地被排列成兩類。第一類人可稱為“社會中堅”,如葛翎、路威、高欣、周莉;第二類人是“社會渣滓”,如秦副局長、章龍喜、馬玉麟、俞大龍。在正面人物中,葛翎、路威代表老一代革命者,在他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熔爐中,幾經鍛煉,形成了對黨忠貞不渝的高貴品質。高欣和周莉代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在反面人物中,秦副局長、章龍喜是“四人幫”的幫派分子骨幹,馬玉麟、俞大龍是“四人幫”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在塑造人物時,小說仍是採用對比的藝術手法,把葛翎與馬玉麟、路威與章龍喜這兩對人物的外貌、經歷及其在獄中的言行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對比,從而使人物性格極為鮮明。
1981年,小說獲得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二等獎。
繼《大牆下的紅玉蘭》之後,從維熙、張賢亮等人創作了多部描寫“文革”時期發生的冤獄、反思歷史的文學作品,被文學界稱為“大牆文學”,《大牆下的紅玉蘭》更被視為“大牆文學”的發韌之作。
1979年,從維熙、梁劍華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在當年的《電影新作》第六期上發表。1980年,顧璧、王重義根據該小說改編繪製的同名連環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201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由肖德生改編、張紅年、王臨友、胡陽春繪製的同名連環畫
《大牆下的紅玉蘭》一經發表就引起讀者強烈反響,在半年中作者收到國內外讀者來信870多封,小說被譯成英、法、日、塞爾維亞等多種文字。小說在主流批評界則引發截然不同的評價。為此《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召開討論會交流意見。隨後,《文藝報》自1979年第7期起開闢專欄,對這部小說展開公開討論。在討論中,一派意見認為小說情節缺乏真實性,實質上是向人們散播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情緒;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該小說恢復和發揮了革命現實主義的傳統,也體現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而由於有人匿名致信《收穫》,將該小說比喻成“解凍文學”、索爾仁尼琴的同類,作者從維熙不得不親自撰文反駁。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原副主任顧驤:這部壯美的悲劇作品,之所以有著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首先因為它是真實的、可信的。作者堅持從生活出發,敢於面對現實……儘管人們可以對小說某些情節的合理性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問,然而,回顧大家共同經歷過的那一段噩夢般的歲月,人們是不會懷疑這個故事本質的真實性的……生活的真實性是這部小說的長處,而作品的某些不足的地方,問題也出在這裡。作品中的某些情節,缺乏濃厚的生活感。人物的塑造上反面形象寫得臉譜化了一些,沒能讓讀者更多窺視他們內心的深處……小說的前半部分寫得較細緻,後半部分似乎忙於交代情節,而放鬆了對人物性格的刻畫。

從維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