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5條詞條名為格非的結果 展開
- 牛奶咖啡組合成員
- 第四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委團成員
-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 中國男作家,代表作《格非文集》
- 北京格非視頻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格非
第四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委團成員
格非,男,出生於1964年,本名劉勇,江蘇鎮江丹徒人。1985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第四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委團成員。
格非2001年調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現為中文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委、主席團成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望春風》,中短篇小說《迷舟》《相遇》《隱身衣》,專著《文學的邀約》《雪隱鷺鷥》等等。中篇小說《隱身衣》獲2015年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獲2016年茅盾文學獎。
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6年發表處女作《追憶鳥攸先生》。格非在給自己作的小傳里曾寫道:“小說寫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給我帶來了一個獨來獨往的自由空間,並給我從現實及記憶中獲得的某種難以言傳的經驗提供了還原的可能。……在寫作中,歲月的流逝使我安寧。“足可見格非一直是今“純文學”的追求者,文學寫作並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於它構成精神超度的烏托邦。
1987年發表《迷舟》。這篇具有濃郁抒情風格的小說,因為故事的關鍵性部位出現空缺,而令人驚奇。傳統小說的“完整性”被這個“空缺”傾刻瓦解,十分寫實的敘事因為這個“空缺”而變得疑難重重。顯然,這個“空缺”來自博爾赫斯的影響,格非運用得頗為嫻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說具有謎一樣的氣質。格非並不多產,但他的小說一篇是一篇,頗值得讀解。《褐色鳥群》也許可以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最費解的一篇小說,
1988年發表時,華東師大中文系部分師生曾召開討論會對這篇小說展開多方研究,結果眾說紛紜。沒有人搞得清這篇小說到底在講些什麼,也沒有人否認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說。事實上,它始終誘惑各種讀者,從最激進的取業批評家到普通的文學愛好者。
2021年4月10日,第四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正式啟動,格非擔任評委團成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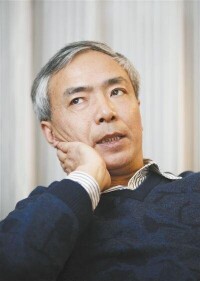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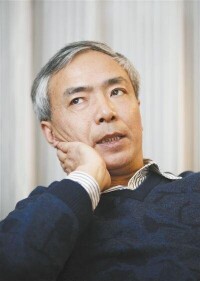
格非生活照
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雙獎得主。
2021年4月16日,憑藉作品《麥爾維爾讀札》,獲得第十七屆(2020年度)十月文學獎——散文獎。
他是個有學者風度的小說家。他喜歡在小說結構上做文章,他像營造迷宮一樣建構他的小說,以此獲得一種智力的樂趣。他的作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趣味,優雅、精緻而純粹,還有一種難得的矜持。他小說的詩性,更多的是來源於創造本身,而非社會人生。借鑒和引進在他那裡似乎是一種責任,或者說是一種命定的選擇。博爾赫斯、普魯斯特等西方大師在不同方面給了他不同程度的影響。
格非始終堅持用規範、純正的語言寫作,他立足於語詞本身的信息量,以繁複、深邃、多層面的敘述保證了意義的儲留,同時賦予文字以特殊的魅力。他的文字確切而細膩,豐滿而華美,這使他的作品宜於翻譯,信息的損耗可以降到最低限度。應該說,格非在文字的運用方式上汲取了西方文學的營養,他的這種文本意義上的實驗是必要的,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也許正是基於語言的特點,格非的敘述風格自有特色。在他的小說中我常發現:當情節停止或趨於停止的時刻,敘述卻在延宕不休,於是語言呈現懸浮狀態。對於讀者而言,一種閱讀的期待由此增強或者減弱了。這也是格非的作品常常不為一般讀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這使我想到新小說的某些寫法。我想,格非敘述上的特定意義恰在其敘述方式中,那就是讓讀者重視瞬間性的感受和思悟;它表明了一種獨特的觀念:瞬間即是永恆,永恆即是瞬間。
中短篇似乎是格非最拿手的,那些在文學圈子裡引起較大反響的作品差不多都出自中短篇,如《褐色鳥群》、《大年》、《迷舟》、《青黃》等。但我認為格非敘述上的秘密是在長篇中體現的。他的幾部長篇中,我最喜歡的是《邊緣》。這部作品是他語言風度的訓練,有一種唯美傾向。先於它的《敵人》則是結構上的實驗。在第三部長篇《慾望的旗幟》中,作者的目光轉向了現實,他以前所未有的興趣,描寫了自己最為熟悉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此後,他就更多地寫類似的現實題材。這一轉向,似乎從側面表明了他前期寫作中特別顯著的實驗性質。
他是個有學者風度的小說家。他喜歡在小說結構上做文章,他像營造迷宮一樣建構他的小說,以此獲得一種智力的樂趣。他的作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趣味,優雅、精緻而純粹,還有一種難得的矜持。他小說的詩性,更多的是來源於創造本身,而非社會人生。借鑒和引進在他那裡似乎是一種責任,或者說是一種命定的選擇。博爾赫斯、普魯斯特等西方大師在不同方面給了他不同程度的影響。
格非始終堅持用規範、純正的語言寫作,他立足於語詞本身的信息量,以繁複、深邃、多層面的敘述保證了意義的儲留,同時賦予文字以特殊的魅力。他的文字確切而細膩,豐滿而華美,這使他的作品宜於翻譯,信息的損耗可以降到最低限度。應該說,格非在文字的運用方式上汲取了西方文學的營養,他的這種文本意義上的實驗是必要的,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
也許正是基於語言的特點,格非的敘述風格自有特色。在他的小說中我常發現:當情節停止或趨於停止的時刻,敘述卻在延宕不休,於是語言呈現懸浮狀態。對於讀者而言,一種閱讀的期待由此增強或者減弱了。這也是格非的作品常常不為一般讀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這使我想到新小說的某些寫法。我想,格非敘述上的特定意義恰在其敘述方式中,那就是讓讀者重視瞬間性的感受和思悟;它表明了一種獨特的觀念:瞬間即是永恆,永恆即是瞬間。
中短篇似乎是格非最拿手的,那些在文學圈子裡引起較大反響的作品差不多都出自中短篇,如《褐色鳥群》、《大年》、《迷舟》、《青黃》等。但我認為格非敘述上的秘密是在長篇中體現的。他的幾部長篇中,我最喜歡的是《邊緣》。這部作品是他語言風度的訓練,有一種唯美傾向。先於它的《敵人》則是結構上的實驗。在第三部長篇《慾望的旗幟》中,作者的目光轉向了現實,他以前所未有的興趣,描寫了自己最為熟悉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此後,他就更多地寫類似的現實題材。這一轉向,似乎從側面表明了他前期寫作中特別顯著的實驗性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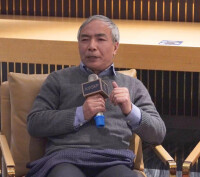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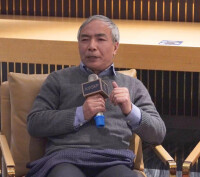
格非
我國古典文學傳統,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顯然還沒被中國人認識到。張愛玲曾經說過:“幾十年後中國可能沒人能讀得懂紅樓夢。而依我看,現在就連一些學者也讀不懂《紅樓夢》。當代寫作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昨天下午,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作客“城市文學講壇”,以當代小說的處境開始了他帶有思辨色彩的演講。
“西方中心論”思想作祟
格非說,幾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國南部一個小村莊,專心寫作《人面桃花》。那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小村莊,但令格非驚訝的是,那裡的農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國家的文化,絕大多數農民對福樓拜、普魯斯特等本土小說家的經典文學作品格外熟稔,津津樂道。格非非常羨慕這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他說“相比之下,我國古典文學傳統,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顯然還沒被中國人認識到。張愛玲曾經說過:‘幾十年後中國可能沒人能讀得懂紅樓夢。’這位有才氣的女作家,讀過很多西方作品,被問到最喜歡哪一部時,說的還是中國小說好看,《紅樓夢》最好看。而依我看,現在就連一些學者也讀不懂《紅樓夢》。”格非說,自己也是到30歲才知道中國的傳統小說的好,開始猛補。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推崇。他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主張向西方文化看齊,“西方中心論”的思想現在仍在許多小說家的頭腦中作祟,他們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視野,進入真正“中國化”的寫作。古典小說值得終生體味。
雖然自己被媒體稱為“先鋒派作家”,但格非對此並不太在意。在演講中,他一再強調,好的小說家一要精通現實、二要精通“魔法”,還有就是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對傳統文化作出回應甚至推進。格非說,西方小說在故事和場景的關係上,常常是停下敘事,描繪場景,比如《巴黎聖母院》停下來描寫環境,但是這個敘事中斷的問題在中國的小說藝術中很早就被解決了。《紅樓夢》的故事完全沒有中斷,而大觀園已經通過元妃省親、劉姥姥的登場出現了。還有,西方小說的結構基本是開始——發生——高潮——結束,而中國人比較重視內心感受到的時間。比如《世說新語》里,一個人看到自己種的樹,長得很大很粗壯了,淚流滿面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這裡強調的就是一種內在的時間,感嘆時間流逝,體現悲憫情懷。格非形象地比喻,西方小說里,蝴蝶飛啊飛,最後一定會落在一隻白手套上;中國的小說里的蝴蝶最後一定會落在草叢裡。格非感慨地說:“中國古典小說的高明與偉大之處是值得我們終生體味的,這些傳統才應該成為我們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
民間文學不能狹窄化
格非說,文學不管表現什麼題材,它本身總是指向人的處境,這一點是不會變的。現在的民間文學存在很大問題,好像一提民間、一提底層就是好,寫知識分子就不好,這其實是把寫作狹窄化。魯迅寫《故鄉》這樣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寫鄉土的,可是魯迅是以知識分子的眼光去看待農村的變化。現在很多人只不過是把農村、民間當做題材來寫,致使有一部分描述鄉土的文學已經變成一種空洞的東西。任何一種基於社會現實的寫作,都需要通過作家個人的經驗才能產生,作家不可能只是一個農民的代言人。
貴在開風氣或挽救風氣
格非說,歷史上所有偉大的作家,在文學史上留得下來的作家,無非兩種,一是開風氣之先,二是挽救風氣。沒有狂放之氣,談何中庸之道?最後只能成為老好人,成不了好作家。格非說,現在有些人過於聰明了,比如做出版的,天天在書店裡買進自己出版的書,每天買200本,把自己做的書買成“暢銷書”,這跟做股票莊家吃進好有一比。等到大家都注意到這本“暢銷書”,都去買了,發行量上到幾萬幾十萬本;他再把自己買的書賣出去,或者打進成本。中國現在正處於一個巨大轉折的時期,為什麼沒有出狄更斯、司湯達這樣反映社會深刻變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現了這樣的一些所謂“文化人”,真是值得深思。

格非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