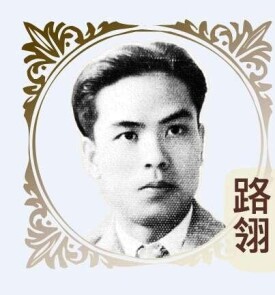路翎
作家,代表作《財主底兒女們》
路翎(1923-1994),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原籍安徽省無為縣,生於江蘇蘇州。原名徐嗣興。漢族。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
1937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品有《家》《祖父的職業》《何紹德被捕了》等。
兩歲時徐家遷至南京。在路翎二歲時,父親趙振寰因故自殺身亡,不久徐氏舉家遷南京,其母改嫁。
1935年入江蘇省立江寧中學。
1937年冬天,隨家入川,就讀於國立四川中學,但因思想左傾,在高中二年級時,被學校開除。
1940年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治研究所職員、煤焦辦事處職員,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講師。
1950年初調到北京任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副組長
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編審。

路翎(中)
17歲時以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一個青年經紀人底遭遇》受胡風賞識而於文壇初露頭角,自此成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
1938年,寫了一首長詩《媽媽的苦難》,向胡風主編的《七月》投稿,沒有發表,但他得到了胡風的鼓勵。
1939年,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之後》被胡風采用。發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叢》。這時用“路翎”作筆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筆名,是為了紀念初戀對象李露玲。)
1940年之後曾在礦區生活工作,因此創作了《家》《祖父的職業》《何紹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礦區生活的作品。
1942年4月寫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1944年發表《飢餓的郭素娥》。
1945年發表《財主底兒女們》表現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心路。
1949年7月寫出反映工人護廠鬥爭的劇本《人民萬歲》,11月完成《女工趙梅英》。
后創作《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劇本。
1951年發表的劇本《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也未得到公演機會,還不時遭到批評,被扣上“明目張膽地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的帽子。在此期間,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和《平原》。
1953年後發表了反映中國人民志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得到大量讀者好評,卻繼續遭到中共作家的批判。
1954年出版散文集《板門店前線散記》,5月起全國幾大報刊紛紛發表批評文章,針對《窪地上的“戰役”》中描寫志願軍戰士談戀愛違反軍紀等,扣上“個人主義”、“溫情主義”、“悲觀主義”等帽子。
1954年上半年撰寫《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后以“三十萬言書”著稱),同年11月,不滿於一些批評家“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又寫出四萬餘言的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
本來還寫了一部長篇《戰爭,為了和平》未發表。
1980年後曾逐步恢復了一些文學才能,重新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華橫溢的路翎了。
著有《羅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蝸牛在荊棘上》《燃燒的荒地》《王貴與李香香》《朱桂花的故事》《祖國在前進》等。
1944年8月15日與電台報務員餘明英結婚。
1994年2月12日在客廳中突然摔倒,因腦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作品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后,出任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
1949年後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組長,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專業作家。
1952年9月《文藝報》加編者按發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蕪反戈一擊《致路翎的公開信》,直指路翎屬於“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遭而馳的”。1952年12月,路翎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體驗生活,
1953年7月回國,9-10月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併當選為作協理事,
1955年6月19日被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抄家和逮捕。
1965年保釋出獄。但在保釋的一年內路翎寫了三十餘封上訴信,結果被以書寫反動信件的罪名再抓起來。路翎感到絕望,精神從此變得失常。
1975年出獄。參加勞改,發配在街道掃馬路。把自己很少的錢都拿來買酒喝。什麼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讓他上街買醬油,他買回來的還是酒,酒精也損害了他的大腦,已經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路翎無罪。
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四屆理事。
批評指責
中共主流文藝批評家對路翎的創作天才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們認為,路翎的創作走上了邪路。他們的批評與指責主要表現在兩點。
一是認為路翎筆下的人物不真實。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認為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那樣複雜的心情,認為路翎硬把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裝到了工人農民心裡去。胡繩對路翎小說的心理描寫特色作出了這樣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一方面為自己心情上的複雜的矛盾而苦惱,另一方面,卻又沾沾自喜,溺愛著自己的這種微妙而纖細的心理,以為憑這點,正足以傲視於一切市儈。”
二是批評路翎小說主題。胡繩對路翎小說的主題有這樣的批評:“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人民大眾從被壓迫生活中的覺醒與可能覺醒中,卻反而想去從人民中找什麼‘原始的強力’,他們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覺醒的人民的集體鬥爭中,卻片面地著重了‘個性解放’的問題。”胡繩認為:“作者多追求著的‘人民的原始的強力,個性的積極解放’是和為了不使自己為生活‘壓潰’,而從生活中‘飛’起來的要求相聯結的,表面上是要‘強’,要‘解放’,實際上卻是想超脫現實生活逃避現實的鬥爭。”
在40年代末已經形成了新的文學規範,即要求文學表現人民群眾,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反映階級鬥爭生活,在這種文學規範的對照下,中共主流批評家批評路翎醜化了人民,提倡的是個人主義,讚揚的是個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學的要求的。
社會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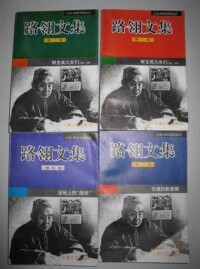
路翎作品集
《路翎小說選》的編者朱珩青所這樣評價路翎的小說:“這小說是別一種聲音。”路翎的小說不同於現代文學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於殘酷的靈魂的拷問與“歇斯底里”的變態情緒,常使讀者痛苦不已,進而“廢書不觀”。
我們讀路翎的小說,會發現他筆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點神經質,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穩定的,甚至都有點瘋狂與變態。
路翎說他“不喜歡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寫”,並說他筆下的“自發性的反抗與自發的痙攣性(即使是潛伏的意識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它是可寶貴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壓下,更是這樣的”。當人們責備作者主題思想“不健康”,認為中國人民是沒有這些的時候,他肯定地回答說:“我認為是有這些的。”胡風在與路翎的談話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視這種心理描寫與內心劇烈糾葛的揭露的,不重視這種狂熱熱情的,人們是理智的。”
路翎曾這樣解釋自己這樣寫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尋求而且寶貴”著“在重壓下帶著所謂歇斯底里的痙攣、心臟抽搐的思想與精神的反抗、渴望未來的萌芽”。他不再滿足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博大悲憫,而“竭力擾動,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路翎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對於人的靈魂的探尋中去,使得長久以來埋藏在人們靈魂深處的情感與理性衝突的火花得以閃現出來,豐富了現代文學對於人(尤其是下層勞動者)的心靈世界的描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強度”。
路翎筆下的人物都帶有一種強烈的浮雕感,線條粗獷、動作僵硬,缺乏現實人物的纖巧、靈敏與情味。每個人在生存的苦難中都表現出“拉奧孔”式的痛苦、絕望與瘋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劇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種樂觀的力量,即使在最陰暗的情境中,也騰躍著一種征服的激情與豪邁。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現實人生中的失敗者,但面對現實人生的絕望,他們又無一不是為“理想”而戰的鬥士,他們“也許是負擔了在別人看來是失敗的結果,可是戰鬥即勝利”這種“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們身上以各種形態體現出來,表達了路翎反抗絕望的姿態。
主題的“瘋癲”與敘述的“瘋癲”在路翎的小說中是一致的,換句話說,路翎是用敘述的“瘋癲”在表現主題的“瘋癲”。
路翎把一切詩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說,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語法的邊緣無節制地膨脹。路翎的語言有些冗長與繁瑣,我們在這裡看出作者寫作時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說不是那種以飄然的態度寫出來的東西。 路翎的語言還有一種焦灼感與蕪雜感。在路翎的小說中,個體生命的爭鬥不僅停留在外在的行動中,同時靈魂的深處亦有血淋淋的謀殺與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間的是緊張的激情與衝突。衝突蘊藏在每一個瞬間。由衝突而危機進而情感迸發,這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內,人物行為大起大落,情緒跌宕起伏,造成人物關係和場面的極度緊張。路翎特別擅長描寫人物的瞬間心理和瞬間心理的變化,追求人物心理變化的幅度、速度和強度。比如在《燃燒的荒地》中,郭子龍先是公開宣稱要向地主吳順廣復仇,但過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吳順廣的幫凶。有一次他到寺廟裡,非常虔誠地想當和尚,但忽然又轉到惡意的嘲弄和尚。這種心理的巨大轉折被路翎寫得絲絲入扣。
路翎的語言還有一種焦灼感與蕪雜感。在路翎的小說中,個體生命的爭鬥不僅停留在外在的行動中,同時靈魂的深處亦有血淋淋的謀殺與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間的是緊張的激情與衝突。衝突蘊藏在每一個瞬間。由衝突而危機進而情感迸發,這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內,人物行為大起大落,情緒跌宕起伏,造成人物關係和場面的極度緊張。路翎特別擅長描寫人物的瞬間心理和瞬間心理的變化,追求人物心理變化的幅度、速度和強度。比如在《燃燒的荒地》中,郭子龍先是公開宣稱要向地主吳順廣復仇,但過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吳順廣的幫凶。有一次他到寺廟裡,非常虔誠地想當和尚,但忽然又轉到惡意的嘲弄和尚。這種心理的巨大轉折被路翎寫得絲絲入扣。

路翎作品封面
路翎似乎急切地尋求著最富表現力的表達方式。但語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觀世界面前總顯出無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無力用語言將自我心中的感觸精確完美充分地表達,於是焦灼、反抗,當進入一種迷狂的狀態中時,語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挾著珍珠與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勢傾瀉而下。激情掩蓋了無能,蕪雜代替了精確,從中我們體味到現實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無際無涯,但另一方面,難以把握的困惑也隨之而來。人們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種情緒、意象,因為在你把握了一種之後,必然會在同一部作品中發現與之相矛盾的同體異質。這是一種最大限度的原生態,是超乎於批判現實主義典型觀的一種藝術美學。它是由路翎內在的藝術氣質決定的。
路翎的小說語言不像蕭紅的《呼蘭河傳》那樣抒情而感傷,他似乎不是用筆在描寫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滿身血痕。冗長的句子是鞭子的長度,貶義的詞句是鞭子上的毒刺。
路翎追求的是粗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蕩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創作中是提倡戰鬥的熱情的,他說:“萬物靜觀皆自得,我們不要,因為它殺死了戰鬥的熱情。將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來,我們不能要,因為它毀滅了複雜的戰鬥熱情,因此也就毀滅了我們底藝術方法里的戰鬥性。”在他的筆下,京派作家那種明心見性的靜觀的審美態度,以及沖淡、明凈、節制、圓潤的筆情墨韻,已經蕩然無存。他犧牲了藝術上的空靈和精緻,換取了獷野雄放,元氣淋漓。正如胡風所說:
從這裡也就產生了他底創作方法上的特點。他不能用只夠現出故事經過的繡像畫的線條,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徵底神氣透出的炭畫的線條,而是追求油畫式的,複雜的色彩和複雜的線條融合在一起的,能夠表現出每一條筋肉底表情,每一個動作底潛力的深度和立體。
李健吾這樣形容路翎的風格:
路翎先生讓我感到他有一股衝勁兒,長江大河,漩著白浪,可也帶著泥沙……他有一股拙勁兒,但是,拙不妨害沖,有時候這兩股力量合成一個,形成一個高大氣勢,在我們的心頭盤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有青年給路翎寫信,信中這樣說:“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熱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擁抱力,驚人地震撼了求進步的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