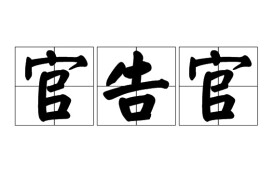官告官
官員相互指責併發生糾紛的行為
官告官是指政府官員之間相互指責,乃至於發生法律糾紛的行為。對應的類似辭彙有,民告官、官告民、民告民,等等。
深圳一名法院庭長指當地國土委員裝修為名違法施工,致其所居住別墅受損,並搭設違建,影響其父所居別墅採光。並將該國土委員告上法庭,兩官員互指名下別墅系非法所得,這就是中國式官告官的起源。
看來官告官也不失為打擊腐敗的一個好辦法,只是俗話說“官官相護”,這種依靠官員間相互舉報來懲治貪官的還不是非常普遍
別墅來源問題
“我是法官,豈非就不能維權了嗎?從明日開端,我就是曠工,也要跟他們奮鬥究竟。”5月25日,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賈宇心情衝動,她指稱深圳市規劃和疆土資本委員會副局級幹部、原征地辦主任劉新雲及其老婆趙海燕以裝修為名,對其的奢華別墅進行外擴下挖、改建、加建、大搞違章修建,嚴重危及到相鄰的她父親別墅的平安。並稱劉新雲還應用其指導幹部權柄,動用各類關係攪擾執法。
官告官的訴訟很頭疼
5月25日下午,龍崗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賈宇稱,她的父親賈秋建及鄰人王艷敏辨別是龍崗區橫崗街道振業城項目一期E組團3棟B座、C座業主,於2006年正式入住。E組團3棟屬於別墅區,深圳市規劃和疆土資本委員會副局級幹部、原征地辦主任劉新雲及其老婆趙海燕購置了A座,成為了兩人的鄰人。

官告官
賈宇稱,劉新雲伉儷還大搞違建,在A座和B座相連的進口處加建樓板,嚴重影響了她父親房子的採光和通風。他們還在花圃曠地內私自加建一棟兩層樓的修建物,改動房子原構造,影響了E組團全體外觀。
該別墅是開拓商送的
賈宇以為,劉新雲、趙海燕外擴下挖、改建、加建的修建物屬於違法修建,且已嚴重影響相連房子的構造平安,已直接招致相鄰房子呈現嚴重質量問題以及房子價值貶損,依法應予以查處,責令答覆原狀。1月29日,她和王艷敏辨別緻電龍崗區橫崗街道執法隊,投訴劉新雲伉儷的違法行為,要求予以制止及恢恢復狀等。當天,執法隊相關任務人員抵達現場進行查詢取證,並下達書面整改告訴書,要求劉趙兩人限日撤除違法修建。這以後,兩人撤除其在花圃曠地內加建的一棟兩層樓修建物,但對恢復A座房子原狀以及形成相鄰房子質量及平安損害未置一詞。
賈宇稱,還有人向她反映,劉新雲、趙海燕伉儷購置這棟別墅,應用了劉新雲的指導幹部權柄,是開拓商半買半送。他們2005年前後就購置了房子,但不斷不敢公開裝修,也不敢入住,直到劉新雲上一年10月份退休,他們才開端裝修房子,讓奢華別墅空置了5年多。
被投訴官員否認獲贈別墅
25日下午,記者來到龍崗區橫崗街道振業城項目一期E組團3棟,劉新雲向記者供認他們的確有差錯,也的確給鄰人房子形成了損害,他們情願承當責任。但劉新雲果斷否認本人應用權柄免費獲贈別墅,甚至攪擾職能部門執法。
趙海燕分析,她之前是某大型企業技術部的黨支部書記,曾經工資很高,年薪達幾十萬元,買別墅的首付主要由她出,還用了銀行按揭借款。在別墅改擴建,他們的確有差錯,但賈宇仗著本人的法院庭長身份,揚言挖了牆角,影響了她家的風水,要求他們支付100萬元的風水費。
趙海燕還指稱,賈宇有多處房產,這處別墅雖然在她父親名下,但實踐上也是由她個人出資購置,當前也不斷供她個人運用。
賈宇回應說,她從1991年進入深圳任務,個人收入超越200萬元以上,她完全買得起別墅和房產。她自己清潔白白做人,沒有收受當事人一分錢。

官告官
官司的來由得從當年7月20日的“普魯士政變”(Preussenschlag)說起。1932年春夏之交,德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4月24日普魯士邦議會(Prussian Landtag)大選中,執政的“普魯士聯盟”(由社會民主黨、天主教中央黨和民主黨聯合而成)在423個議席中總共只得到163席,而極右翼新貴納粹黨在贏得162個議席之後,已經成為了普魯士第一大黨。由於組建新政府、正式上台執政需要在議會中佔據半數以上席位,而納粹黨既不願和德共(57席)聯手,也不肯和普魯士聯盟妥協,這就使得新政府遲遲無法產生。在此情況下,邦總理布勞恩只得援引魏瑪憲法第59條的規定,宣布由已經在選舉中失利的三黨聯盟組成看守內閣、繼續代行政務,直至新政府正式組成。
問題在於,普魯士邦乃是全德的政治重心,該邦大選的結果絕非單純的地方事務,同樣與聯邦政府的態度緊密相關。而此時在柏林執政的弗朗茨·巴本(Franz von Papen)內閣,卻是一個形式上超然於政黨之外、實質上又與政黨紛爭脫不開關聯的怪胎——自兩年前社民黨總理米勒因為經濟危機自行辭職之後,總統興登堡便拒絕再根據混亂的國會選舉結果來任命總理,他動用了憲法第48條賦予總統的“緊急專政權”(Diktaturgewalt),先後委任中央黨人布呂寧和巴本繼任總理。在此期間,中間偏左的社民黨依然是聯邦國會中的頭號黨團(577席中佔143席),他們頻頻出擊,否決政府的大政方針。巴本這個總理雖然得到總統的支持,在國會卻是個“跛腳”,迫切需要得到國會第二大黨納粹黨(107席)的支持。為了和納粹達成妥協,在聯邦議會中真正確立政府的權威,巴本想出了一個交換方案:中央黨在普魯士邦新議會中擁有67個席位,假如該黨脫離普魯士聯盟、與納粹黨聯合,再加上親納粹的民族人民黨(31席),就可以在423個議席中佔據260席,組成一個以納粹黨為主體的普魯士邦新政府。作為交換,納粹黨在聯邦議會中也與中央黨(67席)、民族人民黨(41席)聯手,對抗社民黨的力量。這樣,傳統上在聯邦議會和普魯士邦議會都佔優勢的社民黨、中央黨、民主黨三黨聯盟就由這個新的三黨聯盟取代,巴本總不會吃虧。
在這個交換計劃里,社會民主黨是唯一的犧牲品。該黨雖然執政業績一塌糊塗,但畢竟是魏瑪共和國歷史最久、影響力最大的政黨,得到大部分中間派選民的支持。為了抵制巴本的陰謀、並在7月底的聯邦議會選舉中重奪主動權,社民黨決定首先在普魯士邦發起反擊。“代行政務”的看守內閣先是把一大批社民黨人硬塞進邦政府和過去不帶黨派色彩的公務員隊伍,接著又公開宣布普魯士邦警察(歸屬邦內政部管轄)將優先專註於本邦內部的事務,拒絕無條件履行聯邦政府的某些政令。“內政部”大約相當於我國的公安部,一個省的公安廳居然宣稱自己可以“有選擇”地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偏偏這個省還有足足9萬多警察,豈不是要造反?巴本一看狀況不妙,馬上反擊:7月17日,普魯士邦的納粹黨衝鋒隊和共產黨工人武裝在阿爾托納發生槍戰,聯邦政府宣布:普魯士邦看守內閣已經喪失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控制。三天之後,7月20日上午10點,興登堡總統再度動用緊急專政權,宣布中止普魯士邦國務部的一切職能,由聯邦政府直接管理該邦一切事務,並委任巴本總理為普魯士邦“國家專員”(Reichskommissar)。巴本帶著聯邦內政部長蓋爾等一干人趕到布勞恩那裡,宣稱:如若不從,就要動用軍隊。布勞恩倒想抵抗一番,但社民黨執委會作出了交權、避免流血的決定。此後普魯士邦由“國家專員”直轄了半年才恢復自運作。而1932年秋天這起“官告官”案件的核心問題,就是聯邦政府中止布勞恩內閣的運作有沒有合法性。
魏瑪憲法第19條規定,只有在涉及一個邦與國家的訴訟時,才能由共和國出庭。而1932年這起案件中,布勞恩及其部長雖然已被解職,卻依然使用普魯士邦國務部的名義、以該邦政府的代表身份自居。他們是合法的訴訟主體,中央黨和社民黨議會黨團則不是。而在遭受控告的共和國名義下,顯然還包括那個已經由總統授權、成為普魯士邦全權者的“國家專員”。那麼,到底有幾個普魯士邦呢?倘若進一步追問下去,則已經在選舉中失利、只是代行政務的布勞恩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正當性宣布其警察拒絕履行聯邦政令?而擁有緊急專政權的興登堡總統,又是否可以對作為聯邦自身一部分的普魯士邦行使這種具備“例外”(Ausnahmezustand)性質的權力呢?著實亂得很。

官告官
1919年的魏瑪憲法保留的只是第二帝國的聯邦制組織結構,共和國政府既不打算讓各國繼續保有獨立的國家性質,也不打算要一個事實上的“聯邦國家”。各邦的存在與其說是一個政治決定,還不如說是出於習慣和行政上的方便。普魯士邦代理政府在“官告官”案件中的誤差,就在於從字面而不是實際的政治權勢上理解了“聯邦”的定義。布勞恩政府(乃至其身後的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一方面大力彰顯普魯士邦獨立的國家性,企圖和共和國(以及作為其全權代表的興登堡總統)“分享”事實上的全權;另一方面,他們打的卻又是聯邦主義的旗號。
“國家”與“聯邦”聯手,逼得處於守勢的共和國總統拿出緊急狀態權這個殺手鐧——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聯邦大總統對於聯邦中某一邦,如不盡其依照聯邦憲法或聯邦法律所規定之義務時,得用兵力強制之”,不用和國會商量。他選的也正好是普魯士邦政府的命門:對於“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是否遭到破壞這種典型的例外狀態,在任一主權國家的範圍內只能有一個裁斷者。介入的權威(auctoritatis interpositio)出了手,布勞恩只好早早跑路,遠赴萊比錫去告狀。 1932年10月17日,施米特在憲法法院代表共和國政府做最後陳辭時嚴正指出:“普魯士的確有其榮譽和尊嚴,可是在今天,這種榮譽的受託管理者和捍衛者乃是共和國。”不過在25日,法院還是判決“普魯士政變”違憲,理由是根據魏瑪憲法第17條第2款,“各邦政府應得人民代表之信任”,共和國方面不可撤銷、更不可任命一個邦政府。社會民主黨的羊群自以為趕走了牧羊人便可天下大吉,哪知隨後就來了一頭狼——1933年1月30日,由於社民黨和中央黨還在想著分權,拒絕接受總理施萊歇爾將軍(他也是總統以緊急專政權任命的)提出的推遲國會選舉、以武力鎮壓議會第一大黨納粹黨的建議,橫下一條心的興登堡只好直接授權希特勒這個“得人民代表之信任”的撒旦組閣。希特勒上台後馬上投桃報李,以一部《國家專員法》拔除了所有各邦的議會制:誰也別爭了。在二戰后制定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波恩憲法)中,雖則“聯邦國家”變成了既定的事實,但布勞恩一干人當初在“官告官”案子中反對的“違憲行為”,卻以“聯邦強制”(Bundeszwang)的名義載入了正式法條。所以說官告官,形式上是法,實質上卻是權。“權”的問題之所以沒法以“法”的形式解決,就在於任何“法”都需要主體的介入才能得施行,而主體一介入就引致權力,而且還得是全權,否則無法前進。還是施米特說的好啊:“既然憲法是一種政治性的東西,因而憲法法院還需要基本的政治決斷。”
評價
法律糾紛的實體可以是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主體,因此,從法律角度看,沒有新穎性。但是實體的社會身份的差異,往往會吸引社會輿論的關注。而社會輿論的關注,又往往對法制化進程、廉政化進程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