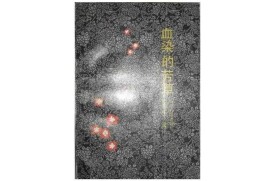血染的芳草
血染的芳草
長篇小說《血染的芳草》是在中外文學家如孫犁、趙樹理、福樓拜等的基礎上的繼承與革新,是一部具有很高藝術價值、很值得深深細品的作品。《血染的芳草》是一部典型的成長主題小說。作者在小說中生動地描寫了蓮蓮、馬嫂、珠珠、滿滿等一大批女性形象,著力表現了蓮蓮不斷感悟、不斷進步、不斷成長的精神狀態,展現了主人公蓮蓮從幼稚走向成熟、從一個弱女子成長為一名革命英雄的變化過程,形成了小說文本自足的精神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不僅有革命女性在苦難中的精神成長史,而且也歌頌了民間社會的生之力,同時也折射了一個民族在血與火的淬礪中所迸發出來的韌性與活力。
《血染的芳草》
作者:崔復生
出版社:中原農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2-03
印刷時間:1992-03-00
印數:5千冊
裝訂:

血染的芳草
1979年曾被評為安陽行署勞動模範。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
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太行志》、《血染的芳草》,長篇報告文學《對起百姓》等。《血染的芳草》獲河南省政府第二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1996年河南廣播文藝一等獎,短篇小說《楊家父子》獲安陽、新加坡聯合徵文特別獎。1993年4月河南省作協等省內外單位評論家及作家在林州舉行了"芳草"研討會,對作品給予充分肯定,發表評論文章10餘篇,被載入《新聞出版1993年鑒》、《河南文化年鑒》。至今共發表短篇文學作品200餘篇。
榮譽《血染的芳草》獲河南省政府第二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河南省廣播文藝一等獎,
《不忘英雄》獲河南省“五四”文學獎銀獎,
短篇小說《楊家父子》獲安陽、新加坡聯合徵文特別獎
縱觀崔復生先生的長篇小說《血染的芳草》,可以說是一部優秀的表現太行山兒女抗戰史。關於該作品的評論在過去並不少見,但大多都是隨感式的評論,很少有系統而深入的探討和分析,這對探求該作的藝術價值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在此,試從作品中內容和表現方法的角度談談一些看法。崔復生先生的長篇小說《血染的芳草》是在中外文學家如孫犁、趙樹理、福樓拜等的基礎上的繼承與革新,是一部具有很高藝術價值、很值得深深細品的作品。這部歷時十年誕生出的力作應該歸於現實型文學,作品向我們展示了抗戰時期太行山兒女們的生活及鬥爭畫卷,其中的對於風俗、民俗、語言的描寫對於我們的民俗學與考查、對比語言學的研究也是極有幫助的。同時,小說中的藝術形象蓮蓮集真、善、美於一身,鮮明體現了作者對藝術真實的價值追求,蓮連形象的典型性是與她所處的時代環境是緊緊相連的,作品向我們展示的不僅是個人的成長曆程,還有當時大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創作是離不開時代背景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有它一定時代的映射……
創作中的創作方向要與個人興趣相一致。
寫作是有技巧在裡面的,要練就一雙慧眼,積累素材,濃縮語言……
寫作是痛苦的過程,也是幸福的過程。
一位稱職的作家,寫出的作品是具有時代感的,他必定能夠觀察、願意觀察、觀察到位,看到許多深層次的東西。
文學作品的類型包括現實型、理想型和象徵型三種。崔復生的長篇小說《血染的芳草》應該歸屬於現實型文學,即我們在文學史上熟悉的“寫實文學”,是一種側重以寫實的方式再現客觀現實的文學形態。《血染的芳草》體現出了現實型文學的兩個基本特徵:再現性和逼真性。
(一)、“誠實的鏡子”:再現性 所謂再現,是指對外在客觀現實狀況作如實刻畫或模擬。它要求文學立足於客觀現實,面對現實,正視現實,並忠實於現實生活,而不是繞開現實,躲避現實。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重要的藝術始終高度忠實於現實,······藝術不僅永遠忠於現實,而且不可能不忠於當代現實。”崔復生的《血染的芳草》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就是在對客觀現實的冷靜觀察和理智分析上直接揭示現實矛盾,觸及人物內心的。雖然小說中所敘述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是真人真事的寫照,但它所集中反映出來的卻是在那個動亂又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的代表,如我們所皆知的紅色娘子軍等,都在蓮蓮身上或多或少有所體現。《血染的芳草》就如同一面時代的鏡子,鮮明直觀地再現出那個年代英勇壯烈的抗戰事實。崔復生在創作中嚴格地遵循了實事求是的態度,但又在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對歷史事實加工改造。正如郭沫若先生堅持的歷史劇創作原則:失事求似(“求似”就是歷史精神的相對真實準確性,“失事”是在不違背歷史基本真實的前提下,對歷史進行創造性的虛構和加工。),而沒有在作品中主觀隨意捏造。作品中所塑造出來的蓮蓮、馬嫂、珠珠等女性形象,並不是作者超時空的、理想化的形象,而是真真切切存在於特定時代社會的具體環境中,主人公身上的性格體現出了非常具體、確定的社會內容,人物的主要活動也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範圍內進行的,而沒有模糊越離。作為現實型文學作品,《血染的芳草》中也同時體現出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情感評價。崔復生把他對那個戰火紛飛年代的主觀情感態度融匯在了戰亂年代環境的再現之中,也滲透在了情節、場面、人物的描繪刻畫之中。崔復生沒有直接出面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的主觀傾向,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崔復生是受到了福樓拜的寫作風格影響。福樓拜一直堅持客觀冷靜的敘事,他說:“藝術家不應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該在生活里露面一樣”。在整部小說的創作中,作者始終是冷靜的敘述,他沒有對作品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發表言論,加以評判,他就是那樣,把活生生的客觀現實突出出來,把自己感受過的現實生活再現在作品中,呈現給讀者,讓讀者獨自去完成下面的體驗,比如在道德上的頓悟,理性的思考,心靈的凈化,情感的共鳴,思想的提升,情操的陶冶以及讀者自己對歷史事件的情感把握與評價,而不是直接地把他自己的感受和態度告訴給讀者。
“熟悉的陌生人”:逼真性
現實型文學立足於客觀現實,再現現實矛盾和本質規律,在藝術表現手段上的基本特點就是逼真性。在《血染的芳草》中,崔復生即是以寫實的手法,按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本來面目進行精細逼真的描繪。比如作者對蓮蓮的肖像採用了白描的手法:“十八歲,肩不寬,一件合體的印花布衫,一雙五色絲線綉成的繡花鞋。微微透紅的臉兒很乾凈,一蓬劉海在耳邊撲散著”,寥寥幾筆,粗中有細,細中透粗,為我們勾勒出了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這無疑大大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給我們如臨其境、如見其人之感。巴爾扎克認為:“小說在細節上不是真實的話,它就毫無足取了。”崔復生對蓮蓮在窯洞院子中盼谷生回來的那種坐卧不安、魂不守舍,焦灼、急切的細節描寫,把活脫脫一個不諳世事、純潔無瑕的少婦形象精緻的表現了出來,以及她拿著谷生衣服泄怨時的舉動,給讀者展現出了盼望夫妻二人幸福生活的山村少婦形象。這是蓮蓮人性的表現,是一個普通的山村少婦對新婚生活的希冀,這些都是生活畫面的真實再現,不誇張不變形,初期的蓮蓮儼然一個小女人形象躍然紙上。這些都是崔復生從現實生活實際出發,描寫的是現實生活里本來就有就會發生的事件,主人公原型是作者從社會生活中汲取而來的創作材料,同時表現的也是作者自己真切的現實感受。在《血染的芳草》中出現的,幾乎都是現實社會中的人情世態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命運,而非虛幻離奇的神仙妖怪和超凡脫俗的英雄豪傑。馬嫂,她一個人承受著柱兒犧牲的凶信,獨自承擔喪失親人的悲痛,在公婆面前強顏歡笑,百般孝順,不忍把凶信告訴二老而寧願二老錯怪自己;又日夜不停地操勞,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參加抗戰,智除漢奸。這並不是傳統抗戰題材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在真實抗戰時代里確實存在的。作者依賴於客觀現實來進行人物塑造,這就使我們感覺到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真實性,更易引起我們的共鳴。同時,小說體現了崔復生對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對真、善、美的追求。 “真實性”是衡量文學創造的首要標準。整部作品所構建的情節與人物,都給人一種真實感。因為作品所依賴的大時代背景是真切存在的,而讀者對於大時代背景也都是了解的,所以讀者在閱讀《血染的芳草》的過程中並不覺得做作、虛假,而是踏實而真誠。在整部作品中,主人公蓮蓮、馬嫂、珠珠、滿滿等,就連那隱形的形象如谷生、柱兒,無不給人以一種美感,這種美不是外在的相貌、衣著,而是他們所代表的那種為了新生活,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國家的利益,勇往直前、不畏犧牲的崇高戰鬥精神,這種精神給予我們鼓舞,深思與震撼,這樣的美才是永不褪色的美,就如那涓涓細流,永遠不停地流淌在我們心中給予滋潤;又如那不絕於耳的鐘鳴,時時給予我們警醒,讓我們不會忘掉現今的幸福是由先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而這種美進一步升華為讀者的覺悟,這也是小說的獨特之處,精妙之處。作品中所有呈現的“真”與“美”把讀者引向一個向“善”的世界,從而可以起到規範讀者行為的作用。由這也可以看到作家崔復生的高尚品格,俗語說“人品決定文品”、“文如其人”,就是這個道理。作品的藝術效應與作家的人格之間雖然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但是其情感評價的高品位來源於作家的以尚“善”為特徵的人格力量,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魯迅說:“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孫犁說,優秀的作品總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產生“發揚其高級,摒棄其低級,文以載道,給人以高尚的熏陶”。馬嫂、蓮蓮這兩個藝術形象都有著高尚的品格,有著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而這種精神的背後即是作家人格的寫照,從而引導著讀者嚮往高尚。由此可以看出,崔復生從孫犁先生那裡的繼承與革新,所以他的作品才會抑“惡”揚“善”,惡勢力終究會被正義抑制,新生力量則如“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給讀者以積極向上的精神影響。
《血染的芳草》中的蓮蓮,是一個難得的典型形象。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於1601年問世,幾百年過去了,從西方演到東方,至今仍然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阿Q也已從東方步入西方,而富於永久的藝術魅力。確實,凡是在文學史上可以稱為典型的文學形象,都具有永恆的藝術魅力。
文學典型是以人的生命形式呈現出來的,是人們直觀自身的審美價值,富有生命的魅力。蓮蓮那獨特的藝術魅力,當來自她性格顯示的一種生命的魅力。這種“生命的魅力”,首先在於蓮蓮的生命所呈現的斑斕色彩,即性格側面的豐富與多彩。蓮蓮從一個初始盼望過自己的甜蜜二人生活,日日盼夫歸盼夫回,只知在丈夫懷中撒嬌、看見手榴彈就捂耳朵的單純少婦,逐步覺醒、自覺參加到抗日隊伍中,最後智斗漢姦殺鬼子,最終成長為出色的抗日戰士,這其中的變化過程豐富了蓮蓮這個人物形象,增加了形象的飽滿,拓展了生命的張力,顯得有血有肉而豐富多彩。她的成長變化既不突然,也不給人脫離實際的感覺:自然真實,合乎人物性格心靈成長的規律,也突出了蓮蓮人物靈魂的深度。當蓮蓮面對一個個現實中鬼子對她生活的打擊時,如當她得知二姐被日本鬼子糟蹋時,她像被一聲霹靂打倒一樣,她“癱倒在地上,全身硬邦邦的絕氣了”。她被救過來后,終於在太行山的晨曦中,送自己的丈夫谷生上路了:“你走吧,不要結記我······”。顯然,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已開始融進她的靈魂中,她不再沉浸於個人的小天地中,不再逃避,而是睜眼看世界,面對殘酷的現實,鼓起勇氣投入到解放自身與民族以及改變現有秩序的願望之中。蓮蓮的這種轉變是情感與靈魂的深度的結合,是震撼人心的。
蓮蓮的形象很典型,她之所以典型,是與她所處的那個戰亂的環境分不開的,如果硬性地把蓮蓮與時代分離,那蓮蓮這個形象也就失去了她的存在意義,而變得失色單薄。恩格斯的“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題,科學地揭示了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環境中形成的。蓮蓮剛結婚不久,只想過屬於她和谷生的二人生活,只要不影響到她的幸福,外面怎麼亂不關心。她膽子小,對谷生依賴性強,她恨不得時時粘著丈夫,怕谷生一去不回,害怕她的小日子會被衝擊,一心營造自己的二人世界,這時的她無論從思想上還是性格行為上,都還只是一個不諳世事、善良單純的以個人利益為主的形象,有著“一人穿暖,全家不冷”的思想。當丈夫不在時,她“思君不見君”,炮聲紛飛的戰亂環境又使她怕事膽小的敏感神經常常產生種種不祥的預感,由此心理活動產生了豐富而又苦悶的精神生活及行為,諸如捶打丈夫的衣服等等。此時的蓮蓮從內蘊到外形的行為就是她所處的環境決定著的。
典型環境不僅是形成蓮蓮性格的基礎,而且還制約著蓮蓮的行動,制約著蓮蓮性格的發展變化。《血染的芳草》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她符合這一藝術規律。蓮蓮在接到二姐被日本鬼子糟蹋的凶信時,她暈了過去;以及她後來所遇到的一系列現實事實都挑戰著她的忍耐極限,到最終割捨出生不久的孩子,毅然踩著谷生、柱兒、馬嫂的足跡義無反顧地走向更嚴酷的抗戰之路,解放人民之路。這些情節,讓她與環境發生強烈的衝突,進而一步步從思想到行動發生轉變,由最初的逃避、只顧小家而成長為一個懂大義的民族英雄、抗戰勇士,這充分顯示了環境對蓮蓮行動的制約、決定作用。
另一方面,蓮蓮剛開始在面對環境時無能為力,只能選擇逃避不關心,但在一定條件下,她卻對環境發生了反作用。漢奸閻懷乾下派了一個偽革命者來到張家莊尋找谷生家人——蓮蓮,當眾人穩住他準備採取行動時,蓮蓮所表現出的行為確實讓大家及讀者捏了一把汗,尤其是當她氣色從容地走到漢奸面前堅定地承認她的身份,又跟著漢奸向庄外走時,讓讀者及眾人不清楚她葫蘆里賣的什麼葯;並且她在路上所表現出的心理及行動也沒讓大家放心。直到她舉起手槍解決了漢奸后,所有人才把懸著的心放了下來,然餘悸未已。當她“一隻手提著馬嫂送給她的那支撅把兒槍,一隻手掂者從漢奸身上搜來的‘東洋造’,站在村口時,眾人望著她卻驚呆了,一個個好像都不認識這女人,誰相信這就是幾個月前還羞得連家門都不敢出的谷生媳婦兒啊!”是的,抗日的戰火終於把蓮蓮磨鍊成一個有勇有謀的抗日勇士了。這些充分顯示出人物在一定條件下對環境的反作用。這種現象在馬嫂那裡也表現得很充分,她把監獄變成了戰場:推動了故事的前進。
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復存在。典型人物地刻畫是離不開典型環境的,而典型環境則是典型人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基礎,沒有典型環境,典型人物的言談、行動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據,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反之,典型環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環境是以典型人物為中心的社會關係系統。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這個系統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聯繫的紐帶,環境便成了一盤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形成的可能。所以,恩格斯關於“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題,是一個整體性命題,不宜拆開來理解。作品中,蓮蓮的典型性是與她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緊密相連的,她的成長曆程是隨著環境的發展而變化的,如果失去了蓮蓮這個藝術形象,作品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活力;如果沒有特殊的環境造就,那蓮蓮恐怕就要定格在剛入門的目光淺顯的山村新媳婦兒的形象上了,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內涵。
難能可貴的是,除了作者寫實的風格與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之外,崔復生在通過大量的訪問及與太行山群眾的多次交談,在閱讀了大量文獻之後,向我們展示出了太行山兒女們的生活風俗畫卷,如娶親、縫肚兜兒等;同時,對地方語言的巧妙運用:“不濟事兒”、“明日個”、“結記”、“燒鍋”、“你咋個不聽話”等,這些不僅向外人宣傳了河南人獨特的民族風情,對於民俗學研究熟悉河南地域文化也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血染的芳草》是崔復生先生歷經十餘年的嘔心瀝血之作,在中國的抗戰文學中,它不僅豐富了敘事題材,拓寬了描寫範圍,而且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鄉土之氣,是以寫實為主的現實型文學的精緻寫照,對藝術真實的價值追求及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二者把握給後世的寫作者樹立了一個典範,其寫作的內在品格也將指引我們求真務實。同時,希望崔復生先生能帶給讀者更多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