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銘
晚清官員、文史學家
李慈銘(公元1830年~1894年),晚清官員、文史學家。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愛伯,號蒓客,室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會稽(今浙江紹興)西郭霞川村人。光緒六年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日記三十餘年不斷,讀書心得無不收錄。學識淵博,承乾嘉漢學之餘緒,治經學、史學,蔚然可觀,被稱為“舊文學的殿軍”。
李慈銘自幼聰穎,勤思好學,博覽群書,為越中俊才。十二三歲即工詩韻,深受漢學大師、學正吳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稱。一生仕途並不得意,11次參加南北鄉試,無不落第而歸。咸豐九年(1859)北游京城,將捐資為戶部郎中,不料為人欺哄,喪失攜資,落魄京師,其母因此變賣田產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
同治九年(1870),41歲始中舉。光緒六年(1880),51歲始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資郎。他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歷閑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光緒十六年(1890)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任內巡視北城,督理街道,均盡其職。遇事敢於發表意見,也不避權勢顯貴,甚至當面折人、議論臧否,因此常常受人嫉恨,遭人詆毀。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戰敗,聞訊憂懼,咯血而卒,時年66歲。袁行雲先生不無感慨地評曰:“其人品、詞章、學問,俱有可稱,是亦未可輕議也。”

李慈銘像
後來歷經二十年,十一次落榜,於四十二歲時始中舉人。最後又經過十年,三次落榜,終於在五十二歲考中進士。
李慈銘十四歲時,祖母病重,乃奉雙親之命迎娶大他五歲的表姐馬淑人為妻。本意是要“沖喜”,無奈,婚禮剛完成,祖母便於當天去世。這件憾事始終是李慈銘心中難以排除的陰影,使得他與妻子一直維持著如姐弟一般的感情,更影響了李慈銘日後的感情生活。
李慈銘酷好女色。同治五年他就“以四百圓番金購買一歌娘為妾”,光緒初年,他又趁華北大旱,人口價低之際借錢買了兩個妾,其中一個妾就花了白銀一百八十兩。他家裡僕役眾多,最窮的時候,他家也“平均常常雇傭僕人三四人,女傭兩人,更夫一名,廚師一名,車夫一名”。雖然“窮困潦倒”卻行必有車。
清代規定,官員不得嫖妓,但是可以“挾優”,也就是與伶人戲子交往,所以官員交好伶人,成為風習。李慈銘頗好“這一口”,他經常在飲宴時叫伶人來陪,也時到伶人下處去住,梅蘭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稱“花榜狀元”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
李慈銘婚後無子,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下,曾於三十七歲、四十歲、五十九歲時,先後納妾三名,但還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為此,他一直耿耿於懷。到了後來,竟經常流連於風月場所,據說因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盡,所以有了雙性戀的傾向。而且還染上了“好男色”之癖。

李慈銘
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李慈銘的錢全部花在古書上。他無錢買煤,他只好在冰冷中顫慄地熬過一天算一天。他熬夜讀書,為求證一事,翻箱倒篋,辛苦非常。他卻興奮地說,“經義悅人,如是如是!”
李慈銘具有愛憎分明的強烈個性,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人或事情,常不假辭色的當面或即時破口大罵,以致於一些至交好友,如張之洞等,最後都因故宣告決裂。有時他也會在日記中自我檢討,但由於不喜歡俯仰隨人、委曲求全的個性使然,始終不改舊習。不過,他處世雖多有峻厲言行,對於親族,甚至家僕、親友遺孤,則多以溫情相待,可見是一位性情中人。
李慈銘的京官生活,呈現一種極為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李慈銘正式收入極低,其他收入來源也不多,所以經常債務纏身,哭窮叫苦。我們看他的日記,其中經常哭窮,什麼“比日窮困不堪”,什麼“比日窘甚,負債有如牛毛矣”。另一方面,他卻一直追求著與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稱的生活方式:住大宅子,用許多僕人,出門必有車馬。
從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銘租了一套豪宅,原閩浙總督季文昌的舊邸,這個房子可不一般:“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廣植花木,氣派宏闊。”花園裡內有軒翠舫、碧交館、花影廊、小東圃等名勝,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長年沉醉於宴飲、歌郎、冶遊的“上流社會生活”。我們看他的日記,他每個月有一半時間,是在外面大飯店吃飯,“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飲宴”,在聲色上更經常大為破費。“光緒三年,他的仲弟在鄉飢餓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卻花一百多兩於酒食聲色之徵逐。‘余雖窮,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
所以李慈銘的生活屬低收入高消費類型。李慈銘的這種矛盾生活狀態,第一個原因當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貪圖享受所致。
李慈銘官位一直不高,所以收入很低。捐官又掏空了家底,所以家中也無法接濟。但李慈銘的生活品味卻相當高。李慈銘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家中還頗有些田產,從小沒吃過苦,生活相當優裕。所以他一生講究享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對衣服的講究和在乎遠超過曾國藩,比如這一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記:“四月間制珠毛皮小貂袖銀紅江紬袍一領。平生衣服,無此都麗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緻之風,團花繡球,儼然宮體。”此袍雖花去他20兩銀子,但他沒有心疼,反而頗為得意。徐一士說:“慈銘嗟貧,時見於《日記》,而頗講甘美享用。”確實不假。

李慈銘塑像
第二個原因是李慈銘心態的消沉。李慈銘成名既早,自視極高,以為憑自己的才華,搏取“黃金屋顏如玉”當如探囊取物,不料一生困頓,仕途潦倒,沉浮冷署,對此一直深以為愧。所以李慈銘任戶部司官期多年間,他對職事表現得相當厭倦,甚至“經年不一詣署”,原因是他“羞與少年為伍”,“與俗吏隨波”。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基本上是在失望、懶散、憤世嫉俗、牢騷滿腹中度過的。所以乾脆就縱情詩酒,以消塊磊。
李慈銘因境遇不順,“口多雌黃”,“性善罵”,“持論苛刻”,愛批評當時官場種種醜態,對“同時名流,無不極口謾罵,不留餘地”。因此獲得了“敢言”的稱號,被人目為清流。史稱他“不避權要,當面折人、議論臧否”。然而雖然痛恨官場腐敗,李慈銘對陞官其實一樣熱衷。光緒十四年(1888)簡放各省學政,他事先也四處活動,做了許多工作,結果沒有成功。光緒十六年終於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后,他“敢言”的鋒芒就大為收斂。門生攀增祥說“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
李慈銘為官之初,也曾矜尚名節,“嘗自訂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婚壽慶賀”。但他遠未能踐行自己的諾言。李慈銘一方面在日記中深刻嘲諷那些“曲計攀援”以求外官饋贈之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一個“曲計攀援”的高手。光緒七年春,他就曾至賢良寺投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以近日窘甚,冀其隨例有酬應也。”這次李“饋別,敬十二金,犒使二千”。
李慈銘一生謀得的最大一筆“饋贈”,是生涯最後幾年擔任“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所獲的每年一千一百餘兩束修,這是他京官生涯後幾年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的基本保障。“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其實只是一個挂名,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幾次,束修卻如此豐厚,原因很簡單:這其實是李鴻章送給他的“封口費”。蓋李鴻章深知李慈銘之善罵,更自知自己身處高層政治矛盾的中心,很容易被清流們抓住小辮子不放,所以他傾力結好李氏。這筆封口費效果不錯,雖然李慈銘雖恣睢放縱,“任情善罵”,但在晚清清流皆競相痛罵李鴻章之時,他卻從來不開口,“慈銘在言路,不劾李鴻章。”
喜藏書,有藏書室名“越縵堂”、“困學樓”、“苟學齋”、“白樺絳樹閣”、“知服樓”等,卧床左右,羅列書櫃,並排盆花,自稱“書可以讀,花可以賞,二者兼得,其樂無窮”。與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蔭來往書信密切。其藏書不足萬卷,但以精見稱。自稱“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模放之”。僅手校、手跋、手批之書有200餘種。
編纂有《越縵堂書目》,著錄書籍800餘種;又有《會稽李氏越縵堂書目錄》,由雲龍輯有《越縵堂讀書記》,記其閱讀書籍990餘種。藏書印頗多,自稱“書籍不可無印記,自須色、篆並臻妍妙,故選不調朱,收藏家爭相矜尚,亦惜書之一事也”。有“越縵堂藏書印”、“白樺絳樹閣清客”、“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蘿庵黃葉院落”、“桃花聖解盫”、“慈銘”朱文長方印、“霞川華隱”朱文方印、“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等數十枚。
其《越縵堂日記》對古籍的解釋、史料的鑒定考證、人物的評價等,有精到之評;以至本人的經歷和對清末政治事件的描述,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為學者所重。著《湖塘林館駢體文抄》、《白樺絳樹閣詩初集》、《重訂周易小義》、《越縵堂詞錄》、《越縵堂經說》、《柯山漫錄》、《後漢書集解》、《霞川花影詞》、《十三經古今文義匯正》等。所藏書於1918年前後由徐惟則、後裔李鍾俊整理,有書9 000餘冊,手稿10餘種;1928年售於北京圖書館。
繆荃孫撰《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李慈銘,字愛伯,會稽人。諸生,入貲為戶部郎中。至都,即以詩文名於時。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廕引為上客。光緒六年,成進士,歸本班,改御史。時朝政日非,慈銘遇事建言,請臨雍,請整頓台綱。大臣則糾孫毓汶、孫楫,疆臣則糾德馨、沈秉成、裕寬,數上疏,均不報。慈銘鬱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銘為文沉博絕麗,詩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黃。服其學者好之,憎其口者惡之。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而評騭之,務得其當,後進翕然大服。著有《越縵堂文》十卷,《白華絳趺閣詩》十卷、《詞》二卷,又《日記》數十冊。弟子著錄數百人,同邑陶方琦為最。
文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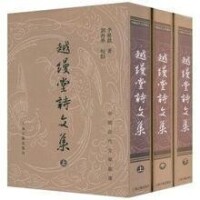
李慈銘
李慈銘自言在創作方面“所得意者莫如詩”(《白華絳跗閣詩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今傳已刻之詩起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同治十三年(1874),共850首,主要反映了貧窘的學者與困頓的名士的生活與心境,山水風物、交遊唱和的“登監閑適之篇”較多,至於“感憤切摯之作”(《越縵堂詩話》),也多是抒寫落拓不遇之感。直接觸及時事、反帝慨時的篇什,如《庚申八月感事》、《出大沽口感事》、《庚午書事》、《京邸冬夜讀書》等,為數寥寥。佔有一定數量的涉及太平天國的詩篇,則表現了地主階級的立場。
李慈銘認為“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他主張內有所蓄。同時廣泛向前人學習,“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為我有”(《越縵堂詩話》)。他的詩大體遵循自己的主張,廣采諸家之長,以寫自身所遭之境,自心所生之感,創造一種“清淡平直,不炫異驚人”(陳衍《石遺室詩話》)的風格,如《自題霞川老屋圖》、《舟入青浦界作》、《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閘作》等。在文章方面,李慈銘認為“文體必本韻偶”(《書凌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強調駢文之美。此外,他的詞也有一些感懷身世之作。
李慈銘除經、史著述之外,刻有《越縵堂文集》12卷、《湖塘林館駢體文》 2卷、《白華絳跗閣詩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隱詞》。尚有《杏花香雪齋詩二集》、《桃花聖解庵樂府》未刻。中華書局出版的《杏花香雪齋詩》10集,為吳道晉所輯。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坦然承認自己重新提起寫日記的興趣是受了《越縵堂日記》的影響。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一文中說道:“《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些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二是許多墨塗,……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越縵堂日記》已列入台灣國中國文教材之一。
《越縵堂日記》的出版經過極為曲折,前後歷時六十餘年。1894年末,李慈銘病逝,遺留日記手稿七十餘冊。當時,沈曾植、繆全孫等人曾極力推動將日記付梓,曾經師事李慈銘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後一盒(日記)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書衡等及學界二十餘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務印書館於1920年以《越縵堂日記》為其名影印出版了遺留六十四冊日記稿的后五十一冊。(內容為李慈銘1863~1889年間的日記)。《越縵堂日記》影印出版后,士林爭相一睹為快,譽之為“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魯迅在《三閑集》中說“《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就是當時日記出版后的真實寫照。
《越縵堂日記》出版后,蔡元培根據李慈銘的遺願擬將剩下的十三冊日記(1854~1862年間日記)進行分類節錄出版,后經錢玄同倡議,仍將剩餘的十三冊日記按前五十一冊之例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線裝本影印出版。這便是《越縵堂日記補》。而樊增祥帶走的李慈銘暮年的日記手稿(1889~1894年記)則如泥牛入海,音信全無。儘管各時期都有熱心人士呼籲追尋,但始終沒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發現。這宗重見天日的手稿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於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學齋日記》共九冊,至此,李慈銘日記始以完璧面世。
代表詩作

李慈銘手稿
又聽呢喃到畫檐,舊巢重待絮泥添。
主人為爾嫌春早,閑過花時不捲簾。
【鑒湖柳枝詞十二首選一】
家家門巷正啼鶯,取次輕陰間嫩晴。
滿院楊花人不到,鞦韆撩亂作清明。
【丁丑九月京邸大風感懷】
流水游龍日夜馳,品題豪竹與哀絲。
誰雲飢餓蒼黃日,猶是承平宴飲時。
天樂瞢騰如昨夢,杞憂涕淚有誰知?
只須一醉生涯了,莫忘高陽舊酒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