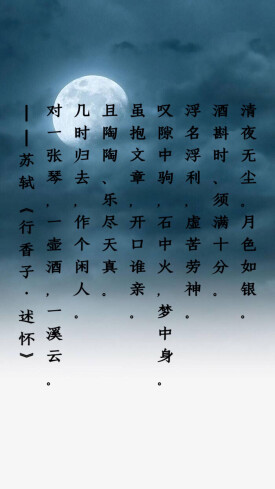述懷
杜甫的詩作
《述懷》是唐代詩人杜甫所創作一首的五言古詩。此詩根據自己的見聞,在詩中簡述了一年來的經歷以及對家屬的思念,用豐富的想象,把心中的憂慮和驚恐具體生動地描寫了出來,讀來感人至深。全詩沒有一句空閑之語,只是平鋪直敘,卻有聲有淚,感人至深。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
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
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
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①述懷:陳述自己的懷抱、志向。
②中原:原指黃河南北一帶,這裡代指中國。逐鹿:比喻爭奪政權。典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③投筆:出自《後漢書·班超傳》:“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事戎軒:即從軍,戎軒指兵車;亦以借指軍隊、軍事。《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
④縱橫計:進獻謀取天下的謀略。不就:不被採納。
⑤慷慨志:奮發有為的雄心壯志。
⑥杖:拿。策:謀略。謁:面見。
⑦關:潼關。
⑧請纓[yīng]:出自《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而致之闕下。”終軍:字雲長,漢武帝時人,西漢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⑨憑軾:乘車。軾:古代車廂前面用作扶手的橫木。下:是敵人降服。東藩:東邊的屬國。
⑩鬱紆[yù yū]:山路盤曲迂迴,崎嶇難行。陟[zhì]:登。岫[xiù]:山。
⑪出沒:時隱時現。
⑫古木:老樹。
⑬千里目:荒涼冷落,令人凄傷的景象。
⑭九逝魂:旅途遙遠而艱險。九:表示多次。
⑮憚:畏懼、害怕。
⑯懷:感。國士:一國之中的傑出人才,《左傳·成公十六年》:“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恩:待遇。
⑰季布:楚漢時人,以重然諾而著名當世,楚國人中廣泛流傳著“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諾:答應,諾言。
⑱侯嬴:年老時始為大梁監門小吏。信陵君慕名往訪,親自執轡御車,迎為上客。魏王命將軍晉鄙領兵十萬救趙,中途停兵不進。侯嬴獻計竊得兵符,奪權代將,救趙卻秦。
⑲感:念。意氣:指志趣投合,君臣際遇,必須實踐諾言,感恩圖報。
去年安祿山叛軍攻破潼關,與妻子兒女隔絕很久。
今夏草木繁茂的時候,才得以脫身向西逃走。
腳穿麻鞋去拜見天子,破舊的衣袖露出兩肘。
朝廷憐憫我得以生還,親朋故友感傷我已老丑。
感激涕零拜授左拾遺,顛沛流離中更感皇恩深厚。
雖然我可以回到家去,卻不忍心立即開口求情。
寄一封書信探問三川,不知道家中親人還在否。
聽說家鄉一帶同遭禍患,瘋狂殺戮乃至雞和狗。
山中的茅屋早已破漏,有誰還能在門戶中留守。
蒼松的樹根被摧折斷毀,山地寒冷屍骨未朽。
能有幾個人保全性命,一家人豈能相伴為偶。
高山上有猛虎出沒,心中鬱結搖頭嘆氣。
自從寄出去一封書信,至今已是十月以後。
反倒害怕消息傳來,心中除此別無他有。
國家命運剛要中興,年老后比平時更愛飲酒。
想到日後歡會的時候,恐怕成為一個貧窮孤獨的老叟。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杜甫仍被叛軍禁於長安。時杜甫得知肅宗移駕鳳翔(是年二月初九日),即有意投奔鳳翔,於是便前往懷遠坊大雲經寺住寺僧贊公處,以避叛軍耳目。與贊公密商后,於四月某日,由長安西城金光門出,間道潛奔行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壬戌),杜甫在鳳翔官拜左拾遺。驚魂稍定,因思念妻子及家人,便寫下了這首詩。
此詩題為“述懷”,所述之“懷”雖主要是對家室存亡的憂懷,但由於處在安史之亂的戰亂流離的大背景下,這種家室之憂就和國家危難密不可分,充分體現出家室之憂的時代特殊性,並從一個側面對戰亂流離的時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內心情感的抒寫,也是時代的寫真。
詩共三段。開頭一段十二句,抒寫自已初授拾遺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親的矛盾心情。開篇兩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關破”,點出國家殘破、京都淪陷、戰亂流離的大背景:“妻子隔絕久”,點明自己與妻子兒女長久相互隔絕、不通音訊的事實。這兩句為下面兩段對家室的千迴百轉的憂念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是全詩的綱領。
接下來兩句,寫自己從淪陷的長安城脫身西走,投奔肅宗。杜甫潛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時草木繁茂,可以隱蔽間道潛行的詩人,故說“脫身得西走”。與妻子兒女隔絕已久,但一有脫身機會,並不是先去探尋家室,而是投奔鳳翔的肅宗,正見出先國后家是詩人的自覺行動。
麻鞋”六句,寫抵鳳翔見肅宗得授拾遺的情景,寫得極樸質、真切、生動、細緻。拜見肅宗時,腳上穿著麻鞋,破舊的衣袖露出兩個胳臂肘,完全是間道逃奔途中的狼狽形象,可以想見麻鞋上還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處處留下荊棘的痕迹。這樣不加任何整飾地去拜見肅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對君主的一片赤誠,也透露出在非常時期君臣朝儀的草率不拘。原生態的生活細節即用極樸質的原生態表達方式來呈現,收到的是極生動真切的藝術效果。千載之下,猶可想見當時情景。細節傳神,樸素傳真,正是這兩句詩的魅力,也是這一時期杜甫的詩歌創作共同的藝術取向。正因為狼狽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愛國的赤誠,因此朝廷上下憫其幸得生還,而親朋故舊則傷其形容憔悴,皇帝也為其忠誠所感動,親授拾遺之職,自已則深感在顛沛流離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淚交零。這四句寫自己在朝廷上下,親朋故舊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樣不加掩飾,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盡致。這六句乍看與憂念家室的主題似乎關係不大,實則正是由於自己一片忠君愛國的赤誠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這一段的最後兩句。“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國家仍在危難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自己無法開口要求告假探視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於君國與憂念家室的內心矛盾,這才引出下面兩段千迴百轉的至情之性之文。
“寄書”以下十二句,抒寫對家室存亡未卜的憂念和悲慨。因未忍開口告假,故有“寄書問三川”之舉,但由於久與家人隔絕,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還在不在三川。這兩句是一層。“比聞”以下,因新近聽到傳言說,那一帶的百姓因遭戰禍,慘遭叛軍殺戮,已經到了雞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難逃此劫難。“山中”四句,便是對家室罹禍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風的茅屋裡,此刻還能有誰在倚窗戶而相望呢?也許都已慘遭殺戮,在摧折衰敗的蒼松之根,屍骨狼藉,地雖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體貼入微而又沉痛徹骨。詩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屍骨一起感受到異鄉土地的寒冷。但畢竟“殺戮到雞狗”的景象只是出之傳聞,因此詩人意中仍有所猶疑,“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二句便是這種心理的反映。在這種“殺戮到雞狗”的情況下,很少有幾個人能僥倖保全性命,就算有人僥倖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團聚,這雖是對情況的反測,卻也透露出詩人意中或存此想。雖然比全家盡遭劫難似乎好一點,但同樣是家室殘破的悲劇。這又是一層。叛軍的殺戮使京城周邊的大片地區成了險惡的猛虎肆虐的場所,自已心情鬱結,難以解釋,只能頻頻回首了。從“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盡室豈相偶”,意凡三層,有轉進,有曲折,充分表現出在音訊隔絕、只憑傳聞的情況下詩人對家室存亡情況的種種預測與想象,語極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鬱悲涼。
“自寄”以下八句,承上“寄書問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與家人隔絕後音訊不通的情況,轉出“反畏消息來”的心理和“恐作窮獨叟”的深悲。在叛軍肆行殺戮的戰亂背景下,十個月來音訊不通,未接家書,詩人的心理便從長期的盼家書轉為害怕有關家人消息的到來,生怕傳來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難的噩耗。因為長期得不到家書的客觀事實很可能預示著家人早已不在人間。這種不祥的預感隨著時間的進程愈積愈強烈,愈執著,最後便由“切盼”演變為“反畏”。處於對立兩極的心理這種出人意料的變化,卻最真實深刻地反映了戰亂給詩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創傷。這種心理描寫,確實非親歷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則將詩人“反畏消息來”時那種既惶恐不安又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盤托出。“漢運初中興”,國運初顯轉機,這是值得慶幸和欣然的,但個人的命運卻不可預料,只能借酒遣悶,沉思默想將來慶祝勝利歡會之時,自己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獨終老了。國家的中興,將來的歡會,反而更襯托出了個人悲劇的命運。
全篇運用傳統的賦法抒寫戰亂年代家室離散,存亡未卜的憂悲。詩人的真實願望自然是盼望家人無恙,合家團聚;但戰亂的現實,特別是叛軍肆意殺戮的暴行和久未接家書的客觀事實卻使詩人對家室的憂念越來越深,從而產生一系列不祥的預感和想象,千迴百轉,如層波疊浪,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只用最樸質的家常語道出,至情至性,感人至深。陶詩的樸質,是於樸質中見平淡;而杜此詩的樸質,是於樸質中見沉痛。此正兩人的不同處。
宋代文學家、詞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腳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
明代文學家高棅《唐詩品彙》:陳後山云:不敢問何如?劉云: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而毫髮不失(“自寄”四句下)。
明代文學家王嗣奭《杜臆》:他人寫苦情,一言兩言便了,此老自“寄書問三川”至末,宛轉發揮,蟬聯不斷,字字俱堪墮淚。
明代戲曲家黃周星《唐詩快》:至性語令人墮淚(“流離”句下)。宋延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十字妙矣,此以五字括之(“反畏”句下)。
清代學者仇兆鰲《杜詩詳註》:申涵光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一時君臣草草,狼藉在目。“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非身經喪亂,不知此語之真。此等詩,無一語空閑,只平平說去,有聲有淚,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鋪敘太實,不知其淋漓慷慨耳。
清代學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真情苦語,道得出。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唐宋詩醇》:李因篤曰:《北征》如萬山之松,中蔚煙霞;此詩如數尺之竹,勢參羅漢。
清代學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妙在反接。若雲“不見消息來”,意淺薄矣(“反畏”句下)。
清代學者沈德潛《說詩啐語》:(杜詩)又有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雲“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今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
清代學者浦起龍《讀杜心解》:詩從一片至情流出。自脫賊拜官后,神魂稍定,因思及室家安否也。……后八司四應中段,四應首段,而“窮獨叟”乃綰定妻子,收束完密。
清代學者楊倫《杜詩鏡銓》:李云:其妙處有一唱三嘆、朱弦疏越之妙。李云:如子長敘事,遇難轉佳,無微不透,而忠厚之意,纏綿筆端。公至性過人,不易企如此。張云:寫出微服瑣尾景況(“麻鞋”六句下)。亦以朴勝,詞旨深厚,卻非元、白率意可比。公詩只是一味真。
清代學者施補華《峴佣說詩》:“自寄一封......寸心亦何有?”亂離光景如繪,真至極矣,沉痛極矣。
近代學者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張廉卿曰:真朴之中,彌復湛至(“流離”句下)。吳云:收極凝重,所謂“盛得水住”者。吳曰:此等皆血性文字,至情至性鬱結而成,生氣淋漓,千載猶烈。其頓挫層折行氣之處,與《史記》、韓文如出一手,此外不可復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