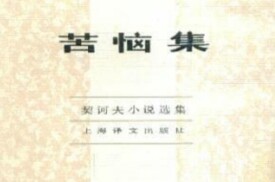苦惱
【俄】契訶夫創作短篇小說
《苦惱》是俄國作家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創作的短篇小說,發表於1886年。小說寫的是一位名叫姚納的車夫,一心想跟別人談談他才死不久的兒子,減輕一些內心的傷痛,可幾次三番沒有人聽他的,結果他只好把滿腹心事向他的小馬訴說。
小說用以小見大的手法反映社會現實。這是一件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作者藉此表現出社會下層小人物悲慘無援的處境和苦惱孤寂的心態,強烈地渲染出沙皇俄國的世態炎涼。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與人關係的自私、冷漠。
在俄國大都市彼得堡趕車的老車夫姚納,身處社會底層,生活十分困苦,遭遇又很不幸,姚納的妻子早己去世,新近又剛死了兒子,深沉的哀痛充塞著他的胸膛,急欲找一個人傾吐自己的悲傷。在一個大雪紛飛之夜,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坐他馬車的客人或遇見的普通人訴說,不是遭到侮辱就是遭到拒絕。在車水馬龍的彼得堡,在川流不息的人流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把話說完,姚納最後只能向同自己相依為命的小母馬去訴苦吐怨。
19世紀80年代,俄國正處於沙皇統治下的黑暗時期。70年代興起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由於無視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得不到農民的支持而最終失敗了。進入80年代后,他們轉而採取暗殺手段來推翻專制制度。雖然他們成功地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但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后,便開始了更加殘酷的血腥鎮壓,革命者成批地被絞死和流放,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普遍的絕望情緒,喪失了以往的那種革命信念和鬥爭精神。窒息的政治空氣也使許多人變得麻木、冷漠,充滿了庸俗的市儈習氣。
契訶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貧困中度過的,因此他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和不幸深有體會。19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了創作生涯,到寫作《苦惱》時,社會責任感已經日益增強,民族傾向也更加鮮明。
19世紀沙皇俄國統治下的俄國社會,沙皇的專制統治使得當時社會中的人等級制度分明,人與人之間關係麻木冷漠。處在上層社會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處在下層的如馬車夫姚納·波塔波夫則生活困苦,掙扎在生存的邊緣,貧富差距十分明顯。
姚納
主人公姚納並沒有提出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任何要求。甚至,他對於自己長期沉浸在困苦中的感覺也早己遲鈍近於“麻木”,他僅僅還保留著一顆慈愛的父心。因此在強忍著喪子之痛時,要求人們賜予一點最起碼的憐憫,以便慢慢地驅散胸中的愁雲慘霧,使他能夠勉強地在這冷酷的人間度過餘生。不料,姚納所見到的人,一個個地泯滅了惻隱之心,同情他的居然是不通人言的小母馬。
軍人
作為社會上層權貴的軍人,當聽到姚納說“老爺,那個,我的兒子—這個星期死了”的時候,他回答,“哦—他是得什麼病死的”,卻又“閉上眼睛,分明不想再聽了”軍人知道自己應該在此時表現出同情心,所以問“他是得什麼病死的”,很明顯,這僅僅是禮節性的敷衍。
心靈隔膜
軍官、夜遊青年和年輕車夫對待姚納的態度集中體現的是小人物之間的心靈隔膜問題。他們雖然和姚納處於同一社會階層—小人物,但是他們對姚納的心靈之門卻是關閉的。正是這些和姚納地位相同,身份相似的小人物在不經意間發出的對他人存在和需求的漠視信號,而釀成了同類的大苦惱、大悲傷。
造成姚納苦惱的軍官、夜遊青年和年輕車夫這類小人物,是契訶夫筆下的匆忙過客和趕路的人,其特殊意義在於借“沒有人理會別人的苦”來揭示人心的隔膜和現實的冷漠。小人物拒絕姚納訴說苦惱的經歷,意味深長,令人深思:人們都在忙碌著,“有誰可曾真正關心那些渴望關心的人,有時這種渴求的標準很低很低,只是給他一對耳朵,聽他傾訴;給他一種目光,寄寓關切、同情和理解”“人們似乎都太忙碌了,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有誰真正關心別人過得怎樣,心情如何?”“即使朋友相見,也只是寒暄客套了事。在這種氛圍背景下,自己的大苦惱,對他人來說也不值得一提。”心與心之間的隔膜造成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不能相互溝通,自己之於別人,別人之於自己,都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自我異化
自我的異化以人性本身的異化為表徵。在表現人類自我內部異化的時候,盧梭將文明人與自然人進行對比,認為當代社會中所謂的文明人是異化后的自然人。文明人與自然人不同,自然人貼近著自然本真的狀態,享受著內在本性的自由。而文明人則更多地被社會各種規則所束縛,生活在他人的意見之中,被他人的看法所奴役,從而喪失了自己內在的獨立性,習慣性地依附在他人對於自我的看法之中。這種文明人不是自足的個體,而是一個外展的自我,他們生存於自身之外,很少關注自我內部的感受,是一種外傾的個體,是一種喪失了主體獨立性人格的所在。
主人公姚納·波塔波夫正是這樣一個背離自己自然本性狀態、不斷自我異化的一個“文明人”的代表。他受限於人類社會中的種種規則制度,不能將自身於束縛與奴役中抽離開來,而只能是無怨無悔地甘心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奴役,喪失了屬於自己的獨立人格,並渴望通過他人的意見尋求自我的精神解脫。小說的開頭一句“我的煩惱向誰去訴說”,表明了作為一個社會文明人,姚納·波塔波夫缺乏自己的獨立人格,在發生了自己兒子不幸死亡的事情之後,他苦於喪子之痛無法緩解,渴求著通過向別人訴說這一苦難的事實,讓別人感受自己的傷痛,希冀別人能給自己以生存的安慰。這種對他人情感上的依附狀態,正是盧梭日中的“人自我的異化”。處在社會生活中的人無法擺脫他人的意見,渴望得到他人的注意與情感交流,並認為在與他人的傾聽與交流中自我的意義才得到了證實,而這種情感上的依附也使得如姚納·波塔波夫的一類人在發生了情感上的傷痛時不能正視自己的生存困境,不能反思造成災難與不幸的緣由,不能在自我內部感覺的關照中得到精神的拯救,而是固步自封,企圖通過對苦惱的講述來獲得他者的精神慰藉。這種行為本身是一種人的存在與其本性的疏離,但作為排解痛感的手段本身也無可厚非,只是在當時當地的社會背景下,聽眾的缺乏使得難以訴說的苦悶愈盛,姚納·波塔波夫也在這種無法排解的情感壓抑中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激情,以至於“現在對他都一個樣兒,只要有主兒就行……”老姚納渴望從他人那裡尋求有效的意見和些許的安慰,但是註定只能不斷在困境中掙扎,難以超拔。
作品層次
《苦惱》的層次非常清楚,寫了姚納四次向他人傾訴,四次碰壁,最後只好走進馬棚,對馬訴說。契訶夫每寫完一次姚納的碰壁,接著便寫他的苦惱,而每次碰壁后,他的苦惱就隨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后,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后,寫了姚納想象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傾訴,整個故事看似平鋪直敘,其實匠心獨運。
姚納遇到的四類人及對他們的稱呼是軍人(老爺)、三位年輕人(老爺)、僕人(老哥)、年輕車夫(老弟),這四類人的先後順序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從高到低的順序,姚納在最後一次碰壁后,他在想象中向“娘兒們”傾訴,從排列順序看,排在牲口(小馬)的前面,可見當時俄羅斯婦女地位的低下。奇怪的是:當姚納向軍人和三位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傾訴時,這兩類人雖不耐煩,卻還敷衍一句:“他是害什麼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當他去向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前者讓他走開,後者一言不發倒頭便睡。如果說,被姚納稱之為老爺的軍人和三位年輕人,決不會花時間去聽一個窮車夫的訴苦,這裡存在社會地位的隔膜;而當姚納去向和他同階層的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他們竟連敷衍的話也懶得說,這的確發人深省。
語言風格
小說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卻內容豐富,這與作者精鍊、簡約的語言風格是分不開的。首先作者用詞簡單、精確、凝練,在環境描寫與人物描寫等方面選用的詞語樸實無華、又簡潔精鍊、寓意卻又十分豐富;其次作者在選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對話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結構簡單、短小精悍,顯示出了語言簡潔的特點,再次作者在描寫時還運用了一些修辭格,收到了簡單、精鍊、形象、生動的修辭效果、另外《苦惱》中還大量運用了省略號,這些省略號的運用也使語言含蓄、凝練,產生空靈之美。
契訶夫與其他一些俄國作家不同,他筆下的人物對話極其精鍊,毫無冗長和羅嗦之感。人物對話不僅符合特定環境下和場合里人物的性格邏輯,而且能恰當地映射出人物此時此景的內心活動。三個青年的對話顯示出他們尋歡作樂、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納挨了他們一巴掌還說:“嘻嘻!……好有興緻的幾位老爺……”內心正轉著這樣的念頭:他們有興趣和他打著玩,大概也有興趣聽他談談兒子。同時,姚納的對話也反映了他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性格和急於傾訴內心愁苦的心情。這對刻畫馬車夫的性格特徵和深層心理狀態起了很大作用。
描寫手法
契科夫在《苦惱》中也採用了現實主義客觀描寫手法,他強調作者在創作中的客觀態度,但絲毫不反對作品應有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不是廉價的說教,不是硬塞給讀者,而是把鮮明的傾向絲毫不露行跡地融入對現實生活的客觀描述中,他認為傾向性是作者主觀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這種流露越隱蔽越好。全文通篇沒有作者主觀的說教,但讀者卻從作者抑鬱的描述中,看到人間的冷酷和世態炎涼。這正是契科夫“態度越是客觀,所產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現實主義的成功體現。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於冷如冰霜的社會的揭露,真實入木三分,令人叫絕。《苦惱》它強烈刺激著讀者的不是別的,乃是驚人的真實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苦惱》是)契訶夫最佳的短篇小說之一。
前蘇聯作家高爾基:它是一部非常真實生動的作品。
英國女作家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於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
契訶夫(1860-1904),俄國小說家、戲劇家。出生於破產商人家庭,早年邊做家庭教師,邊求學。1884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