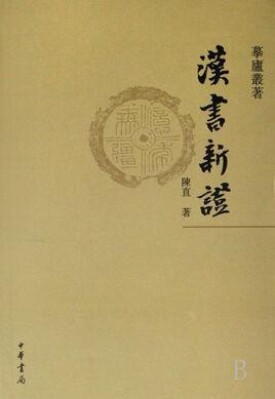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陳直的結果 展開
- 中國好聲音第三季學員
- 宋代養生學家
-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陳直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陳直,原名邦直,字進宧(宜),號摹廬,又號弄瓦翁。祖籍江蘇鎮江,遷居江蘇東台。出生於1901年3月13日。1980年6月2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0歲。生前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考古研究室與秦漢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學學術委員,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陝西省政協委員,陝西省社聯及史學會顧問,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籌備小組組長等職。
陳直出生於一個貧困的讀書人家庭。在家庭的影響熏陶下,他自少年時代便“尤喜治秦漢史”。從13歲起,即系統研讀《史》《漢》,以後每二年必通讀一次,相沿為習。為了糊口,17歲的陳直到揚州宜之齋碑店當學徒,后又做家庭教師、縣誌編輯、義務教員等。在緊張勞作之餘,自學不輟。24歲時,撰成《史漢問答》二卷,39歲前刊行的著作有《楚辭大義述》、《楚辭拾遺》、《漢晉木簡考略》、《漢封泥考略》、《列國印製》、《周秦諸子述略》、《摹廬金石錄》等多種。其中不少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好評。如《漢晉木簡考略》,1934年一出版即流布海外,為學人所矚目。再如他26歲時寫成的《楚辭拾遺》,與洪興祖、戴震等鴻儒巨匠的著作並列,為研究楚辭的必讀之書。此外著有的《朱育對濮陽興問較注》、《東坡詞話》、《慈萱室駢文》及詩集因條件限制,未能刊印。另又對古代貨幣進行研究,著《列國幣考》,並參與了由丁福保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的撰寫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斷然拒絕了敵偽的封官許願。於1940年逃離淪陷區,繞道香港,經昆明、貴陽、成都,最後抵達陝、甘。為謀生計,先後在蘭州、西安等地金融機構中供職,從事與學術豪無關係的文牘工作。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關中為秦地故都的地理優勢,致力於收集整理秦漢瓦當、貨幣、璽印、陶器等文物,作為研究秦漢歷史的資料。他以學者的敏銳目光,從古董商手中挽救保護了許多稀世國寶,僅陶器就收藏200餘件。其中如居攝二年陶瓶、咸里高昌陶鼎、永承大靈瓦、羽陽千秋瓦、天毋極瓦范、蘇解鳥陶器蓋、野雞范、大前右足范、楊字板范、蕭將軍府瓦片等,皆為罕見之珍品。
1949年後經著名學者、教育部長馬敘倫推薦,由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邀請,他自1950年開始執教於西北大學歷史系,從此才得以集中精力從事學術研究。1955-1966年間,是他科研大豐收的時期,200餘萬字的學術巨著《摹廬從書》、百餘篇學術論文,主要完成於此期間。1963-1964年,他應著名學者翦伯贊及佟冬的邀請,分別赴北京大學和東北文史演技所講學。中華書局委託西北大學歷史系標點《漢書》,他任總較另與冉昭德共同主編《漢書選》,作為全國高校歷史專業史學名著選讀課程教材。
“文革”期間,陳直的研究工作被斥為“四舊”而遭受批判。在險峻的政治形勢下,其家境亦因老伴不幸去世而急劇惡化。面對各種壓力,他以驚人的毅力,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默默地開始修訂舊稿的工作,並把全部文稿親手用毛筆抄寫了四份,整個工程在1000萬字以上,從而給後人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
粉碎“四人幫”以後,陳直雖年近八旬高齡,但卻以極大的熱情,把主要精力用於培養研究生及指導中、青年教師業務進修方面。直到謝世前一刻,他還在為以為研究生解答問題,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直治學,師承清代樸學的傳統,同時也深受王國維近代考據學二重證據法的影響,既重要文獻資料、亦重考古資料,提出了“使文獻和考古合為一家”,“使考古為歷史服務的”學術主張,並大力倡導“搞人民史”,“搞手工業史”。特別是在擴大資料來源方面,他獨闢蹊徑,別開生面,把人們不太注意的瓦當、磚文、璽印、封泥、貨幣、錢範、銅鏡、陶器、漆器等尋常古物,出神入化地引入史學研究殿堂,獲得了突出的成就,可謂是前出古人,后啟來者。
《摹廬叢書》是陳直50歲以後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叢書由18種學術專著組成,即《讀金日札》、《讀子日札》、《漢書新證》、《史記新證》、《居延漢簡綜論》、《居延漢簡簡要》、《居延漢簡紀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訂誤》、《敦煌漢簡釋文平議》、《關中秦漢陶錄》、(考證部分獨立成冊,名為《關中秦漢陶錄提要》),《秦漢瓦當概述》、《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鹽鐵論解要》、《三輔黃圖校正》、《古籍述聞》、《顏氏家訓注補正》、《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文史考古論叢。至1994年,叢書已全部正式出版或發表。另有手稿本4部,分別為四川、陝西兩省圖書館,西北大學圖書館及陳直家人收藏。
《漢書新證》作為陳直的代表作,1959年出版后即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20年後經續補再版,更受到學人的推崇。該著取資古器物考證《漢書》,在確定《百官公卿表》未載之官名,考證州郡縣屬吏名稱,考證地理名稱之誤字,考證姓氏,訂正人名,印證宮殿名稱,確定漢代物價,疏證典制,揭示《漢書》古字奧秘,考訂避諱義例,考證習俗語,考證軍事設置,考訂顏師古注文錯誤等方面,皆前人所未言,對推進題無剩義的《漢書》研究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史記新證》是《漢書新證》的姊妹篇,1979年出版。因《漢書新證》完成在先,《史》《漢》重複部分,此書則刪削不錄。所謂“新證”者,是在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及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較補》之外,再用考古資料對《史記》加以解釋。由於全書取材廣泛,考證精到,發前人之所未發,被學術界奉為《史記》研究之圭臬。
《兩漢經濟史料論叢》是陳直的又一部力作,初版於1958年,增訂後於1980年再版。全書計有《西漢屯戍研究》、《關於兩漢的手工業》、《兩漢工人的類別》、《兩漢工人題名表》、《鹽鐵及其他採礦》、《關於兩漢的徒》、《漢代的米穀價及內郡邊郡物價情況》等6文1表,對史籍缺載的兩漢下層民眾和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與工作,以及同其日常生活相關的一些問題,作了極有價值的探討。當50年代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同志普遍感到秦漢手工業幾乎無話可講之際,陳直此書運用文獻和考古相結合的方法,奇迹般地在這一領域開闢出了一片廣闊的新天地,取得了奠基性的重大成就,從而將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三輔黃圖校正》為斟直古籍整理方面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該書在前人校勘《黃圖》的基礎上,對其原本、今本的成書時間及由原本到今本的發展過程,作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其中博採各種古籍及銅器、磚甓、瓦當銘文以及親身訪問的見聞,對《黃圖》逐字逐句作出校正,辨明源流出處,釐正傳抄錯誤,為秦漢都城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摹廬叢著七種》是陳直《摹廬叢書》中7種專著的彙集本,1981年出版。其中《讀子日札》為讀墨、荀、韓、呂覽、淮南5種子書的札記;《鹽鐵論解要》是對《鹽鐵論》的校訂增補與考證詮釋;《敦煌漢簡平議》為折中、修訂沙畹、王國維、賀昌群、勞干四家有關敦煌漢簡的詮解;《秦漢瓦當概述》是將傳世及後世發現的秦漢瓦當分類敘述考證,並加以綜合論述;《關中秦漢陶錄提要》是對《關中秦漢陶錄》及《續陶錄》所收之陶瓦器物的考證文字彙篆;《顏氏家訓注補正》系對清代學者趙敬夫、盧抱經、錢辛楣三家關於 《顏氏家訓》註釋的補正;《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原系陳直青年時代所作,后經增補,遂成完璧,對研究南北朝門閥史,具有重要價值。
《居延漢簡研究》為陳直探討居延漢簡的5種專著之彙編,1986年出版。其中因事名篇,作貫通性專題考證者,曰《居延漢簡綜論》;對居延、敦煌、羅布代爾、武威磨咀子諸漢簡作解要或通釋者,曰《居延漢簡解要》;校訂居延漢簡釋文者曰《居延漢簡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訂》;研究居延漢簡紀年問題者,曰《居延漢簡系年》。所論極富創見,成一家之言,為治漢簡的必讀之書。
《文史考古叢書》是陳直的論文選集,1988年出版。原題《述學叢編》,后改今名,共收入文學、史學、考古論文61篇。其中《楚辭解要》系據少作《楚辭拾遺》重加較補;《故技述聞》是整理當年其父講述古籍的筆記並融入己見而成,列為《摹廬叢書》一種。文集中多數文章雖曾公開發表,但集精粹於一篋,畢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讀金日札》為陳直研究金文的專著,內容分為“通義”(34條)、“傳世銅器”(56條)、“發掘銅器”(27條)、“璽陶文學”(計兩文)四類,時限上自殷商,下迄嬴秦。所論不僅對古銅器銘文的字義、句意多有創見,而且闡發了其中有關國家、政治、管制、生產、科技、醫學等方面的內涵。該著部分內容曾在《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發表,全文經整理刊於《南京博物院60周年紀念文章》(1993年)。
《關中秦漢陶錄》是陳直的一部考古專著,1994年出版。全書包括三部著作:一是《關中秦漢陶錄》及《補編》(即《續陶錄》),收錄秦漢陶器拓片495紙,摹本5紙,涉及器物501件,分為陶器、瓦當瓦片、磚文、錢範四大類,“皆以前人未經著錄之品為斷”。二是《雲紋瓦4圖錄》,收拓片55紙(秦葵紋瓦6品、漢雲紋瓦49品)。以上兩種著作手稿一直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珍藏,40年未曾面世。三是《摹廬藏瓦》(附陳直其他藏瓦),共收拓片97紙,涉及器物110件,為陳直家藏。書中所收拓片均為原拓,原器大多毀佚不存,拓片亦多為孤本,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陳直手書考釋文字,辯偽斷代,著錄源流,考究存佚,且以之訂正《史》、《漢》,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出版採用手稿原大影印,錦函線裝,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該書品類之廣,搜羅之富、考證之精,均超過世傳同類諸書。
陳直還精於近體詩,詩作約200餘首,急名曰《摹廬詩約》。1992年出版的《陳值先生紀念文集》,曾選其代表作20首發表。
陳直先生與秦漢史研究——紀念陳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誕辰100周年
作者:黃留珠
今年是新千年的開始,也是著名的史學家、考古學家陳直教授逝世20周年暨誕辰100周年的年份。我們以深深的敬意,無限緬懷這位曾對秦漢歷史和秦漢考古研究,對中國學術事業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前輩;也僅僅以這種著文的樸素形式,來紀念這位終生奉獻學術事業的師長!
眾所周知,陳先生治學,路子很寬,歷史文學,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訓詁,譜牒宗教,歷算醫藥,幾乎無所不綜。但他用力最勤者,還在秦漢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話講,叫做“喜治秦漢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學術成就,於秦漢史最為卓著;他治史的經驗,於秦漢史領域最為豐富。在紀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如果對這方面有所總結,使之啟迪後學,繼承發揚光大,無疑是對先生最好最有意義的一種紀念。
新突破
1.
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國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讀、不能不研究的。這就是說,中國古代史工作者,對於秦漢史幾乎無人不通曉、無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漢史這塊園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別密集,題目也大多都被人做過,所以,很難再找到未開墾的處女地。面對如此一個屢經深耕細作的領域,陳直先生硬是憑藉著他那深厚的學術功底,以敢啃硬骨頭、敢打硬仗的無畏精神,通過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這裡不妨以他對《史記》、《漢書》的研究為例,來做具體的說明。
陳先生對《史記》、《漢書》的研究,發端很早。他從13歲起即系統研讀《史記》、《漢書》,以後每二年必通讀一次,相沿為習[2]。24歲時,他便寫出了《史漢問答》二卷[2],反映出這方面研究的濃厚興趣。後來他在西北特別是在西安供職期間,充分利用這裡曾是周秦漢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優勢,採用文獻與文物考古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史記》、《漢書》,研究古史,從而使其水平達到更高的層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時間,寫出了13萬字的《漢書新證》[3]。次年,又完成了14萬字的《史記新證》[3]。這是他對《史記》、《漢書》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認為可以的傳世之作。1959年,《漢書新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出版社的《新書介紹》評價稱:
《漢書》成書後,注者甚多,唐之顏師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餘家,顏師古以後,注者復有數十家。但這些注《漢書》的人,都以書面材料為主,轉相引證,問題滋多。本書著者是國內治《漢書》的專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漢銅器、木簡、封泥等物,所以與前此《漢書》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證,尤有精湛獨到之處,可以認為是研究《漢書》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陸人的商品意識還極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紹絕無廣告成分,是非常平實的,許多地方甚至評價偏低。但由此亦不難看出《漢書新證》非凡的學術價值;它對題無剩義的《漢書》研究來說,確乎是一個空前的突破。1979年,經過續證、訂補的《漢書新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數近35萬。先生《自序》云:
此書曾於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證雲者,取別於舊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為居延、敦煌兩木簡,漢銅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漢印、貨幣、石刻各種。其體例有時仿裴注,系證聞式,旁搜遠紹,故不偏重於音義。嗣後於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記新證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歷史系接受中華書局標點漢書之囑託,我亦參加工作,因此又將全部漢書,泛覽一過,歷四個月之久竣事。溫故知新,簽記所得,於是始有撰寫續證之計劃。迨暑期休假,隨讀隨記,歷時半歲,又成續證二卷。思及新續二證,各自為書,容有未善。乃於六○年十月,合前後兩編,再加訂補,匯為一書,即今本也。
同年,《史記新證》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該書《自序》中指出:“余之為新證,是在會注考證(黃按:指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及考證校補(黃按:指日人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之外,加以解釋,其材料多取材於考古各方面”;“因漢書完成在先,與之重複者,大部分均已刪削”;“書名新證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證實太史公之紀載,與逐字作訓詁音義者,尚微有區別”。顯然,《史記新證》同《漢書新證》一樣,也是運用文獻與文物考古相結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領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國維提出,被稱作“二重證據法”,見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證》。同時王氏又在其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的演講中,說了如下膾炙人口的話:“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后,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陳先生研究《史記》、《漢書》的方法,正是繼承了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法,並有新的發展。對此,著名學者李學勤研究員曾作總結說:
我們知道漢代文物極為零散繁多,真是所謂片磚殘瓦,散金碎玉,而陳先生卻積幾十年的功力,加以彙集萃聚,一一與文獻相印證,為漢代研究別開生面。如他自己所說,這一新道路,“為推陳出新者所讚許,為守舊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計已。”他開拓的道路,已為學術界大多數所肯定了。這正是把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做了進一步的發揮,從而取得豐富的成果[4]。
上述陳先生關於《史記》、《漢書》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漢史領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這些新突破的獲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在擴大資料來源方面,他獨闢蹊徑,創新最多,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
先行者
1.
先行者
一般認為,歷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論取向,始於20世紀60年代崛起的美國的激進派史學家[5]。例如吉諾維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騰吧,約旦河,奴隸創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書,以奴隸為主體,論述他們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生活習俗、食物衣著、娛樂活動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個方面,進而展現美國特有的奴隸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學理論,則強調共同的工人文化對整個美國歷史的影響和作用[5]。另外,被稱為歷史多元論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國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種工人、農民、囚犯、婦女、移民等社會下層民眾為中心來考察和解釋整個美國的歷史[6]。這種“自下而上”的理論,近年來無論在國外抑或在國內都頗為流行,被許多史學工作者奉為圭臬。其實,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後新中國的史學實踐中早已存在;此中,陳直先生的秦漢史研究即是這方面的典型,只不過以往人們沒有把它提到應有的高度去認識罷了!
1958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直所著《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一書,由《西漢屯戍研究》、《關於兩漢的手工業》、《鹽鐵及其他採礦》、《關於兩漢的徒》、《漢代米穀價及內郡邊郡物價情況》等五篇論文組成。此書除了體現陳先生將文物考古資料與傳統文獻資料相結合的治學特點之外,最大的一項宗旨,即“發揮兩漢人民在手工業方面的高度成就”[7]。這種“發揮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應該說同國外史家倡導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事實上,陳先生這一撰史宗旨,在《兩漢經濟史料論叢》出版之前,就已經付諸實踐。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兩漢工人的形態》[3],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上的《漢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漢史的論文,便是很好的證明。
1980年,經過增訂的《兩漢經濟史料論叢》,由陝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訂版較初版增加了《兩漢工人的類別》、《兩漢工人題名表》等一文一表,從而更加突出了全書的主題。對於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評述指出:
《兩漢工人的類別》與《兩漢工人題名表》,乃作者獨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基礎上,將兩漢工人劃分為官府手工業及私人作坊兩大類,分別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藝的發展與提高、工官設置、工人範圍的擴大、官府手工業鑄器存在的問題、分工問題、畫工寺工供工並工問題、工官署中主要器與兼作器的區別、官民工互助、京師考工令撥工幫助郡國、大司農工巧奴、官工兼多門技藝、一工兼兩工、漆工工令、工人題名次序稱呼位置諸問題、義工輩工傭工等多方面的內容展開了論述。文中作者高度稱讚了工人的創造性勞動,歌頌了他們的高貴品質和團結合作的精神,尖銳揭露了當時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會不合理現實,並對士大夫賤視工人現象作了批判。後者收集了漢代工人題名三百一十六個,其中見於文獻者僅十餘人,其餘皆從出土古物中發現。表中詳細羅列了工別、籍貫、時代、題名作品及所見著錄等情況。古今中外史學家當中,如此精心為工人樹碑立傳者,實不多見[2]。
應該說,上面的評述至今仍不失其價值與意義。實際上,這也反映了陳直先生秦漢史研究的另一大特點。
其後不久,陳先生在寫給一個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這種發揮人民高度成就、為工人樹碑立傳的撰史宗旨,概括為“搞人民史,搞手工業史,不搞帝王家譜”等幾句話[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們的研究取向時,其切入點可能不盡相同,其具體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後的結論上每每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陳直先生的“搞人民史”,與國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謂之適例。二者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從時間上來看,陳直先生顯然應該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陳直學
1.
陳直學
已故的秦漢史專家林劍鳴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們說過:日本學者出於對陳直先生學問的欽佩與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陳直學。對此,我雖然沒有直接看到過有關的文字材料,但從日本學術研究最高獎“學士賞”獲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漢法制史研究》中譯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講的一段話:“當筆者年輕的時候——如果那時的中、日關係和今天一樣正常化,並有可能到中國來留學的話,我一定會到西北大學來投到陳直教授的門下”,以及給陳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稱等情況來看,陳先生在日本學術界確乎享有極高的威望,林劍鳴教授的說法,當有所據。我想,這裡暫可不管國外學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經建立陳直學的問題,倒是我們中國學人自己需要認真考慮這一關乎學術發展的大事,尤其是陳先生生前供職的西北大學及他的受業弟子們,更是責無旁貸。故筆者願藉此紀念陳先生逝世20周年暨誕辰100周年的機會,就“陳直學”來談點淺見,以與對此感興趣的國內外學界師友,共同探討。
所謂陳直學,應該是這樣一種概念:即以陳直先生的治學思想為主線而形成的一種研究中國古史,特別是秦漢史的科學方向。陳先生的治學思想,具體包含這樣三個既彼此區別,又緊密關聯的方面:一是“使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業史”[2]。關於上述的三個方面,我曾分別做過如下的闡釋:
——“使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既是一種研究的方法,同時也體現了一種史學思想。它的要義,陳先生曾多次論述。例如《漢書新證·自序》講:“使考古為歷史服務,既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停滯於文獻方面。”《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自序》講:“力求使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合為一家,使考古資料為歷史研究服務。”《關於兩漢的手工業》一文開頭講:“題目建立在歷史上,證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單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為考古而考古,意在將歷史與考古二者合為一家,使考古為歷史而服務。”在中國學術界,如此旗幟鮮明地倡導這一思想方法的,陳先生是步王國維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終生為此而奮鬥。特別是他五十歲之後,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覺地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從事歷史研究,從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顯示了特色[2]。
——如果說陳先生關於考古為歷史研究服務的思想,較多地帶有方法論的色彩的話,那末,他關於寫人民史的主張,則完全是一個哲學式的命題[2]。
——究竟誰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將相,還是廣大人民群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反映著歷史學家的立場與識見。當然,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不等於否定帝王將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更不等於不需要研究帝王將相。在這樣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上,陳先生的態度是鮮明而堅定的[2]。
——陳先生寫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業史”的主張相輔相成。通過探討手工業的發展情況,展示勞動人民的巨大創造力,表現他們的聰明才智,從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眾是歷史主人的真理。這樣,寫人民史也就有了具體的落腳點,而不致只是一句時髦的空言。這裡,自然還要看到,寫人民史,搞手工業史,均需遵循“使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的原則[2]。
顯而易見,在陳直先生的治學思想中,“使文獻與考古合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業史”是研究落腳點。三者渾然一體,構成完整的研究秦漢史的科學方向——也就是我們所講的“陳直學”。研究者沿著這一方向,如同陳直先生那樣,不為功名利祿所誘,不為燈紅酒綠所動,踏踏實實一心研治學問,必然會達到史學的頂峰。
也許有朋友會問,作為“科學方向”,“搞手工業史”的提法是否有點太狹窄了?難道諾大的秦漢史除了“手工業史”再沒有其他內容么?其實,陳先生的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友人向陳先生說,秦漢的手工業,幾乎無話可講,尤其東漢是空白點。陳先生不以為然,指出:“兩漢手工業在文獻上記載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卻很多,試看兩漢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經過手工業的過程?”[7]於是他運用文獻與考古相結合的方法,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奇迹出現了。原來被學人認為無話可講的兩漢手工業,在他的筆下,竟洋洋洒洒寫出了近10萬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中的《關於兩漢的手工業》一文。這是研究兩漢手工業的權威之作,以後凡研究漢代手工業者,均不得不以它為基礎。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歷史背景,那末,對陳先生所提的“搞手工業史”,將會少去許多異議。實際上,這一提法並不排斥對其他方面的研究。
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時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諱言,在陳直先生那些足以傳世的著述中,失誤之處也是存在的,對此,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於學術的發展與進步。學術領域,以追求真理為惟一目標,這裡需要學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學術詰難與學術批評,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諛奉承。我想,作為一代宗師的陳直先生,其在天之靈是會歡迎大家對他批評指正的。這類批評不僅不會影響陳直先生所開闢的學術研究方向的正確性,相反,倒是陳直學在新條件下的發展與完善。
【參考文獻】
[1]陳直.摹廬叢著七種[M].濟南:齊魯書社,1981.
[2]黃留珠.陳直先生治學精神與思想初探[A].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編.陳直先生紀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3]《晉陽學刊》編輯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李學勤.陳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編.陳直先生紀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5]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6]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7]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