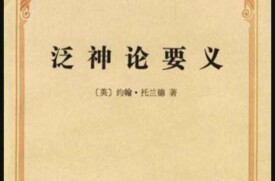泛神論
泛神論
泛神論(pantheism)是指把神和整個宇宙或自然視為同一的哲學理論,即太一論。
泛神論是東方最古老的思維,其認為神就是萬物的本體,“自然法則”是神的化身,這是宗教信仰種類之一,謂宇宙間只有一個長住不變,自有永有,絕對永恆的“本質”。其否認運動是物質的固有屬性,物質的客觀實在性,萬事萬物不斷發展的多樣性,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無神論講究實事求是、客觀公正、有理有據,承認且科學探尋物質世界;有神論之宗教並無說服力且不可證偽,故最符合邏輯的結論即是起源於內心構建以精神寄託或對解脫死亡的嚮往。由於政教分離原則,也為了確保科學教育體系不受影響,絕大多數國家對宗教會採取無神論或中立態度;政教合一國家對宗教採取有神論態度。
泛神論,一稱萬有神教即太一,謂宇宙間只有一個長住不變,自有永有,絕對永恆的“本質”( essence)或有限之物(finite things),萬殊變遷,其本身並無真正的存在,印度教稱為幻影(maya)。此派反對超越神論,否認神的位格,以及上帝創世之說,謂有限之物,乃出自無限,非由於創造。蓋自無限出有限,乃為一種內在的原則,此即上帝。有限無限,均屬一源,故宇宙非上帝所創造,上帝即寓於宇宙之內。
在大部分人的思想當中,尤其宗教信徒,都以為宇宙存在一種萬能的力量,一種大能,它是這種萬能的力量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我們,而如果想解脫,必須要回歸這種萬能的力量,或者認識它,臣服於它。基督教的上帝是這種萬能力量的人格化,印度教的梵,道家的道是這種萬能力量的非人格化(印度教裡面也有一部分是人格化梵)。這個世間只有一種宗教徹底否認存在這種人格化的萬能力量,它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的獨特之處就在於無我論的提出,"我",巴利語是Ataman,它的原義是恆常,主宰的意思,而佛陀說沒有Atman,即沒有主宰,沒有“我",沒有萬能力量。然而Ataman這個詞經過中國人的翻譯以後,失去了原義,很多所謂的佛教信徒甚至把不自私,把泛神論的萬物一體乃至不二論等當成了無我,卻承認存在有萬能的力量,存有主宰,與真正的佛法完全背道而馳。
泛神論是一種將自然界與神等同起來,以強調自然界的至高無上的哲學觀點。其認為神就存在於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並沒有另外的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這種觀點曾流行於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西歐,代表人物有布魯諾、斯賓諾莎等。
從泛神論又發展出泛自然神論(Pandeism),這是將自然神論和泛神論合併起來的一種哲學觀點。這個觀點認為上帝在創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規則之後,將自己化身成宇宙以及世界萬物。泛自然神論起源於19世紀的德國的哲學思想界。
在2001年,漫畫跟書籍系列呆伯特(Dilbert)的作者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出版了《上帝的碎片》(God’s Debris)一書。在此書中,他建立了與泛自然神論相關的一種哲學觀點。泛自然神論的觀點在盤古神話中有所體現。在大部分關於盤古的傳說中,都有如下內容:
東方神話傳說:“盤古死去,身上的器官變化成天地間的萬物:身體變為高山,肌肉變成良田,血液成為江河,筋骨變成大路,牙齒變為玉石,皮毛變成草木...”
代表人物就是莊子、斯賓諾莎和色諾芬尼。
“仁義”二字被視為儒家思想的標誌,“道德”一詞卻是道家思想的精華。莊子的“道”是天道,這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為的殘生傷性的。
在莊子的哲學中,“天”是與“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天”代表著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為”的一切,與自然相背離的一切。“人為”兩字合起來,即是一個“偽”字。
莊子主張順從天道,而摒棄“人為”,摒棄人性中那些“偽”的雜質。順從“天道”,從而與天地相通的,就是莊子所提倡的“德”。
在莊子看來,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導什麼,規定什麼,而是要去掉什麼,忘掉什麼,忘掉成心、機心、分別心。既然如此,還用得著政治宣傳、禮樂教化、仁義勸導?這些宣傳、教化、勸導,莊子認為都是人性中的“偽”,故要摒棄它。
作為道家學派始祖的老莊哲學是在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唯一能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學說分庭抗禮的古代最偉大的學說。它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的地位絕不低於儒家和佛家。
色諾芬尼(約公元前570年~前480年或470年,或公元前565年~473年),古希臘哲學家、詩人、歷史學家社會和宗教評論家,埃利亞派的先驅。色諾芬尼認為神是宇宙的永恆原則,它是所有事物都存在於其中的“一”和“一切”。換句話說,神就是世界,他並不是純粹的精神,而是整個有生命的自然。色諾芬尼將神與世界統一,這一泛神論的重點不在於神,而是在世界上。
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著名的荷蘭哲學家。其本為猶太人,猶太教會以其背叛教義,驅逐出境,后卜居於海牙,過著艱苦的生活。其不承認神是自然的創造主,其認為自然本身就是神化身,其學說被稱為“斯賓諾莎的上帝”,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和德國的啟蒙運動有著頗大的影響,同時也促使了唯心到唯物,宗教到科學的自然派過度。
道教是道法自然,道家信徒強調的是修仙而不是拜神,其是跟著榜樣學習而不是崇拜榜樣。仙是一種自由的狀態,佛和道之所以能融合,這是因為二教都不承認萬能的神,只承認“神通”,其本質上是修鍊得到的一種技能,不是與生俱來的,有了雜念和惡行之後還會失去。由於沒有神通,在道家來看就沒有自由,無法逍遙,在佛家來看,它是覺悟后自然而然具有的一種屬性,而且有利於弘法,故道家要修仙練神通,佛家說覺悟之後就會有神通。這時,雖然有了生物與非生物區別,但是道教認為非生物可通過注靈或點化賦予生命修仙,生物則可自修成仙。
在老子看來,“道”,從道體的角度來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我們是根本無法表述,甚至是我們根本無法了解的。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有這麼個東西,它先天地而生,可卻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捪之而弗得。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正像普羅提諾對於太一的描述一般,它是超越於世界萬物之上、超越於人類的理性之上、超越於我們的感官體驗之上的。因此,對於“道”究竟是個什麼東東,我們除了可以說它是我們的語言無法描述的之外,我們對它無話可說。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之上,我們所說的“道不可言”才有意義。
同時,對於“道”的特點、“道”的作用、我們如何認識“道”、如何因循“道”,對於老子來說,都沒有任何的不可說,甚至要大說特說。並且,對於這些關於“道”用的內容,老子完全是用了一種合乎人類的正常智慧、常規理性的方式來進行論述的,其中絲毫未見任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拿著拐棍敲你腦袋三下關上正門讓你去悟的所謂境界。
老子的“道”是我們能夠感知,能夠了解,能夠傳授的;老子的“道”是我們可以掌握、運用的;老子的“道”是要求我們堅定不移的葆守執持,以指導我們的行動的;老子的“道”是適用於人主治理天下的過程中的,在人主治理天下的過程中,所取法於的正是“道”;老子的“道”,人主一樣會失去它。當人主不能按照“法道”的原則,當人主不能因循“天之道”生養、輔助萬物的規律去從事的時候,人主便失“道”了。
莊子也繼承了老子的思想,據傳,又嘗隱居南華山,故唐玄宗天寶初,詔封莊周為南華真人,稱其著書《莊子》為南華經。據《莊子》記載,莊子住在貧民區,生活窮苦,靠打草鞋過活。《史記》中記載,莊子曾在家鄉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官,在職不久就歸隱了。楚威王聞知以厚幣禮聘,被莊子拒絕,在當時學者名人中,他和惠施經常往來,《莊子》書中有不少他和惠施進行討論、爭辯的故事。莊子對現實十分悲觀,消極厭世,對整個人生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罰,他認為仁義是一種黥刑,它是非是一種劓刑。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和獨特的學風、文風。莊子用相對主義的理論回答了先秦哲學中“天人”之辯和“名實”之辯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莊子和老子一樣把“道”作為世界最高原理,講天道自然無為。但在“道”和“物”的關係上,他具有與老子不同的明顯泛神論色彩。他認為形體產生於精神,而個別精神產生於“道”。在莊子哲學中,“道”是宇宙的本體,它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由“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道”本身是萬物之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人如果得“道”,即獲得了無限和自由。
印度教中,梵與“我”或“彼一”,都是古印度所指的終極實在,它是超越和不可規範的唯一實在,多通過否定(非……,非……)加以講述。《奧義書》和其後的各正統學派在通過否定后,正面斷定“梵”與“我”的存在,而且是唯一、不二的存在。這種終極觀是實體性的,在思想的最高位置。“梵”是“非概念”的,超越一切名相概念和判斷推理,不能靠思辨體驗,只能通過瑜伽直接體驗。梵我無處不在,現世只是“終極實在”一種扭曲、不充分的表現,追求梵我時必須捨棄與現世的根本聯繫。婆羅門教視現世是不真的,但亦明白表達在一切無常無我之上,有一個肯定性的梵我境界。視世間為“假立”;僧佉(數論)以梵為自性,視世間為現象,都是以梵為宇宙的本體。”又佛為婆羅門又稱梵,清凈者之意也。俱舍論二十四曰:“真沙門性,經亦說名婆羅門性,以能遣除諸煩惱故。佛與梵德相應,它是故世尊猶應名梵。由契經說,佛亦名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