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主義
基督教教派正式的或民間的信仰
千禧年主義是某些基督教教派正式的或民間的信仰,千禧年是人類倒數第二個世代,是世界末日來臨前的最後一個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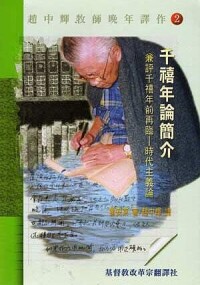
千禧年主義相關書籍
中國歷史上的千禧年主義
一些人相信在千禧年到來和世界末日到來之前將會有一個短暫的與撒但或是敵基督交戰的時期,之後就是最後的審判。千禧年主義亦是明教關於一千年觀念中的教條,明教認為每一個千年循環都是在異端和毀滅性的大災難中結束,直至最後一個禧年邪惡的大破壞與最終和平之王戰勝邪靈后結束(一些人相信是2000年)。
某些基督教徒所抱有的一種新年,謂在基督復臨之前或者緊隨其後,將要出現1000年的聖徒統治。這種信念通常以《啟示錄》第20章1-7節為依據。
基督教的主體從未認可千禧年主義,但是從基督教初期就有許多信徒宣講它。
而在19世紀啟示論和千禧年主義思想重新興起,例如普利茅斯兄弟會和基督復臨派。
在20世紀後半葉,千禧年主義一詞由社會科學家所採用,含義也有所引申,指期待世界及早突然發生變化的任何宗教群體。這類派別往往興起於重大社會變動或社會危機之時,其爭取目標往往是推進某種受取締的社會群體,如美拉尼西亞群島的貨物崇拜。
關於世界終末的思想,是否西方特有,與中國的思想和歷史沒有關係?近些年來,在美國和日本的漢學研究界出現了一種動向,將西方千禧年主義(Chiliasm或millenarianism)的思想觀念用於研究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思想乃至歷史上的各種民間"起義"。當代漢語學界一早就關注漢語思想傳統中的所謂烏托邦思想,直接的觸發因素還不是毛澤東主義具有的烏托邦精神,而是康有為這樣的儒教左派--公羊學派的"大同"思想。事實上,人們不需要如何費勁,就可以從原始中國思想中找到烏托邦思想的要素和相關語詞。可是,如今人們發現,千僖年主義並不就是烏托邦思想。烏托邦思想提供的是保證人人可以分享的幸福世界景觀,千禧年主義刻寫的是為了世界的終極轉變清除某些人的生命(遑論幸福)的終末時刻。烏托邦思想關注描繪理想的、甚至靜態的生存狀態--所以Ralf Dahrendorf稱烏托邦思想是"靜態思維",與此相反,千禧年主義關注世界終極轉變的激蕩狀態--善與惡、天使與魔鬼、光明與黑暗的之間combat(交戰)狀態。這樣的狀態有如CarlSchmitt的Ausnakmezu-stand(例外狀態)或Emstfall(緊急關頭),死上無數條命是必須的,遑論他們的幸福?在這樣的狀態中,甚至以不殺生為第一戒律的佛教徒也必須"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護法優婆塞等,應執刀杖擁護如是執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十二)"烏托邦思想關心超逾了現世的理想狀態,至於這個現世世界是否出現了緊急關頭,反倒極其冷淡,有如莫爾在《烏托邦》中勸已經不治的病人最好"自己斷食"、或者"讓其安睡"。千禧年主義牢牢記住的是這個世界已經病入膏肓,新世紀急切地就要來臨。並非如某些學者(如日人三石善吉)所說的那樣,烏托邦思想是菁英知識人的理想國,千禧年主義是遭遇現世損害的平民百姓的"起義"熱情。菁英知識人或遭遇現世損害的平民百姓都可能具有烏托邦思想或投身千禧年主義的爭戰。可以說,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烏托邦思想渴求幸福,千禧年主義渴求正義。在古老的千禧年主義中不僅有急迫的終末論,而且有嚴峻的神義論,烏托邦思想就並非如此。千禧年主義的末世景觀中的緊急關頭要命的時間緊迫感全然來自神義的忿怒,近代以來,神義的忿怒變成了人義的忿怒,仍然沒有改變這種思想的基本結構。在歷史中,千禧年主義的熱情大多還是蘊藏在知識人,而非平民百姓身上。平民百姓從來就是被動員的政治對象,千禧年主義的知識人熱情僅需要到平民百姓身上尋找現世的不滿,再從政治上把它納入千禧年主義的末世景觀。
annis(作王一千年)這樣的理念在形式上的對應提法,恐怕不會有什麼指望。比較文化研究中的相反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即便像一些比較研究者那樣找出了兩種文化思想中的相同語詞或觀念,並不等於其含義就是相同的。相反,人們倒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同民族文化都共有的思想類型,或Max.Weber所謂的"理想類型"。於是可以問,千禧年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方式,是否可能在中國思想中找到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千禧年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思想方式,或者問,具有怎樣的思想結構。
千禧年主義給人帶來的首先是大災變臨頭的時間感,就好像中國人熟悉的所謂"閏八月",在這樣的年分中,必有災難和變局發生。不過,在"閏八月"的緊急關頭時間意識中,並沒有確定"義"(Gerechtigkeit)的問題,災變之後是否一定會有幸福王國(就算這僅是一個朝代的想象罷)出現,並不確定、也是未可知的。千禧年主義的大災變一定是一個嶄新世界的前兆,在大災變中的聖者一定自稱知道有"義"的千年王國正在走來。《啟示錄》不僅顯示了由獸支配的人間可怖的社會政治狀況、上帝的忿怒以及降至人間的災異(啟6:1-16:21),而且出現了對抗可怖的人間狀況中的惡的聖者,他們是即將出現的千年王國的擔綱者(啟14章)。的確,這樣的思想觀念中國人倒不陌生:在時世艱難的時期,總有聖人出現要替天行道。不過千禧年主義的聖者不是少數人的菁英群體,而是數量可觀的聖潔信眾(十四萬四千人)。於是出現了善與惡的爭戰--千年王國來臨之前的大決戰(啟16章)。千年王國是為"神與人共住,人為神之民"的終極性新天地出現作準備的,因而大決戰本身也是終極性的。由於千年王國催生的決戰是在現世中發生的,千年王國並不就等於天國(新天新地)本身,大決戰就是現世歷史中的最後決戰和最後審判,終極狀態的絕對完滿性已經通過聖者的爭戰多少體現出來了。千禧年主義的歷史時間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神跡性的:此世的自然時間發生了終末性的突然中斷,是神義力量作用的結果--所以才有自然災變的發生。
可以發現作為一種思想方式的千禧年主義具有這樣的觀念結構:現世生活世界出現終極斷裂以便向新天地絕然轉變,在轉變過程中出現自然災變和聖者群體為新天新地的到來而展開對惡勢力的爭戰。現世的人被分成了屬於惡勢力的和屬於善勢力的兩類。這種劃分是因為那些自己感覺為現世中的屬靈者通過靈智感到真正的福社和公義已經等待得不耐煩,時間急迫,有必要在這終末時刻展開一場屬於"你死我活的鬥爭"的現世清洗。相當重要的是:這一切都以一個新天地的出現為前提,只不過在古老的千禧年主義中,這個新天地是由超越的神義論(Theodizee)保障的,在現代千禧年主義中是由人義論(Anthrodizee)來保障的。
在中國古代儒教的革命改制或"受命"改制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千禧年主義的某些類型特徵。無論革命改制還是受命改制,說的都是一代新聖王興起取代舊聖王,其時有災異出現,有"維天降紀",天帝命龍馬神龜賜河圖洛書之類,賦予聖者轉變現世生活秩序的正當法權。革命或受命的轉變需要托天帝的賜"命",革命者或受命者必須自居聖人(有德),在現世秩序的轉變中免不了要出現的爭戰也得神聖化。這種"受命改制"的思想並不是儒教專有的,據稱支撐當年黃巾起義的道教經籍《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中就有"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漢書·李尋傳》)。在重新"受命"之前的緊急關頭,難免"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可驚訝的,因為隨後就將出現"天下大吉"的"太平世"。
然而,中國古代思想中政治高層和社會底層都可以利用的革命改制論或受命改制論,在時間轉變的終極性上無論如何不能與西方的千禧年主義相比。"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習傳知識,使得現世生活世界的時間轉變不過是歷史周期性反覆出現的朝代時刻,而非歷史的終末時刻。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古代思想中的上帝觀念不是絕對"義"的超越者,此世與天帝之間不是像猶太-基督教的的上帝與其從絕對虛無中創造出來的此世之間那樣,有絕然斷裂的二元關係。千禧年主義歷史時間的轉變之所以可能成為終末的轉變,乃因為上帝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這個此世根本沒有自身的自在性。Karl Lowith的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te(《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透析過的古希臘的循環歷史觀念與猶太基督教的斷裂歷史觀念的差異,在這裡同樣適合中國思想中的歷史觀與猶太-基督教歷史觀的差異,只不過兩者的根本差異不在於前者是所謂"順進式"、後者是"倒進式",而在於那更為根本的Genesie(創世紀)。
儒教公羊學派的三世論提供了通過"據亂之世"、"昇平之世"進入"太平之世"的終局性歷史時間演進觀念,但這種觀念中的現世秩序的轉變反倒不如革命或受命說來得強烈。況且,三世之說一直沒有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法理和歷史哲學法理的主導性觀念。董仲舒是公羊學派的早期大師,他的政治-歷史法理卻是五德相勝的輪轉學說,這種學說無法得出終末轉變的政治-歷史法權。三世說經何休確立時,公羊學派已經失去勢力。從思想方式的結構和思想歷史兩方面來看,三世論與受命論是兩種不大相干的思想,前者是民族文化主義的歷史哲學,後者是現世統治秩序更迭的政治法理。如果受命論或革命論更迭現世秩序的政治法理與三世論的終末性歷史哲學相融貫,成為負有某種宗教或民族文化使命的終極性的受命論或革命論,就可能出現地道中國的千禧年主義。這種情形恰恰在近代中國與西方思想的接觸中發生了,而且不止一次。洪秀全的受命論與道德途說的基督教終末論結合起來,為太平天國運動提供了"奉天誅妖"之檄,接下來是晚清新公羊學派復興與三世說與西方世俗化的千禧年主義的融貫,然後有儒教馬克思主義推動的終極性革命運動。儘管千禧年主義在中國古代思想中顯得不如莫教授描述的西方情形那樣來得強烈和源遠流長,作為一種思想方式,畢竟可以在革命或受命論以及三世論中。發現某些基本的相同思想要素。一旦歷史提供了契機,千禧年主義就會成為漢語思想的酵素,創造性地轉化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那樣的現代儒教式千禧年主義的時間感覺。
千禧年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唯靈主義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的諾斯替主義(靈智主義Gnosticism)。本來只涉及個體生命得救的聖靈信仰,首先在《啟示錄》中、隨後在Joachim的聖父-聖子-聖靈的三段論政治歷史觀中轉變成了政治的彌賽亞主義。在我看來,文化大革命同樣屬於Eric
Voegelin所深刻論述過以列寧革命為代表的現代政治諾斯替主義運動,這種運動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還有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Isaiah Berlin問道:"今天誰能說希特勒完全失敗了?他僅僅統治了十幾年,在這段時間裡他給其屬民的生活觀念和生活結構造成的變化,歐洲最大膽的歷史學家和正直思想家也難以想象。"我們有過中國式的政治諾斯替主義運動,已經不可能把千禧年主義當作與已無關的西方問題來看待,即便人們可以說,傳統中國思想中根本沒有這種東西,然而我們畢竟已經有過了。
從思想方式來看,無論哪種千禧年主義,其基點都是新的開端的必然性(神義的作用也罷、歷史的規律也罷)。不僅朋霍費爾在走向弄場時會說,"終點對於我是開端",為"主義"獻身的黨人在走向刑場時同樣會說、而且事實上也說過類似的話。這迫使我們懷疑基督教的終末論與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義的差別在於"開端"與"終末"。實際上,基督教的終末論與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義終末論都基於對新的開端的信仰。千禧年主義源於《但以理書》,經新約《啟示錄》傳揚光大。但福音書的終末論與此完全不同,終末就在耶穌基督的"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約4:23;5:25)。基督教終末論與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義終末論對新的開端的信仰不同,基督的終末帶來的是現世中的新時間,上帝國已經通過基督的身體臨世。莫教授說得好:"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帶著問題死的。"我還想說,基督是帶著自身的困苦走上十字架的。在十字架上,耶穌作為上帝的兒子對天父喊道:"我父,你為什麼離棄我?"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耶穌作為人的兒子對自己的母親喊道:"看,你的兒子:……我口渴!"這樣的上帝帶來的終末既不是清洗此世的命令,也不是教人冒充救世主對自己在此世的鄰人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對自己的天父說的"成了",而是基督與"世人"一同受苦的愛。基督教終末論的新正是基督臨世受苦和受死的愛,而不是一場終極性的決戰。基督教信仰的終末以耶酥基督的"我口渴!"和臨刑的"我父,你為什麼離棄我?"而與所有千禧年主義區別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