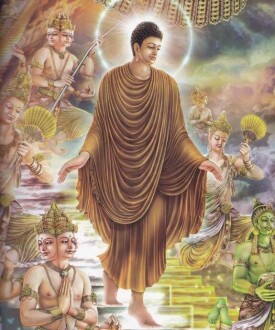支謙
三國時佛經翻譯家
支謙:三國時佛經翻譯家,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詳(約3世紀)。本月氏人,其祖父法度於漢靈帝時率國人數百移居中國,支謙隨之俱來。受業於支讖門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謂。東漢末,遷居吳地。因聰明超眾,時人稱為“智囊”。吳主孫權拜其為博士,輔導太子孫亮。從吳孫權黃武二年到孫亮建興二年(公元223-253年),約三十年間,譯出佛經《大明度無極經》、《大阿彌陀經》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創作了《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其翻譯以大乘“般若性空”為重點,為安世高、支讖以後譯經大師。
他的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氏族後裔。他從小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精通漢文,后又兼學梵書,受業於同族學者支亮,通達大乘佛教理論。他對從前那些過分樸質以致隱晦義理的譯本很不滿意,因此翻譯佛經時主張“尚文”和“尚質”要調和。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來說,由質趨文,乃必然之勢;支謙則風氣之先後世。支敏度評價他的翻譯︰“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僧肇認為他的翻譯“文勝於質”。但僧肇的老師鳩摩羅什翻譯《維摩經》時,大篇幅引用支謙原來的譯本。
漢獻帝末年,洛陽一帶發生兵亂,他隨族人避亂南渡到東吳。在那裡他得到從事翻譯的機會,從吳黃武元年到建興中約三十年間(223—252)搜集了各種原本和譯本,未譯的補譯,已譯的訂正。對《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等重要經典,直接加以重譯。同時他又幫助從印度來華的維祇難和竺將炎譯經。傳說他到東吳后曾得到吳主孫權的信任,叫他輔導太子孫登:後來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過隱居生活,年六十歲卒于山中。
支謙的譯述比較豐富,晉道安的經錄里就著錄了三十部,梁僧佑又據《別錄》補充了六部。慧皎《高僧傳》說有四十九部。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旁搜雜錄增廣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別生或傳抄的異本,不足為據。
現經考訂出於支謙翻譯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1、《阿彌陀經》(又稱《無量壽經》)二卷,2、《須賴經》一卷,3、《維摩詰經》二卷,4、《私訶末經》一卷,5、《差摩羯經》一卷,6、《月明童子經》一卷,7、《龍施女經》一卷,8、《七女經》一卷,9、《了本生死經》一卷,10、《大明度無極經》四卷,11、《慧印三昧經》一卷,12、《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13、《菩薩本業經》一卷,14、《釋摩男經》一卷,15、《賴吒和羅經》一卷,16、《梵摩渝經》一卷,17、《齋經》一卷,18、《大般泥洹經》二卷,19、《義足經》二卷,20、《法句經》二卷,21、《佛醫經》一卷,22、《四願經》一卷,23、《阿難四事經》一卷,24、《八師經》一卷,25、《孛經鈔》一卷,26、《瑞應本起經》二卷,27、《菩薩本緣經》四卷,28、《老女人經》一卷,29、《撰集百緣經》七卷。
在這些佛經里《了本生死經》,據道安的《經注序》說,原來是漢末譯出,支謙加以註解或修改,道安的經錄便又將它列在支謙譯本之內。黃武三年(225)支謙曾請竺將炎譯出維祇難傳來的略本《法句經》(五百偈本),後來又請他根據中本(七百倡本)加以補訂,其間自然也有支謙參加的意見,所以可說是支謙和竺將炎的共同譯本。其次《佛醫經》,情況也相同。另外,《歷代三寶記》載有支謙所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並加註說:‘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別錄大概泛指另外一種記錄,決不會是劉宋時代的《別錄》,因為僧佑著作《出三藏記集》時,曾見過《別錄》,並將其中所載的支謙譯本都收在《記集》里,卻沒有提到這樣一種《四十二章》。所以支謙是否重譯過《四十二章經》尚有疑問。最後,《菩薩本緣經》(始見於《歷代三寶記》)和《撰集百緣經》(始見於《大唐內典錄》),雖然原始的記錄出處不明,但從譯文體裁上看無妨視為支謙所譯。
支謙除翻譯外,還作了合譯和譯註的功夫。他曾將所譯有關大乘佛教陀羅尼門修行的要籍《無量門微密持經》和兩種舊譯(《阿難陀目怯尼呵離陀鄰尼經》、《無端底總持經》,現已不存)對勘,區別本(母)末(子),分章斷句,上下排列,首創了會譯的體裁(後來支敏度的合《維摩》、《首楞嚴》,道安的合《放光》、《光贊》,都取法於此)。支謙自譯的經也偶爾加以自注,像《大明度無極經》首卷,就是一例。這種作法足以濟翻譯之窮,而使原本的意義洞然明白。
支謙又深諳音律,留意經文中讚頌的歌唱。他曾依據《無量壽經》、《中本起經》創作了《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傳了。後來連《共議》一章梵唄也絕響了,現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無量壽經》里法藏比丘贊佛的一段和《瑞應本起經》里天樂般遮之歌及梵天勸請的兩段而已。他這一創作對讚唄藝術的發展有相當影響。被稱為始制梵唄的陳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啟發而有《瑞應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構,成為學者之所宗。
支謙翻譯的風格,對後來佛典翻譯的改進,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對譯文尚質的偏向,主張尚文尚約應該調和。這當然是為了更好的暢達經意使人易解的緣故。深知翻譯甘苦的人,像後來的支愍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給予他的翻譯文體的評語是:‘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了原文本意,譯文就難恰到好處。看他所改譯的《大明度無極經》,對般若‘冥末解懸’的宗旨是比支讖《道行》更能闡發的。他用‘得法意而為證’等譯語,雖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說法,但般若‘不壞假名而說實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經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說‘由言證己,當還本無’。本無即指的實相)。他翻譯的《維摩詰經》,充分表現了大乘佛教善權方便以統萬行的精神。後來羅什門下雖對他的翻譯還嫌有‘理滯於文’的不足處(見僧肇的經序),可是仔細將羅什重譯的《維摩經》相對照,不少地方都採用謙譯,述而不改,足見支謙譯風已遠為羅什的先驅。不過,在拘泥形式的學人看到支謙盡量刪除梵本的繁複而各取省便,又竭力減少音譯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時連應存原音的陀羅尼也意譯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後來道安就說他是‘斲鑿之巧者’,又以為‘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這是從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來說,由質趨文,乃是必然的趨勢;支謙開風氣之先,是不能否認的。
另外,支謙的譯文風格也很適合於佛傳文學的翻譯,因而他繼承了漢末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那樣‘奕奕流便足騰玄趣’的傳統,更翻出了《瑞應本起經》。這一翻譯不但豐富了佛傳文學的內容,而且通過讚唄的運用影響到後來偈頌譯文的改進,也是值得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