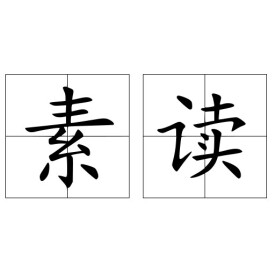素讀
素讀
素讀是日本人對古代私塾教學方式的定義,即指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將其反覆誦讀,爛熟於心,從而達到夯實文化根基的目的。強調以記憶學習為中心,反覆朗讀。
在閱讀或觀賞時不加以任何個人的偏見或喜惡,平和地完成,以更好的悟出原作者的思想和訴求!
素讀是日本人對古代私塾教學方式的定義:不追求投入理解,只是將其反覆誦讀,爛熟於心。
日本人把人們那種私塾授課方式定義為“素讀”。日本右腦開發專家七田真在《超右腦照相記憶法》的“第五章——教育的原點是背誦和記憶”里這樣論述:“‘素讀’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讀內容的含義,只是純粹地讀。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這樣按字面來教孩子‘素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的。”他還說:“這種不求理解、大量背誦的方法是培養天才的真實方法,也就是右腦教育法。猶太教育培養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的教育就是以記憶學習為中心,強調反覆朗讀。”
日本筑波大學的加藤榮一教授講述了一件事:“1991年3月1日。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會上遇到了創業家井深先生。本人向他請教‘使腦子變聰明的方法’。他回答說:就是要大量的死記硬背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素讀’——不求理解含義、只照著字面朗讀漢籍(即中國的經史子集)。戰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有10個人,他們全都作過這種‘素讀’練習。湯川秀樹先生從3歲就開始接受這種訓練了。”
“素讀”對人們民族的優秀人才有過怎樣的影響呢?遠的不說,單是20世紀前半葉的那一代文化人,哪一個不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錢穆9歲就熟背“三國”,除把“四書”全部“吃”到肚子裡外,還背熟了《朱子章句集》;楊振寧在初入中學時背誦過整本《孟子》……
但這種“素讀”經典的教育方式被歷史廢棄了。1912年1月19日,民國政府下令“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五四”運動以後,“四書五經”更是首當其衝被視為封建主義的糟粕而遭徹底批判。此後,入選中小學課本的都是大白話一樣的文選,自然不需“念經”似的記誦,以背誦為主要目的的“素讀”在課堂上就此式微。
不可否認.廢止讀經是歷史上的進步。但,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回顧母語教學之路.人們遠離經典的腳步是否該有所修正呢?
“五四”運動20多年後,朱自清先生已看到了拋棄“素讀”經典帶來的問題。他在《經典常談》中說:“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因此,他提出:“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而錢伯誠先生在給朱先生這本書的再版前言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經典訓練並不就是恢復讀經教育。恢復讀經教育是開倒車.這是‘五四’運動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一股腦兒反對讀經,走極端,棄之如敝履,造成文化的斷層.這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這卻是‘五四’運動未曾解決好的問題。”
足見.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接受本國經典的訓練是必須的義務。經典,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血液。
然而,對於尚未具備“相當教育”的中小學生而言.是否也有接受經典訓練的必要呢?時下不少人質疑,為什麼要讀那些距今已經一兩千年的經史子集?這是一個宏大的課題,非本人這樣一個小學老師的三言兩語可以說透的,姑且放下不論。但從母語教學的規律來看,答案非常明確:應該讀!
漢語的發展具有非常強的因襲性。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母語體系就已經相當完善了,語言的辭彙、詞性結構、句法結構以及音樂質感等各方面都已相當成熟。每一個讀過諸子百家典籍的人,無不被那精闢洗鍊、生動優美的語言文字所震撼。人們至今仍沿用的格言、成語等經典詞句大多數源自諸子百家典籍,漢語言活力的源頭就在經史子集的典籍里。單是這些典籍的語言風格,就足為後世的模範。比如有學者論述《孟子》的語言:“後來統治了本人國2000多年的標準書面語,在《孟子》那裡已經臻於成熟,並成為後世古文家絕好的典範。”人們現在所讀的白話文章,就語言文字而言,大都遠不及古代典籍那樣精鍊簡約、曉暢準確。
正因如此,古代私塾里提倡“素讀”就是“背”,是要求忠實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誦。整篇背誦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唐代詩人杜牧在《答庄充書》中論述:好文章是“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的。任何一篇好文章絕不是字詞句段的拼盤,可以隨意拆散組合,它是“意”、“氣”相連.受“兵衛”呵護而貫穿始終的。人們現在則是常常讓學生斷章取義地“選擇喜歡背誦的段落”,這種碎片似的記誦缺少整體意境,往往記得不深刻。因而,大多數學生對課文中的字詞句都沒有多少印象.只是了解內容.而難以達到對文意的深刻感受,更談不上對作者行文的“氣”勢參悟了。
再者,單從識字而言,人們知道一個人只要掌握2400個常用字就可自行閱讀。可是,人們現在要用6年的時間才讓學生學完2500多個漢字。按課時計,平均每天識字才一個多點。最可惜的是,6年後,一個人的閱讀興趣培養期已經錯過了,再補就為時已晚了。而古代私塾的“素讀”,不追求講解的精深透徹,學生有足夠的誦讀時間,在反覆的朗讀中自悟自得。那時選用的教材都是《三字經》、《弟子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聲律啟蒙》、《笠翁對韻》、《唐詩三百首》等韻文或詩詞,每個漢字都置於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學童在大量的誦讀中不知不覺熟知了文字的音、形、義,無須獨立識字。經口誦心惟的訓練,一兩年時間就可以認識大量的漢字,為早期的拓展閱讀和寫作提供了條件。比如一篇《千字文》,不用一個月學生就可背得滾瓜爛熟,文中只有6個字是重複使用過一次的。也就是說,不用一個月背熟它,基本能認990多個漢字.而四字一詞的《千字文》每一句都是有具體意境可幫助記憶的,背熟了終生難忘。
如此可見,舊時私塾那種做法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體現為“積累”:在童蒙時期輸入大量的經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為言辭行文確立了可效仿的典範,以期達到將來的厚積薄發之功。這是遵循了語文的習得之道。
另一方面,漢語那些“能把種子種在讀者身上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被人們稱為“古文”的典籍里。那是人們民族的精神大廈的基礎。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就靠著那些典籍為載體一路舒展到人們眼前,人們怎能捨棄呢?
可見,無論從漢語的習得之道還是從呵護、培養民族精神而言,都決定了人們不可忽視對本民族的經典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