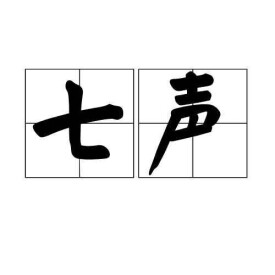七聲
中國古代七聲音階中的七個級
〖thesevennotesofChina'sancientscale〗中國古代七聲音階中的七個級,即宮、商、角、清角(比角高半音)、徵、羽和變宮(比宮音低半個音),相當於現行簡譜中的1、2、3、4、5、6、7。
詞語:七聲
拼音:qī shēng
戲曲中常用到的音#4(變徵,意為由徵音變化而來,比徵音低半個音)和b7(閏)。
中國古代音樂節奏採用三分損益法分為五音,即宮、商、角、徵、羽(也就是現在的1`2`3`5`6`),後來發展到七聲(也就是現在的1`2`3`4`5`6`7`)
清樂:
宮,商,角,清角,徵,羽,變宮,分別對應1,2,3,4,5,6, 7。
這與西方的自然大小調相似,清角是角音上方的小二度。變宮是宮音下方的小二度。
雅樂:
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分別對應1,2,3,升4,5,6,7,
變徵是徵音下方的小二度。
燕樂:
宮,商,角,清角,徵,羽,閏,分別對應1,2,3,4,5,6,降7,
閏是宮音下方的大二度。

七聲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4-7
I S B N:9787506358019
南京、香港、藏地、北美,一時一地,足跡即為心跡。
目光所及,那些久違的人與事。
“一均之中,間有七聲。”正是這些零落的聲響,凝聚為大的和音。
城市裡萬聲迭轉,《七聲》穿析群囂,放聲因慣習而為人所忽略的音響。
主人公毛果的成長,貫穿世間故事。祖父母相互照扶的和鳴弦曲、童年玩伴“洪才”的家庭舊事、民間藝人“泥人尹”的跌宕絕唱、木工師傅“於叔叔”的悲喜人生、餐館弱智女侍“阿霞”身置社會底層的哀涼、女性友人“安”?過度自我所產生的悲劇,偷渡工人“阿德”身不由己的命運,極盡大半生為自己洗刷文革時期罪名、卻因好賭而終招凄涼晚景的“老陶”……
他們都是你我身邊的凡常人物,其聲雖細隱,卻與大時代的跫音同奏,一則則人生故事交迭出流動於坊市的主旋律,造就環境的調式。
葛亮 原籍南京,現居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文字發表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集《七聲》、《謎鴉》、《相忘江湖的魚》,文化隨筆《繪色》等。曾獲2008年香港藝術發展獎、首屆香港書獎、台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台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家書系”、“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8-2009中國小說排行榜”及台灣“2006年度誠品選書”。長篇小說《朱雀》獲“亞洲周刊2009年全球華人十大小說”獎。作者也是這一獎項迄今最年輕的獲獎人。
推薦序:葛亮的感覺 /韓少功
自序:他們的聲音/葛亮
琴瑟
洪才
泥人尹
於叔叔傳
阿霞
安的故事
阿德與史蒂夫
老陶
英珠
威廉
拾歲紀(代跋)
附錄:命若琴弦——葛亮《七聲》/張瑞芬
獨家收錄《七聲》番外篇
這個作品對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場的超越性在於﹐它昭示了一個人對藝術的忠誠﹐對任何生命律動的尊崇和敬畏﹐對觀察﹑描寫以及小說美學的忘我投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這個時代感覺僵死症的療治者之一。諸多“人已經退場” ﹑“個性已經消亡” ﹑“創作就是複製”一類的後現代大話﹐都在這一位年輕小說家面前出現了動搖。在這一點上﹐〈阿霞〉堪稱不可多得的範例之一﹐作者的少年成熟令人驚嘆。 ——韓少功(作家)
《七聲》以白描手法寫出七則南京和香港的人物故事,包括了外祖父母畢生不渝的深情(〈琴瑟〉),一個木工師傅的悲歡人生(〈於叔叔傳〉),一個叛逆的女大學生素描(〈安的故事〉),一個弱智餐館女工的卑微遭遇(〈阿霞〉)等。葛亮不再訴諸《謎鴉》的神秘奇情,轉而規規矩矩的勾勒人生即景;故鄉南京的人事尤其讓他寫來得心應手。他的敍事溫潤清澈,對生命的種種不堪充滿包容同情,但也同時維持了一種作為旁觀者的矜持距離。
〈於叔叔傳〉﹑〈阿霞〉兩篇特別動人,尤其是前者幾乎可以當作是新時期以後市場經濟崛起的寓言來讀,頗有討論空間,後者則是延續正宗歐西現實主義風格,以底層社會、心地簡單人物的遭遇反映人生百態。正如張瑞芬教授所言,文字清新明凈,配合敘事者毛果有情而又不失矜持的角度,顯得溫柔敦厚。的確在大陸出身的年輕作家中獨樹一格。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表現在葛亮身上的,是早熟、機警。看葛亮,不單看見他,也看著他豐厚的閱歷跟站在他後頭、漠漠但廣袤的群眾。這使小說跳脫一人、一物,而拔升到凝視一個群體跟其共同命運的悲天憫人,感染力十足。讀葛亮,老是想起兩岸新一代作家,大陸敦厚,烘托以大土地、大文化,常見驚艷之作,但也常受資源捆綁;台灣熟技巧、聰明惜閱歷薄。兩邊各有限制了。《七聲》除了寫出「一抹時代的輪廓」外,倒相當生動地雕鑿了葛亮的聰慧跟慈悲,讓說故事的葛亮,成為非常迷人的主角了 ——吳鈞堯(作家、台灣《幼獅文藝》主編)
葛亮的故事裡沒有歷史的笨重感,也沒有走火入魔的實驗手法,他以一條清亮嗓音,三十歲不到的年齡,別闢蹊徑,重新回歸說故事的趣味。他的語言,乾淨洗鍊,節奏迅疾,有三月陽春的颯爽與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鮮明的印子,帶領著讀者步步尋向不可知的徑外人世。早在寫性愛人生的《謎鴉》里,他就展露了這樣的絕佳天分,到了這本類自傳的短篇小說集《七聲》,葛亮鼓點頻催,流暢依然。故事環繞著成分良好,背景優越的男主角毛果,總共七則小人物記事,像穿珠一般的串起邊緣人、世間事,可分立也可合觀的七段卑微人生。以孩童至少年毛果為視角,回憶往事故人,少了《謎鴉》的酷樣與老成,《七聲》寓熱情於冷筆,各篇緊湊相接,比起《謎鴉》來,無疑進境顯明,技巧愈隱,餘味更厚。 ——張瑞芬(評論家﹐台灣逢甲大學教授)
整體而言,慈悲的質量以及節制的書寫,構成葛亮作品里最動人的質素。他的文字極有敘事魅力,每每能逗引讀者的閱讀興味;而作為一名聰慧的創作者,葛亮亦擅於在故事的結尾力求平淡收斂,是高潮以後刻意的低調。而從《謎鴉》到《七聲》,葛亮不斷展現其深具懸疑感與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這一點亦是大陸中生代作家莫言、蘇童、余華等所擅場,然而故事的講述之外呢?蘇童輩的故事敘述既多,困境亦隨之而顯;這一點,亦是我對青年作家葛亮未來創作之路的擔慮,或是多慮。也許在故事之外,仍有些什麼是值得創作者去追尋的。 ——石曉楓(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教授 )
葛亮作品的重要價值,在於把文字轉化成一種衡器,用以衡量時空變遷中人的心靈變化,並將此作為一種指標體系,互為因果地評價時空緯度對人的影響。這彷彿科學研究一樣的方法,令他的寫作充滿了歷史感。歷史感通常是一種使命感,但這種使命不是“受命於天”,而是來自於作者本人對時空變遷充滿的失力感和焦慮感。從總體上來講,每個人類個體的生命都是悲劇,因為從時間上來看,人無一倖免地走向以死亡為結局的終點。但宿命的悲劇並不應該成為人類悲傷的理由,它的意義更在於將警示人們珍惜短暫的生命,即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拓展空間範圍,實現密度的增加。人是時空中的一芥微粒,但它又可以無限大,因為它是時空這一超越現實場景的組成。歷史感是人對自身這種客觀身份所體現出的使命感。因而小說對於人生的意義,就將是對人生密度的稱量與解構。 ——馬季(批評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