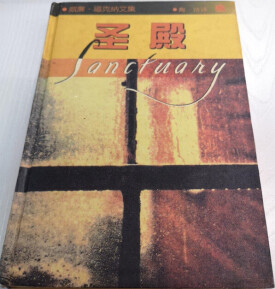共找到14條詞條名為聖殿的結果 展開
聖殿
美國作家福克納的作品
《聖殿》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於1931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是福克納第一部獲得大量讀者的小說。描繪了一幅被敗壞了的南方社會的場景,堪稱福克納揭露和抨擊美國南方醜惡現實的最有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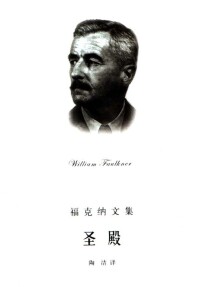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聖殿》
在這部小說中,女性的身體如同自然一樣被男性佔有和主宰,並且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還不僅於此。這部作品的主要內涵在於,作者要將譚波爾比作一隻學舌的鸚鵡,她就像自然一樣沒有話語權,它們同樣具有被動性。在作品中譚波爾多次化身為鸚鵡,變成一隻沒有思想、沒有自由的動物,一切都掌握在別人的手中,包括生命。當危險來臨的時候,她只能用“我爸爸是法官”來保護自己。她父親命令她做偽證,只能在法庭上像鸚鵡學舌一樣去回答問題。在作品中,這位可憐的女孩就像自然一樣沒有主動權,沒有話語權。在閱讀時我們可以發現,福克納一直沒有寫出譚波爾說的什麼,只是簡單地說譚波爾一直在喃喃自語。讀者只能聽到譚波爾在說話,但是始終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其實,她很清楚地預見了她會被強暴,於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對著一個老人大喊大叫,但是恰巧這個老人又聾又啞,她的話語很自然地又被忽略了,“就像炙熱的水泡掉進了寂靜的海中”。作者在這裡故意安排了一個聾啞老人就是為了表達譚波爾的失語性和無助,這個巧妙的設計極具諷刺意味,她的呼喊不會有任何的作用,只能被外界所主宰,她的人生與生命沒有任何的自由度可言,只能屈服於男權主義的思想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動的,她不可以反抗與呼籲。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可憐的女性與自然有著驚人的相似,她們在受到傷害的時候,都不能抗爭,都沒有話語權,只能默默承受。
關於“金魚眼”,福克納曾有過兩次不盡相同的評論。1947年他在密西西比大學否認“金魚眼”在生活中有“原型”,說“他只是罪惡的象徵”。10年後,在弗吉尼亞大學他則說“金魚眼”是“一個淪落了的人。他只是湊巧成了現代社會中的罪惡的象徵”。儘管兩次都提到“金魚眼”是罪惡的象徵,但後面一次主要是在強調他是一個“淪落了的人”。仔細分析起來,這兩種說法都有其正確性。不過應該說他第二次講得更為全面。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金魚眼”在小說中的作用的確是作為罪惡的象徵。他是黑社會的頭目,他從事各種不法活動,用令人髮指的方式強暴譚波爾並在小說所包括的一個多月中槍殺了兩個人。但他不僅僅是一個象徵,而且是一個小說人物,一個有多面性、有生活經歷的人。
當金魚眼剛一出生時,每個人都認為他是瞎子,而且直到五歲時才長出頭髮。醫生說它可能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如果悉心照顧,他或許會長大一點。他的爸爸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拋棄了他和他媽媽。他母親只好和他的瘋子奶奶生活在一起。金魚眼在他出生后的幾周里明顯是個身體上不健康的孩子,而且這期間他的父親又拋棄了他們母子,而母親由於工作不能悉心照顧他,使他不但沒有康復的機會,反而病情越發嚴重。在這個即不完整又不健康的家裡,天生多病的金魚眼只會變得更加病態。
早在他上小學時,他變態的行為和性格就出現了。學校的集體生活使得金魚眼感覺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之間的不同。由於沒有健康的身體,家的溫暖,缺少關心和愛護,金魚眼不平衡的心理狀態變得更加極端。當別人健康的身體和幸福的家庭與自己既不健康的身體和家庭形成強烈的對比時,自卑感便油然而生。如果自卑的心理不能得到恰當的處理,這個人就會轉而憎恨他人和周圍的社會。金魚眼就是這樣一個有著強烈反社會心理和行為的人。為了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強壯和有力,在他很小時他殘忍地用剪子殺掉了兩隻小鳥和一隻貓。通過虐殺小動物,他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一種優越感,得到了一種滿足。長大之後,金魚眼的自戀型人格障礙也隨之放大。他想通過自己幻想的世界努力去補償心理上的自卑,繼而滿足對完美身體的需求。因此,當他在,老法國人院里見到譚波爾時,他變態的心理完全暴露出來。為了強姦譚波爾可是又是性無能,他以奇怪的方式殺死了唐米。他把譚波爾劫持到妓院五周后,在他回到母親身邊前,殺死了他雇來與譚波爾發生性關係的那個男人。金魚眼在綁架譚波爾之後,他想通過武力完全控制她,以期滿足心理的控制他人的慾望。實際上,強姦譚波爾是他補償自己變態的自卑心理的一種方式。
金魚眼的變態甚至是犯罪的行為,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的道德敗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所處的家庭,社會的殘缺敗壞的一面。事實上,在現代社會裡有同樣一些人有著這種病態的心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對於物質和利益的追求往往置個人的健康、心理和生活於次要地位,使這些人產生反社會,自暴自棄甚至是自我毀滅的心理。
1932年,福克納為小說的現代文庫版寫了篇序言,強調他寫書出自“庸俗的想法”,創作動機純粹是為了賺錢,手法是用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來製造轟動效應。他說:“我拿出一點點時問,設想一個密西西比州的人會相信是當前潮流的東西,選擇我認為是正確的答案,構建了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為恐怖的故事,花了大約三星期的時間把它寫了出來,寄給了史密斯……他立即回信說,‘老天爺啊,我可不能出這本書。我們倆都會進監獄的。’……我把《聖殿》的稿子整個兒忘掉了,一直到史密斯把清樣寄給我。我發現稿子寫得實在太糟糕了,只有兩個辦法:撕掉它或者重寫一遍。我又想,‘它也許會賣錢的;也許有一萬個人會買的。’於是我撕掉清樣,重新寫了這本書。小說已經排過版,所以我還得付錢,為了那重新寫一遍的特權,努力使它不至於太丟《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的丑。我改得還是不錯的。我希望你們會買這本書並且告訴你們的朋友。我希望他們也會買這本書。”他在1947年跟密西西比大學英語系學生座談、1955年訪問日本、甚至在1957年任弗吉尼亞大學住校作家時仍然重複這個觀點,儘管日本學者和弗吉尼亞大學的學生都不相信這是本粗製濫造以贏利為目的的壞書。雖然福克納在藍登書屋出版《聖殿》時不讓收進這個序言,但由於福克納的自我貶抑,評論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對《聖殿》評價不高。
1956年有位學者發現了福克納說已經撕掉或扔掉的原稿清樣和打字稿並且跟公開發表的《聖殿》作了些比較,“證實”了福克納的一貫說法。他認為原來的稿子確實寫得不夠精心,因為其中包含了兩個故事:霍拉斯·班鮑的故事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研究及譚波爾·德雷克的故事和對邪惡的探討。福克納似乎拿不定主意以哪一個為主,內容顯得很凌亂。然而,這位學者也注意到福克納在修改過程中“改變了小說的整個核心和含義;簡化了過於複雜的結構;刪除了無關緊要的東西;澄清了沒有必要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晦澀段落;充實了需要擴展的部分;給了小說一個高潮;並且使它擺脫了對在此以前福克納所寫小說的從屬關係。”1963年,福學專家邁克爾·米爾蓋特引了福克納在日本的講話——“請記住,你們讀的是第二個版本……你們沒看到的是那個卑劣的粗製濫造的東西……你們看到的是我極盡全力使之儘可能地忠實、動人、富有深意的那本書”——來證明福克納批評的是未經修改的那個版本。他還提請人們注意,福克納在修改過程中所做的大量刪節,完全不包括任何可以說明福克納所謂“庸俗想法”的特別暴力或“最為恐怖”的東西。不過,他的結論還是,“《聖殿》並不屬於福克納的偉大小說之列。……福克納不可能把《聖殿》寫成一部可以跟《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的成就相媲美的書,但他確實把它改寫成一部能證明他自己所說的‘改得還是不錯’的看法……的作品。”
這種情況到了1972年開始有所改變,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把《聖殿》原稿清樣和修改本按左右對照的排版形式彙編出版。編者傑拉德·朗福德在前言中詳細描述他對兩個文本所作的比較,指出福克納並不是如人們所想象的把一個恐怖的色情故事改寫成一部更有意義的作品。他也不同意第一稿因目的不明確而混亂不清的說法。相反,他用大量事實論證初稿是以霍拉斯為主人公,描繪這個跟《喧嘩與騷動》里的昆丁一樣敏感多思的長不大的中年人在面對邪惡和理想幻滅時發現自己也充滿邪惡。在朗福德看來,《聖殿》的初稿極其有意思,並不比修改稿更加“恐怖”,只是在敘述方式上採用更多的試驗手法,可以說是後來《押沙龍,押沙龍!》敘述手法的萌芽。福克納在修改稿里把故事更多地集中到譚波爾和金魚眼身上,似乎是想“把一個進展很慢的心理研究精簡提煉成一個可以馬上由好萊塢拍成電影的故事”。
《聖殿》是福克納所有長篇中唯一開始就獲得商業成功的作品,但也是一部廣受批評的作品。福克納認為寫該書是為了“庸俗的想法”,製造的是一個“最為恐怖的故事”。小說本來包括關於霍拉斯·班鮑、譚波爾·屈萊克的兩個故事,後來刪除了次要的枝節,加入了高潮,因而到讀者手裡的版本已大為不同。福克納在這部小說中使用的語言比較簡練,文句也不複雜,跟《喧嘩與騷動》大不一樣。福克納用快節奏的手法把大量經過高度提煉的細節直接推到讀者的跟前,而且故意有所省略,留出一些空白來迫使讀者進入故事情節,參與創作和想象,從而在令人窒息的事實面前痛苦地作出他含而不露但迫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社會腐敗了,人性泯滅了,世界快要完蛋”的結論。
《聖殿》的故事就是開始在這麼一個地方,而且開始的場面極富象徵意義,充分表現了哥特小說最根本的特徵:善與惡的對立。在林中一條溪流的兩邊蹲著兩個人,隔溪而望,僵持著。看起來他們在幾乎所有方面都相反。一個高,另一矮;一個著裝考究,另一個衣不合體,而且褲褪上、鞋上都沾滿了泥;一個光著頭另一個戴著一頂似乎從未取下過的草帽;一個舉止文雅,另一個則口裡總是斜叼著一支煙;一個衣兜里裝著一本書,另一個衣兜里裝的則是一把手槍。後來我們得知,他們中一個是律師,另一個卻是黑社會頭目,殺人兇手。這些對立的因素幾乎都具有象徵意義。他們的個子象徵著高尚和卑劣;光著的頭和壓得很低的草帽象徵著光明與黑暗,誠實與欺詐;而他們的著裝、舉止以及所攜帶的書和手槍則分別象徵文明與野蠻。很明顯,他們是善與惡、正義與罪孽的代表。小說中還有許多這樣的兩極對立:偵探與兇手,法律與罪行、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與本質上的腐敗墮落,世俗觀念與道德意識,同情與冷酷,無私與貪婪等等。正是在這些對立與衝突中,小說的情節得以展開,主題得以深化。
那兩人就這樣蹲著,隔溪而對,幾乎沒說話,相持了兩個小時。這種似乎沒有盡頭的相持象徵著善與惡之間永恆的對立和衝突。只不過,這部小說並非像一般哥特式小說和偵探小說那樣以正義戰勝邪惡來結束,而是邪惡最終戰勝了正義。這樣的結局,或者說這一主題思想也在卷首這貌似平靜卻暗藏殺機的對立中暗示出來,因為他們之間表面上相持不下,實際上是揣著槍的人把揣著書的人控制在那裡,並最後將他押送去了法國人莊園的廢墟。這預示著在一個法律被潮弄、道德被踐踏、個人利益重於良心的社會裡,正義是多麼軟弱無力而罪惡則是怎樣肆意橫行。這正是《聖殿》要展示的南方社會的狀況和作者要表達的思想。
《聖殿》的故事情節主要是以兩個人物為中心展開的。一個是賀拉斯,另一個是譚波爾·屈萊克。前者主要是作為一件兇殺案的辯護律師而像偵探一樣偵察案情搜尋證據;而後者則是這一案件的受害人之一和主要見證人,並且同時也是引發此案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這個案件把這兩個毫無關係的人的故事聯結在一起。譚波爾是一個18歲的女學生。同賀拉斯一樣她也來自一個法官家庭。但她的性格和思想同賀拉斯幾乎完全不同。德萊克法官和他的四個兒子是南方清教文化的代表,把婦女的貞節和家庭聲譽看得重於一切。為了家庭聲譽,他們可以置法律和道德良心於不顧。他們完全按南方清教婦道觀來要求和束縛譚波爾,把她看作是(正如她的名字Temple所暗示的)“神聖的殿堂”,禁止她同男孩子交往。但是“爵士樂時代”的譚波爾已不再是舊南方的淑女。那種壓抑婦女人性的桎梏,不但沒有使她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相反卻使她產生了逆反心理。由於具有這種心理又缺乏正確的道德信念,所以她專門想做他們不准她做的事。特別是她上大學住到校園后,她更是毫無顧忌地同男同學交往,甚至在晚上溜出去同鎮上的男孩子鬼混。她在同男孩子的交往中極不嚴肅,更不用說有什麼愛情。她純粹是為了好玩和追求刺激。她甚至不在乎約會的對象是誰,她需要的只是約會;“她把約會的時間記在她那供抄襲用的拉丁‘直譯本’里,這樣她就用不著管是同誰約會。她只需要打扮,過一會兒就會有人來叫她。”
她牽扯進這個兇殺案就是因為跑出去和一個同她一樣毫無道德觀念、毫無責任心的男人戈德溫約會造成的。戈德溫是弗吉尼亞大學的畢業生,然而他在大學里所學到的只是怎樣以“紳士派頭”大碗喝酒和說大話吹牛皮。他在同譚波爾約會期間多次酗酒,最後導致在法國人莊園附近翻車,使自己和譚波爾落入“金魚眼”等黑社會分子手中。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繼續酗酒,而不設法使譚波爾和自己脫身。第二天清晨,他竟扔下譚波爾不管一個人溜了。他是一個毫無責任心的膽小鬼,對譚波爾的遭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他也是那個以傳統價值觀念的淪喪為特徵、以追求享樂為目的的時代的典型人物。
儘管戈德溫負有重要責任,但譚波爾的遭遇以及她隨後的墮落的主要根源還在於她自身,在於她沒有一套立身處世的正確原則或價值觀念,而是以遊戲人生的態度來對待生活和與人交往。她挑逗男孩子,只是為了玩玩。她在還有法律和世俗觀念管束著的學校或城裡,這樣“玩玩”還算幸運沒有遇到危險。可是在法國人莊園這麼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她那一套遊戲規則就不靈了,只會給她帶來危險。當她落入那些不法分子手中后,她既害怕又感到刺激。一方面理智告訴她面臨的危險,因此她要求戈德溫帶她離開,並一再懇求盧比(私酒製造者戈德溫的妻子)幫她逃走。然而另一方面,她又感到興奮和刺激,下意識地不想離開。盧比一再勸她走掉,她借口說沒有車。盧比說:“你知道我怎麼取水嗎?我走路。一英里,一天六趟”。後來在小說《修女安魂曲》(這部小說被看作是《聖殿》的續集)里,她也承認她“有兩條腿”,完全可以離開。所以盧比說:“我知道你這種人。我見過。總是在逃跑,但並不太快”,“你是在玩”,“當你回去后,你就有向別人吹噓的東西了”。盧比的這些話可謂一針見血,揭示了譚波爾這類人的本質,同時也指明了譚波爾處在那種情形中的矛盾心情。
不幸的是,人們身上的那種非理性的東西往往比理性更能支配一個人的行為從而更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正是譚波爾的情況。她不斷懇求人幫助並告訴自己應該離開,但她沒有離開。非但如此,她還把對鎮上男孩子的那一套也有意無意地搬了出來。她在那些不法分子喝酒時不斷進進出出,在他們面前展示自己。盧比曾告誡她呆在一個地方不要動,但她就是不聽。不但如此,就寢時,她甚至當著一個男人的面脫掉外衣並拿出化妝盒來塗脂抹粉。不管她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挑逗性的行為對那些不法分子們起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就連曾在盧比的要求下出面保護過她的戈德溫·李也受到刺激。所以盧比對她說:“我怕的不是李……而是你。”部分由於她的挑逗,唐米和戈德溫,甚至連那個陽萎的“金魚眼”也一個接一個在黑暗中摸到她床前。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她的心情仍然是又驚又怕又渴望。當“金魚眼”來到她床前時,她競在心裡說:“來吧,撫摸我。撫摸我!如果你不,你就是一個膽小鬼。膽小鬼!”當“金魚眼”撫摸她時,她為“保護”自己所作的只是先把自己想象成一個“頭髮花白戴著眼鏡”的“45歲的老師”,接著又把自己想象成一個“長著長長的白鬍子的老頭”。幸好一方面由於盧比的保護,另一方面由於這些不法分子要外出活動,那天晚上總算沒出事。可是第二天早上,當戈德溫也攔車溜走後,她仍然留在那裡。這時盧比連自己的丈夫也控制不住了,只好帶著孩子到外面去,以示抗議。不過在戈德溫“動手”之前,“金魚眼”槍殺了唐米,用玉米芯強暴了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令人髮指的獸行與兇殺發生在星期日上午10點。這是基督復活之日,也是人們上教堂之時,但那卻是譚波爾在精神和道德上死亡的時刻。在這之前她還有一絲天真和單純,對罪惡還有一點恐懼。在這之後,她落入“金魚眼”的掌握之中,在道德上、精神上完全墮落了。她變得是非不分、毫無正義感,對戈德溫的冤案和曾經幫助過她的盧比的遭遇無動於衷。至於在性方面,她的慾望和行為更是同野獸一樣令人作嘔。當賀拉斯最後在妓院找到她時,要她講述她在法國人莊園的遭遇和案情發生經過。在講述中,她對罪犯的暴行和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悲慘遭遇不僅不感到憤怒和羞愧,相反,“她實際上是帶著驕傲在講述這一經歷”。正是由於她道德上的墮落和是非不分,當她最後出庭作證時竟作偽證,把強暴過自己的“金魚眼”所犯的罪行都推到戈德溫身上,致使戈德溫被暴徒們活活燒死。譚波爾的例子可以表明,一個人如果從小沒有得到正確的精神指導,沒有樹立起正確的道德意識,當他同罪惡相交時會墮落到什麼地步。
由此可見,賀拉斯在“偵破”過程中得到的不僅僅是案件的真象,而且是一些關於生活、社會和人性的真理。《聖殿》這部小說使用偵探手法的真正意義就是要用這種手法來有助於對社會、對人的探索。其實,與通常的偵探小說不同《聖殿》並沒有製造迷霧來掩蓋案情。儘管有些細節到後來才逐漸揭示出來,讀者一直都知道案情的大致真相和誰是真兇。所以這部小說的重點不像一般小說那樣放在“誰幹的”上面,而是放在“業餘偵探”賀拉斯律師在“偵破”過程中究竟“發現了什麼”上。他所發現的遠非案件的真相,他發現了存在於南方社會、政治、法律、文化傳統和人身上的普遍的罪惡。
然而,福克納不是絕對不進行心理分析的。譚波爾對霍拉斯說的那番話就是她在遭到強暴前一天晚上所思所想的心理活動的十分真切的描繪。對於那個敏感多思、好幻想的知識分子霍拉斯,福克納並不吝惜任何心理描寫。第二十九章關於霍拉斯衝進人們殘害戈德溫的場地,第十九章表現他潛意識裡亂倫慾念的有關他凝視小蓓兒照片的那一節。尤其是第二十三章他終於認識到自己意識深處不可告人的罪惡思想的那一段,都是用意識流手法表現的既生動又深刻的心理分析。福克納也不是不採用其它現代派手法的。譚波爾被強暴的故事就運用了多視角多層次的敘述方法。第五到十四章用的是全能視角,由作者進行描述。第十九章里,魯碧從她的角度把這事件又介紹了一遍。到了第二十三章,譚波爾親自出面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霍拉斯。同一個故事反覆講述了三次,卻都沒有交代那關鍵部分。其目的很明顯,就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使他們不僅重視事件在小說里的作用,而且去挖掘文本以外的寓意。
福克納在談到文體時曾反覆強調“主題,故事,創造自己的文體”,作家企圖寫的作品控制它的文體,強迫(作家使用某種)文體”。他還明確地表示過,“看比聽強,無聲勝於有聲,用文字創造的形象就是無聲的。文中驚雷、文中仙樂,都只能在無聲中領會”。可以說《聖殿》的手法充分表現了他的觀點。福克納在1928和1929兩年裡寫了三本風格迥異的小說:用典型的意識流、多視角等現代派手法表現的《喧嘩與騷動》、也用意識流和內心獨自等手法但不是用多視角來把同一個故事重複講述多遍而是各自介紹故事一個部分或方面的《我彌留之際》以及基本上不用這些手法而是以情節取勝的《聖殿》。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福克納具有何等高超的手法技巧。何況,三種不同的手法講述了三個不同的故事,表現了社會的不同側面。《喧嘩與騷動》展現了上流社會貴族階層的沒落,《我彌留之際》刻畫鄉野村民的自私與自尊、頑強拼搏與苟且偷生兼而有之的兩面性,而《聖殿》所揭示的畫面既包括上流社會及其習俗和保護它們的法律體系又涵蓋了下層社會乃至底層犯罪分子的種種心態。應該說,雖然《聖殿》跟《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在風格上大相徑庭,但它同樣展示了“人的內心衝突”,也同樣能證明福克納無論在思想深度還是藝術造詣方面都無愧於大師的稱號。
哥特式
《聖殿》里充滿了暴力、兇殺、強姦和瀰漫著令人恐怖的氣氛,其中特別突出的是暴力引起的死亡。小說中共有七人死亡:兩人被燒死,兩人被槍殺,兩人被絞死,還有一個人帶著冒血泡的喉管和吊在背後“越吊越下去的頭”跑了一段路才倒下。哥特小說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一個“哥特式地點”,比如陰森的城堡、荒廢的莊園、鬧鬼的房屋或者充滿危險的荒野等等。《聖殿》中的哥特式地點是被當地人稱之為老法國人莊園的地方。那是一個充滿傳說和早已被廢棄了的莊園,現在是一個製造和販賣私酒的窩點,是犯罪分子的場所。它不受法律的管轄和社會道德的約束。任何不慎闖入此地的外人都會遭受難以預測的危險。正是在這裡,誤入其中的譚波爾·德萊克度過了一個惡夢般的夜晚,並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僅目睹了一個人被槍殺,而且自己也被強暴。
命名
其實諷刺在《聖殿》里隨處可見,成了這部小說的思想和藝術的核心。比如斯諾普斯是一個堂堂的州議員,卻是一個滑稽可笑的卑鄙小人。戈拉哈姆是地區檢察官,卻為了當國會議員肆意踐踏法律。譚波爾的名字有“神聖殿堂”之意,卻墮落成一個道德上和性生活上的無恥之人。娜西莎等人名為基督徒,卻毫無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對苦難中的母親和孩子毫無同情之心。相反盧比這樣一個被人鄙視的人卻具有許多美德。賀拉斯性格軟弱,卻不得不肩負起伸張正義的沉重使命。“金魚眼”是罪惡的化身,卻出生在聖誕節。就連小說的名字“聖殿”(Sanctuary)也不無諷刺之意。關於“聖殿”的意義,福克納曾說,那是一個人們“躲避麻煩”的“安全地方”。他是指在以前如果一個人逃到教堂的聖壇上,他就能躲債或逃避追捕這一古老傳統。然而在小說中,不論是法庭,還是法國人莊園或者孟菲斯妓院都只是藏污納垢之處,既不神聖也不安全。
蒙太奇
福克納在《聖殿》這部作品中通過精心的蒙太奇剪輯效果,對比了城市與鄉村,人與窮人、道德與罪行、正派與情慾,溶所有這一切於全無憐憫與尊嚴的情感結構之中,反映了人類社會生活的陰暗面。
《聖殿》的故事情節的展開主要集中在老法國人駐地、孟菲斯及傑弗生鎮三地,這三處的社會背景並非彼此孤立,綜合併里分析不難發現作者是頗具匠心的。福克納精心安排了這三個地方,蒙太奇手法突出了它們的共性,以罪惡之本可以從這三幅圖畫的深層結構得到揭示。老法國人駐地是三個地域中最自然、最樸實的地方,到處都是被廢棄的痕迹,住在這兒的是兩種靠天吃飯的人:一個又聾又瞎的老人與一白痴,一對經法律程序結合的夫婦及他們的孩子。這五口人依賴地里自然生長的一點農作物過活。儘管讀者初涉此地時聽到的是鳥聲,看到是夭然池塘,而那聲卻“規律得令人感到不自然,尤如鍾控制一般”,那池卻又是“被“金魚眼”吐過唾液”的池塘。
《聖殿》的開頭部分就描寫了律師本博與惡棍“金魚眼”池塘旁僅有的一次會面,並就其表情、衣著、外貌、動作等予以濃墨描寫,甚至強調本博隨身攜帶著一本書,而“金魚眼”攜帶的則是一把槍,他們彼此雖無共同語言,卻又隔著閃爍的塘水相互凝視達兩小時之久。作者的安排無疑是令人費解的,但肯定具有某種深刻意義。顯然,福克納並非想強調本博與“金魚眼”的差異性,而是企圖誘導讀者去探索他們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之間的共性。
另外,譚波爾是《聖殿》中的核心人物,她的被奸是小說的主要情節,但關於她的被奸過程,福克納並未平鋪直敘,而是採取多種敘述法,引導讀者去綜合分析,從中自作結論。
在福克納的作品里,《聖殿》是唯一一部剛一面世就暢銷的小說。它在1931年由凱普與史密斯出版社出版后,三周之內的發行量就相當於1929年出版的《喧嘩與騷動》和1930年的《我彌留之際》銷售額的總和。不僅如此,好萊塢馬上買下該小說的電影攝製權,很快就拍成了電影。
1933年,《聖殿》被譯成法文,著名作家馬爾羅在前言里給予高度評價,說它是一部沒有偵探但充滿偵探故事氣氛的小說,福克納把希臘悲劇引進了偵探故事。奇怪的是《聖殿》也是福克納本人批評最多的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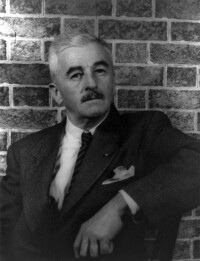
威廉·福克納
福克納194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