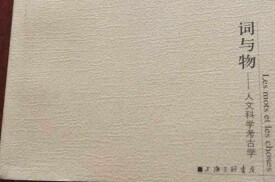詞與物
詞與物
《詞與物》一書最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 DE MICHEL FOUCAULT)1966年出版的著作,全名為《 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出版時,福柯傾向於將該書命名為「事物的秩序」,但編輯希望改名為「詞與物」,最後福柯讓步了。而該書的英文版標題則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 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 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語詞與事物》的副標題是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種人文科學的考古學。福柯強調他在這本書里作的是一種考古學研究,但這絕不是通常意義上作為研究古代文物的考古學,而是指的“知識考古學”(une archéologie du savoir)。
什麼是福柯意義上的知識考古學?
福柯認為,在不同時代的知識論述中,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秩序既是作為物的內在規律和確定了物相互間遭遇的方式的隱蔽網路而大的中被給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於由注視、檢驗和語言所創造的網路中。”正是以一定的秩序為基礎,語言、知覺和實踐才是有效的,並且三者或多或少地表達了秩序。“這樣,在人們也許稱之為對有序代碼的使用與對秩序本身進行反省之間的所有文化中,就存在著純粹的秩序經驗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經驗。”而這本書研究的就是這種秩序經驗,要研究的是在何種基礎上知識和理論才是可能的,知識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秩序空間中被構建起來的。所以,福柯關心的並不是具體科學知識的進展情況,也不是科學的分類問題,也不是知識是否為真以及如何為真的問題,他研究和關心的是整個知識領域、整個認識論領域,知識是通過何種秩序經驗而成為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認識型(épistémè)的概念。Epistémè本是古希臘語,就是“真理”、“知識”的意思,其反義詞是doxa,意思是“意見”。在巴門尼德那裡,區分了兩種道理,即真理(épistémè)之路和意見(doxa)之路。不過,福柯借用這個古希臘詞,用來指某一個時代人們共有的經驗秩序的結構,是一種先天的認識構型(confirguration)。
在這本書中,福柯通過考古學研究,考察了16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中的兩次認識型的中斷(rupture)。
第一個中斷,由文藝復興時代(la Renaissance)過渡到古典時代(l’âge classique),發生的時間大約是17世紀中葉;
第二個中斷,發生在19世紀初,由古典時代過渡到現代性(la modernité),這個現代性一直延續到福柯自己所處的時代。
在西方文化中,有時將文藝復興之後,就開始稱作現代,因此,由培根、笛卡爾之後的西方哲學稱為現代哲學(la philosophie moderne),而笛卡爾被稱作第一位現代哲學家。而福柯則的研究則表明,即使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文化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在19世紀初有過一次突然性的認識型的轉換,從而產生了一種與古典時代有極大差異的現代認識型。所以,現代性認識型中的理性,已經不同於古典時代的理性,但這其實並非理性本身的進展,而是“物的存在方式,以及那個在對物作分類時把物交付出知識的秩序的存在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福柯的考古學研究還研究了現代的人文科學,他認為在古典時代“人”並不存在,只是隨著19世紀初現代認識型的出現,才出現了“人”,關於人的所謂人文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文學與神話研究。但是人文科學不是科學,而是處在與生物學、經濟學、語言學相臨近的位置而取得了貌似科學的假象。既然“人”只是近期的一個構思,那麼這個構思也可能消失。“人”,應該成為知識(le savoir)的實證領域,而並非科學(la science)的對象。隨後,福柯的研究還表明,隨著精神分析學、人種學的發展,以及同樣不談及人本身的語言學的發展,“人”將終結了,“人”將消失。
《語詞與事物》分有前言,第一編,第二編三部分。第一編考察了第一個認識型的中斷,第二編則考察了第二次認識型的中斷,以及“人”和人文科學的誕生和消失。接下來我將嘗試跟隨著福柯的思路,踏上知識的考古之旅。
《語詞與事物》一書的第一編考察了第一個認識型的中斷,即從文藝復興時代的認識型到古典時代認識型的轉變。那麼,先要考察被古典時代認識型所取代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認識型是怎樣的。
書中寫道:“直到16世紀末,相似性(la ressemblance)在西方文化知識中一直起著創建者的作用。”存在著四種相似性的主要形式:
① 適合(convenientia):事物在空間上彼此接近,其邊界相接或邊緣互相混合。相似性就出現在兩物之間的這一結合處。例如,植物長在雄鹿的角上。
② 仿效(aemulatio):不受位置律束縛,能靜止地在遠處起作用。
③ 類推(l’analogie):類似仿效,不受位置律束縛;也類似於適合,談及配合、聯繫和接合。例如:植物是站著的動物。
④ 交感(les sympathies)。交感沒有確定的法則,自由自在地在宇宙間發揮作用。例如,在葬禮上使用的紀念死者的月季花,這些花就和死亡聯繫在一起了。
那麼,憑什麼標記,相似性被認出來呢?因為,世界就是充滿相似性的神秘空間,是一本用相似性的記號書寫的大書,而人所要做的就是發現、辨認、譯讀這些記號。這些記號來自何處,當然是上帝,“上帝為了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只是在大自然上播下了種種供我們辨認的形式”。相似性既是認識的形式,也是認識所產生的知識的形式,在16世紀知識型中相似性成為最普遍的東西。
那麼在這一知識型中語言與事物是什麼關係?表現為兩種形式:
第一,在其初始形式中,“語言是物的完全確實和透明的符號,因為語言與物相似” 。
第二,語言不再直接與所命名的物相似,但“仍以另一種形式成為啟示的場所並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表達的空間中” 。語言與世界形成為一種類推關係,而不是指稱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內,語言與事物相互交織的空間中是以書寫的絕對優先權為先決條件的,書寫物優於言說物。基於書寫的角度,存在三種語言層次:
①書寫形式,語言是事物的一個印痕,是事物的標記;
②書寫形式之上,存在著評論,評論重述了在新的話語中被給定的符號;
③書寫形式之下,存在著文本。
三個層次通過相似性的原則統一在一起。但是,從文藝復興時期末期開始,這種基於書寫的三元結構慢慢消失了:
一是因為三元結構被“能指/所指”的二元結構所取代,
二是因為語言本身不再表現為相似性而是表現為表象。
從古典時代開始,書寫的至上性被懸置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重組。
古典時代認識型是表象(réprésentation)。塞萬提斯小說中的英雄堂?吉訶德的冒險,意味著依賴“相似性”認識型進行思考在現實世界中只會處處碰壁,而代之而興的則是表象的認識型,所以福柯評價《堂?吉訶德》為第一部現代文學作品。
在17世紀初,相似性不再是知識的形式,而成為謬誤的原因,並相繼遭到培根、笛卡爾等人的批判。於是,西方文化的認識型的基本排列發生了變化,形成了新的構型:“理性主義”。
福柯提醒我們要注意區分三件事:機械論、數學化、 Mathesis 。
對於古典認識型,其關鍵在於它與Mathesis的一種關係。Mathesis被理解為一門關於秩序與尺度(l’ordre et la mesure)的普遍科學。它與古典認識型的關係表現為:
一,存在物之間的關係通過秩序和尺度為形式得到思考,並且尺度問題可歸於秩序問題;
二,在探尋Mathesis的相互關係中,一些新的經驗領域形成了,這些領域將其基礎建立在一門可能的秩序科學之上。
於是,關於詞語、存在物和需求領域,出現了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
文藝復興時代符號的三元結構,現在被一種二元結構所取代。“符號包含兩個觀念:一個是進行表象的物的觀念,另一個是被表象物的觀念;符號的本性在於用第二個觀念來刺激第一個觀念。”而要成為純粹的二元結構,符號必須滿足下列條件:它必須進行表象,即表明它與它所指稱的事物的關係,這才能成為一個符號;同時這個表象又反過來能表象自身,因為符號中除了它所指稱的東西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這樣,這種二元制結構的符號成為古典時代思想的工具。
接下來,福柯用三章,分別論述了古典時代的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
福柯寫道:“語言在古典時代的存在,既是最高的,又並不引人注目”。說它是最高的,因為語詞已經接受表象思想的任務,語言表象思想,如同思想表象自身一般。也正因此,語言使自身成為看不見的,或者幾乎看不見的,因為語詞對於表象來說是透明的,以致於它只是被看作表象。普通語法,則“是對與同時性相關的詞語秩序的研究,表象這一同時性,正是普通語法的任務。因此,普通語法的適合對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任何個體語言,而是被理解為一系列詞語符號的話語。這一序列通過與表象的同時性聯繫起來。”普通語法所做的工作就是使語法規則之下但又與語法規則同構的表象功能呈現出來。福柯還提出了一個語言四邊形的說法:即命題、表達、指明、衍生四種理論構成了一個語言四邊形的四條線段,這個四邊形的中央存在著名詞,語言的一切功能在此交叉。這就是整個古典語言經驗。古典論述(discours)的基本任務把名詞賦予給物,並在這個名詞中去命名物的存在。
在古典時代,關於生物這一領域,是通過自然史來認識的,自然史的興起與笛卡爾主義大致同時,都因同一個認識型才得以可能。自然史將語言與事物間的表象關係當作自己的可能性條件,通過觀察構建了一個新的經驗領域。觀察就是系統地看,並從中找出結構。接下來,通過特性、連續性等,一個新的經驗性領域通過自然史的話語被建構起來了,這個經驗領域被構成為可描述(descriptible)的和可整理的(ordonnable)。不過,古典時代生物學並不存在,因為生命(la vie)並不存在,生命沒有進入經驗領域;存在的是生物。自然史的研究者關注的是將各種生物在一個有秩序的網路中加以描述並命名。
在古典時代,政治經濟學還不存在,因為生產並沒有進入知識序列,知識序列中存在著的是一個一般領域:財富。在16世紀,相似性的認識型,同樣支配著財富交換領域。在17世紀,隨著“重商主義”在財富、貨幣間確立的是一種反思的連接,使貨幣成為表象和分析財富的工具,並反過來使財富成為由貨幣表象的內涵。那重商主義的財富指什麼?就是所有那些因可被表象而能成為慾望對象的東西。一個新的經驗領域“財富”出現了。
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都服從於同一個構型(la meme configuration),即表象的認識型。雖然在這三個經驗領域,各有其不同的具體形式,但畢竟都服從於表象的認識型,而且也都可以在語言四邊形的框架內加以解釋。所以,“17、18世紀的人們並不憑藉先前世代獲得的一切,也不依照不久將被發現的一切,來思考財富、自然或語言;他們是從一個一般排列出發來思考它們的:這個排列不僅規定了它們的概念和方法,而且更為基本的是為語言、自然個體和需要及慾望的對象確定了某種存在方式;這個存在方式就是表象的存在方式。”
在《語詞與事物》一書的第二編,福柯首先考察了現代認識型的誕生。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分別被語言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取代了,但這種取代並非佔據了普通語法、自然史和財富分析原來佔據的地方,而是在這些知識並不存在的地方。“19世紀的知識對象形成於古典的全部存在都陷入沉默的地方。”事物不再以原有的方式被描述,呈現給知識的不再是財富、生物、話語,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古典時代把事物在一個空間中展開為秩序,而19世紀開始,大寫的歷史(Histoire)將在一個時間系列中展開,並將其法則相繼強加在生物結構、生產分析、語言群分析之上。這裡,歷史不能被簡單地被理解為前後的相繼;“歷史是經驗性之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在這個存在方式的基礎上,經驗性才得以在可能的認識和可能的科學的知識空間中被確認、設定、排列和散布。”
現代認識型的確立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確實性之基本的存在方式並沒有變化;人的財富、自然的種、充斥在語言中的詞仍然保留在古典時代;雙重表象──其作用是指示表象、分析表象、組合和分解表象,以便使一般的秩序原則,與表象之同一和差異的體系一起,在諸表象中湧現。只是在第二階段,詞、綱和財富才會獲得一種不再與表象的存在方式相共存的存在方式。”
第七章研究的正是第一階段。在經濟學領域,亞當?斯密引入了勞動概念,但是他並非發明作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勞動,不過他卻轉移了勞動。財富將根據勞動的單元被分解,勞動單元真正產生了財富。於是,“由財富最終表象的,不再是慾望的對象,而是勞動。”在語言領域,則出現了比較語法,從而闡明了詞形變化體系,這已經出純粹語言學的維度。“從現在起,存在著語言的一個內在“機制”,它不僅決定了每一個語言的個體性,而且還決定了每一個語言同其他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正是這個機制,作為同一與差異的持有者,作為鄰近性的符號,作為相似關係的標記,才將成為歷史的支撐。對這個機制而言,歷史性將能夠進入言語本身的深處。”類似地,在自然領域,通過“組織結構”這個概念,揭示了有機無機的區分,從而也將歷史性引入了。這些變化,導致了勞動、生命和語言在經驗領域中出現了,而這也意味著人將作為勞動著的人、生活著的人和說話的人(l’homme qui travaille, qui vit et qui parle)而出現。
接下來的第八章研究了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知識的實證性(la positivité)改變了其性質和形式。在經濟學領域,“生產作為知識空間中的基本形式,已經取代了交換,生產一方面使得新的可認識對象(如資本)呈現出來,另一方面規定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如生產形式的分析)”;在生物領域,開始使用比較解剖學方法並研究生物的內在組織結構,“那是因為大寫的生命(la Vie),作為知識的基本形式,使得新的對象(如特性和功能的關係)和新的關係(如對類似的尋求)呈現出來;在語言領域,“作為知識方式的大寫話語(le Discours)已被大寫的語言(le Langage)所取代,大寫的語言定義了直至那時沿未明顯的對象(語法體系在其中彼此類似的語言的家族)並規定了尚有未被使用的的方法(對輔音和母音的轉換規則作分析)”。這樣,新的現代性的認識型被建構起來了。
在福柯看來,在18世紀末以前,人(l’homme)並不存在。生命、勞動、語言的歷史深度也不存在。“人”是新近的產物,是現代認識型的產物。當然,此前也有關於人的討論,但並不存在關於人本身的認識論意識。只是在現代認識型中,才出現了“根據經濟學、語文學和生物學的規律而生活、講話和勞動的個人,並且還憑著一種內在的扭曲和重疊並藉助於那些規律的作用而獲得權利去認識並完全整理它們的個人,有關這個個體的現代論題,所有這些我們熟悉的並相關於“人文科學”的論題” 。
為什麼會這樣呢?在古典時代,人的本性,是可以無限地表象外在世界和表象自身的主體。但是,現代認識型使人們認識到人的有限性(la finitude),即人受制於勞動、生命和語言。人首先已經是一個生命,有一個身體,才能生活;首先有語詞,人才能說話;首先有生產工具,才能勞動。因此,生命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軀體給予我的;生產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慾望賦予我的;語言的存在方式,只是沿著我的會說話的思想的細長線索而賦予我的。
在這種有限性之中,人是一個奇怪的經驗—先驗對子(un doublet empirico-transcendantal) ,而現代性的門檻就在於人作為經驗—先驗對子被構建之日。古典時代,對人的研究其實不過是對錶象的研究。但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既然分析的不再是表象,而是有限的人,那麼重要的就是要在認識中在被給出的經驗內容的基礎上,闡明認識的條件。因此,“存在一種人類認識的歷史,既能賦予經驗知識,又決定經驗知識的形式。”康德的批判哲學區分了經驗、先驗等等,並通過時空、範疇等,闡明了先天綜合知識之所以可能的先驗形式,正是這種“人類認識的歷史”的反映。
現代思想將人看作一個的經驗—先驗對子,所以人也是不解(la méconnaissance)的場所,人是我思與非思的混合場所。在現代經驗中,在知識中創立了人這個可能性,包含著思想的一個命令:思想既是自己所知的一切的知識,又是其改正,既是它的反思對象的存在方式之反思,又是其轉化。思想必須使自身的存在發生改變,或者在非思的方向上行進,否則無法發現非思。所以,“現代思想,一開始並且就其深度而言,就是某種行動方式”。現代思想是在這樣一個方向上前過,即在這個方向上,人的他者(l’autre)應該成為與人相同者(le même)。於是福柯發現,人處於一種權力內部,這個權力使人散開,使人遠離他自己的起源;但這個權力不是別的,就是人自己的存在的權力。現代性用源於人自身的權力來反對人自身。
現代認識型產生了人,也產生了關於人的新的經驗領域,這就是人文科學。現代認識型在三個方向上敞開,這三個方向即:數理科學、經驗科學、哲學反思。人文科學並不在三者之中,而是在三者限定的區域內。就在這三個維度之中,為人文科學提供了空間,那麼如何定義本質意義上的人文科學?根據兩方面:“一是限定性分析在其中得以展開的維度;二是那些把語言、生命和勞動當作對象的經驗科學據以能分佈的維度。”實際上,人文科學只是就人是活著、勞動著、說話著的人,才關注於人。於是,在生物學、經濟學、語文學相鄰近的領域,誕生了心理學、社會學、文學和神話研究,構成了人文科學的三個領域。這三個領域也代表著不同的構成模式(見下表):
Fonction功能 Normes規範 生物學、心理學
Conflit衝突 Règles規則 經濟學、社會學
Sens意義 Systhèmes體系 語文學、文學與神話分析
從這三個模式出發,可以描述自19世紀以來的所有人文科學。功能和規範,衝突和規則、意義和體系,這三組對子完整地覆蓋了有關人的認識的整個領域。心理學基本上是依據功能和規範對人進行的研究,但也可以從另二個模式進行研究;社會學基本上是一種依據規則和衝突而對人進行的研究;文學和神話的分析根本上發球一種有關意義和指稱系的分析。每個領域都可以用另兩個模式作為次要模式進行研究。但是,這種種“人”的科學,是現代認識型的組成部分,但並不是科學。因為使人文科學成為可能的,就是某種與生物學、經濟學和語文學相臨近的位置;“只就人文科學處於生物學、經濟學和語文學的旁邊,或確切地說,處於其下面,處在其投影空間中而言,人文科學才存在著” 。
20世紀,精神分析學與人種學相繼興起,這兩門學科在現代知識中佔據著一個特權地位。所有的人文科學只是通過不理睬無意識,期望著無意識隨著意識的分析而倒退著被揭開面紗,人文科學才能向無意識行進,而精神分析則是直接和有意地指向無意識的。精神分析位於無意識的維度內,而人種學則位於歷史性的維度內。人種學在文化中研究的,是結構的不變式。人種學能與三個實證性(生命、需求和勞動、語言)中的每一個都結成關係,探索三者是如何被規範化的。因此人種學的一般問題是自然與文化的關係問題,詢問人的知識成為可能的區域。人種學與精神分析並不是人文科學的組成部分,而是貫穿了人文科學。二者是“反科學”,不停地拆解那在人文科學中創造和重新創造自己的實證性的人,即它們消解了人。而第三門“反科學”,則能覆蓋精神分析和人種學的維度,這就是語言學。因為從語言內部,從趨向於極點的各種語言遊戲中,顯現出來的正是“人的終結”。
人的終結,人的消失,這說明了什麼?要注意福柯並沒有說人已經消失,而是說“人正在消失”。事實上,人一方面不斷被種種人文科學及其他現代科學所構建、所強化,一方面又不斷地受到精神分析學、人種學、語言遊戲的消解、解構。但是,正是這個正在不斷消解的過程,顯示出一種新哲學的希望,使人有可能從“人類學沉睡”中醒來。福柯指出,“人類學作為人之分析確實在現代思想中起著一種構建作用”。從19世紀早期開始,“人是什麼?”這個問題貫穿著現代思想。反思是現代哲學的特徵,反思用來設法把人限定為生活、勞動、說話的主體。於是,“我們發現哲學再次沉睡於這一褶層中;這不是獨斷論的沉睡,而是人類學的沉睡。”而哲學就是要讓人們從這種沉睡中醒來。
在《語詞與事物》一書的最後一頁,福柯寫道:“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