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余純順的結果 展開
- 中國探險家、藝術家
- 小行星
余純順
中國探險家、藝術家
余純順(1951.12-1996.6.13),上海人,大學本科。
1988年7月1日開始孤身徒步全中國的旅行、探險之舉。行程達4萬多公里。發表遊記40餘萬字,沿途拍攝照片8千餘張,為沿途人們作了150餘場題為“壯心獻給父母之邦”的演講。尤其是完成了人類首次孤身徒步穿過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征服“世界第三極”的壯舉,1996年6月13日在即將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羅布泊全境的壯舉時,不幸在羅布泊西遇難。
概述
余純順在羅布泊莊嚴地走完了他不平坦的人生之路。身後也不平靜,先有墓被盜,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寫了一本書,說他是一個為名聲所累、不夠清醒的英雄。
目的
余純順這次來新疆,主要目的是實施他孤身徒步走訪全中國探險計劃中,徒步穿越羅布泊的項目。庫爾勒人以慣有的熱情,迎接他的到來,樓蘭賓館對他的食宿予以全免。
余純順穿越羅布泊探險活動的前期準備工作,在我們的配合下,緊張而有序地進行著。我們協助他制定了穿越羅布泊以及米蘭至敦煌兩個方案,確定了行進線路。
同時,根據羅布泊的氣候特點,極力勸阻他改換季節,以使穿越活動更具成功把握。我們提出:穿越羅布泊,應在九、十月,那時恰好可以避開高溫和大風天氣。
“另外,這次穿越羅布泊活動,將有上海市電視台攝製組隨同作追蹤拍攝。他們一行稍後即到庫爾勒市。日程安排已經不可更改。"余純順接著說。
信心
1996年5月31日一早,上海電視台紀錄片室主任編導宋繼昌等4人組成的攝製組抵達庫爾勒市。這時,1996年5月27日余純順制定的“孤身徒步縱穿羅布泊日程及上海電視台追蹤拍攝日程表“,已經正式列印成稿。攝製組還在烏魯木齊時,余純順便於1996年5月28日下午由庫爾勒出發,徒步前往172公裡外的兵團農二師32團場了。在談到此行的目的時,余純順說:“前幾個月一直忙於整理日記和寫稿,很少活動,更談不上走路了。走這百多公里路,一來可以做穿越羅布泊前的“熱身”,二也使我適應一下塔里木周邊地區的氣候、環境,為十月份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準備”。
他最後充滿自信地說:“我這可以說是“小試牛刀“,勝率在百分之百!”
1996年5月29日下午17時左右,一場突如其來的沙塵暴襲擊了庫爾勒市以南地區,我們很為余純順擔心,因為沙塵暴掠過的地方,正是32團及其鄰近的另外幾個團場和尉犁縣。
1996年6月2日上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黨委宣傳部,在樓蘭賓館五樓會議室召開新聞發布會。余純順在會上慷慨陳詞,表示了穿越羅布泊的決心。自治州人壽保險公司為余純順、上海市電視台攝製組、陪同以及兩位司機共10人,免費提供了價值100萬元人民幣的人身保險。
準備事物
1996年6月4日,余純順穿越羅布泊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石油物探局地調三處提供“賓士”沙漠車二台,車上配有電台;購買了夏季常用藥品;號稱“沙漠王”的退休地質工程師、年過花甲的趙子允,被請來擔任前進橋至土垠段的嚮導。我的任務是陪同餘純順一行,由庫爾勒經營盤到前進橋,並全程服務。
有關單位為這次活動,免費提供了發電機一部,攝製組自備衛星導航儀GPS三台。
湖心地帶
1996年6月6日,是余純順及攝製組進軍羅布泊的日子。路線為自西向東南。即由庫爾勒出發,經胡楊溝、營盤、老開屏、前進橋、龍城雅丹群、土垠后,進入羅布泊湖心。
上午,為積極配合上海電視台對穿越羅布泊行動的連續報道,余純順把一份新聞稿和線路草圖稿,以傳真發往上海,並同遠在北京的朋友通了電話。隨後,他把不便攜帶的一些書籍、資料捆紮好,連同部分攝影器材一起,委託友人保管。
下午13時30分,余純順縱穿羅布泊壯行儀式在樓蘭賓館新樓前舉行。當地旅遊局、人保公司和賓館的領導,為余純順等人胸前佩上了大紅花。幾名蒙古族的姑娘,依次為我們敬獻了“上馬酒”。各界代表人士先後講話,預祝余純順孤身穿越羅布泊成功。熱烈日下的余純順,自稱除飲少量啤酒,從不沾白酒的他毫不推讓,幾碗酒喝下,已是滿臉通紅,激動的心情,流於言表。他站在話筒前,汗水夾著淚水不住的從臉上滴下。面對著百餘名與會人士,他再次表示:一定能順利實現穿越,打破6月份不能進入和穿越羅布泊的神話。大家對此抱以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下午15時30分,余純順一行9人,分乘兩台沙漠車,駛離樓蘭賓館。余純順意欲征服羅布泊未料卻魂歸羅布泊悲壯的一幕,正式啟開。
汽車的轟鳴聲打破了庫魯克塔格山的沉靜。車身捲起的衝天塵土如同濃霧,烈日象一團火球高懸在我們的頭頂,汽車駕駛室里悶熱難當,坐在前排司機老張師傅一側的余純順,不住用毛巾拭去頭上和脖脛上的汗水。當天晚上9點多,喘息未定的汽車停在了庫魯克塔格山南坡沖積帶上,一處比較平坦的地方,決定在這裡扎建營地。經過6小時近200公里的顛簸,大家實在不願多走哪怕半公里了。這裡遍布一叢叢、一簇簇的麻黃草和梭梭柴成了蚊子、飛蜢棲身的好去處。夜幕降臨時,它們成群結隊向我們襲來,胳膊上、腿上很快被叮起了包,大家只好躲進悶熱的帳篷里。
6月7日一早,每人吃了一包速食麵,我們又迎著初升的太陽上路了。在車上,余純順得意得地說:“我有一位朋友,是位報社女記者,她寫了篇關於我歷時八載走中國的文章,據她自己講已經替她掙了三千多塊錢稿費!”有人調侃說:“余老師你已經成一棵搖錢樹了!“話音未落,就覺車身往右後方猛地斜了下去,停車后,才知道右後車胎扎入了一塊長形的利石。乘著換輪胎的功夫,攝製組抓拍了一些余純順在沙丘間孤身徒步的鏡頭。重新上路走出96公里后,一行人到了孔雀河岸邊的老開屏。這裡有成百上千間廢棄了的部隊營房,從丟棄的廢品看,這裡曾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醫院,另外也駐紮過汽車分隊。有人說,老開屏是取孔雀開屏之意,其實這個地名同元寶莊(原爆庄)等地名一樣,是老一代軍人創建中國原子彈試驗場后,為紀念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所起的地名。
在一處空地上,停有西北石油地質局一部宿營車,一位只穿一條褲衩,渾身被晒成紫銅色的小夥子是這裡唯一的老住戶。他告訴我們:馬上要進行原子彈試驗,東邊正在清場,勸我們不要進去,以免白費周折。每逢試驗,必是清場,這一貫例我們都很清楚。後退的確於心不忍,大家商量后,一致同意按原定計劃行動。在這裡吃過午餐,我們繼續往前進橋方向進發。在這后一百多公里沿途中,遍布部隊遺棄的營房、若干簡易機場、巨大的工事,從這些斷壁殘垣上,我們只能遙想當年這裡升騰過的數十次耀眼的輝煌!
疾駛13個小時,里程錶顯示出我們只走了250公里。在快要到達二號營地時,不料裝載食品物資的一台車,不留意一下陷入了爛泥中,卸下車上的全部物資,幾經掙扎后,總算開了出來。這個營地距著名的龍城雅丹群僅僅5公里,但是夜幕降臨,加上方向極難辨認,我們只好很不情願地在這裡紮下了二號營地(E:90°02`,N:40°49`)。

余純順
1996年6月8日早晨,余純順一行來到了龍城。龍城位於孔雀河下游,屬孔雀河下游雅丹分佈區。連同樓蘭古城一帶的雅丹在內,其長度東西為40公里,南北寬約160公里,面積約1800平方公里。往南望去,只見密集分佈的雅丹群正反射著朝陽的金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雕萬琢,使得這些毫無生命千年不語的風蝕土堆群,呈現出萬千儀態。其氣勢之恢宏、神廳與壯麗,令人驚嘆不已。在這裡,余純順精神異常亢奮。面對攝像機,他激動的說:“我到過新疆許多地方,只有龍城充滿了輝煌的詩意。”“迄今為止,到過和將要到羅布泊的上海人,一個是彭加木,一個就是我(註:彭加木曾在上海工作過)。如今,彭加木已經魂歸大漠了,而我,只有我余純順,一定能征服羅布泊!”
在龍城的拍攝進行了4個小時。余純順意猶未盡,利用拍攝間隙,自己也拍了不少照片。
1996年6月8日是下午,余順純一行經過土垠,踏上了羅布泊乾涸不毛的湖盆。在E90°18`44"、N40°34`34"處向西抵達羅布泊西岸,紮下了第三號營地,往西偏北數百米,便是積滿黃沙的孔雀河河道,明天一早我們要小心翼翼跨越河道,沿河去樓蘭。
準備吃飯時,上海電視台的宋繼昌編導告訴我:“老余要準備徒走了。一條線路是由前進橋至庫爾勒,一條線路是從土垠起用3天時間穿越羅布泊,最後到前進橋。”剛吃過晚飯,余純順叫住了我,讓我給他提供庫爾勒前進橋間的公里數。查對了我過去每日行程記錄后,我把幾組數字抄在一份報紙上寫好交給了他。余純順邊看邊說:“老彭,從庫爾勒到前進橋這段路,我記的很亂。再說,個別路段時不時有車輛、人員活動。如果徒步,需要預埋飲用水,但又考慮這樣怕不安全。”我回答:“明天我要去樓蘭,細節問題回來后再說吧。”
我提醒他:“前進橋到庫爾勒大部分都無路可走,但只要你順著庫魯克塔格山往西走,就可以到甘羊廠,那裡有人又有水,應該沒有問題。”
等吃完飯,除余純順外,大家都匆匆鑽進帳篷休息了,因為我們在羅布泊湖盆中的行進異常艱苦。大家早已疲憊不堪。由庫爾勒出發時前兩台車的空調就全都壞了,進入湖盆,車外陣陣熱風不斷刮進車裡,加上汽車自身的熱度更使每個人都象在被蒸烤,在湖盆中,我們停車,便於攝製組拍攝,頭頂烈日,讓人頓生毛髮欲焦之感。目極所在,一望無際翻翹著的鹽殼,呈現出令人心悸的灰褐色。鹽殼下邊是厚可盈尺的青灰色土層,土層下則是潔白的鹽塊。天不見飛鳥,地不長寸草,時時處處暗藏著危機,這就是羅布泊。難怪余純順說:“這樣的地方,只能用來放原子彈。”其實,羅布泊曾是一個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的泱泱大湖。只是滄海桑田,山河巨變,加上近世紀人類活動的干擾,才使它變為眼前這乾旱不毛的死亡地域。
據新疆若縣誌記載:“一九六四年十月上旬,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幾天,在羅布泊地區荒原上,我空軍巡場飛機意外發現了一群約一、二百人的國民黨馬步芳、馬鴻奎余部殘匪。三天後,這群游弋了十數年的匪徒被接出荒漠。”試想,如果羅布泊及其周邊地帶,沒有水草,沒有野生動物,這幫殘匪何以能在這裡生存十多年呢?在去羅布泊的途中,我們多次看到受驚嚇后狂奔的野羊,多則數十隻,少則三、五隻。這說明,至少羅布泊附近還是有生命的。
1996年6月9日8時,我們離開三號營地,由東向西進發,去探訪神秘消失近兩千年的樓蘭。道路十分難走,5個小時汽車僅僅走了14公里,平均時速僅2.8公里。這時,我們用GPS測量,還有近7公里路程。站在孔雀河干河床南岸,雖能看見樓蘭城中的佛塔高聳,但雅丹密布,汽車無法再前行一步。我提出棄車徒步的建議,大家把出發時間定在了下午17時。離出發時間還有4個小時,我們赤裸著身子坐在汽車下,苦苦等待著出發的那一刻。在44度的高溫下,大家被熱的幾乎喘不上氣來,只好隨著汽車的陰影東躲西藏。殊不知這時的汽車在灼熱的陽光強烈照射下,車身也成了強熱源,幫不了我們多少忙。
好不容易熬到了17時,我們決定除留下老張、大張兩位司機原地留守外,其餘8人各背12瓶礦泉水、4聽八寶粥以及睡袋、相機等,徒步去樓蘭。樓蘭被雅丹緊緊包圍著,四周遍布黃沙斷磧。常年盛行的東北風,使我們腳下的雅丹溝壑走向同主風方向一致,走起來比我們以前由北向南穿越雅丹去樓蘭要省力。大約兩個小時后,樓蘭古城被我們踏在了腳下。
來不及休息,攝製組就架好機器準備拍片了。不料忙中出錯,所帶電池竟未充電。宋導提出讓我返回司機留守處另取幾隻。我說:這裡地形複雜,大家都知道,天一黑路上容易走偏方向。並提出,明天一大早去取,也絕對在光線最好時趕到,不影響拍片。在一旁的余純順聽了這話有些激動,大聲道:“這次拍片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明天絕對來不及!要說天晚,我不怕,我去取。兩個小時我完全可以打個來回!”最後,趙工提出他去,這才打破了僵局。事後趙工告訴我們,他們返回的路線偏東北了,怎麼也找不著汽車,著急中,我們目送趙工向東奔去,
直到夜裡十一點多,看到了兩位司機的火堆后,才回到汽車邊。晚上,我在樓蘭城西北歪脖子胡楊樹下,挖出了1995年11月帶考察隊來這裡時,埋下的三頂帳篷,一些午餐肉罐頭。臨睡前在樓蘭佛塔南側平台上,余純順興緻勃勃,大談樓蘭的興衰,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成因。他說:“塔里木盆地遠古時代曾經是汪洋大海,海水甚至淹沒過阿爾金山和昆崙山東部。由大海變為沙漠,大概經歷了十幾億年。”他認為,羅布泊一帶的雅丹為烈風剝蝕后,成為塔克拉瑪乾的主要沙漠。我告訴他,1994年塔克拉瑪干沙漠國際大會有結論說:那裡的沙子起源於盆地自身。余純順聽了以不屑的口氣說:“那不過是一家之言!”
早飯後,我收拾好行裝,獨自坐在背囊上抽著煙,這時,余純順走來了。應余純順的要求,我給他畫了由樓蘭至前進橋的線路草圖。此刻以肉眼能清晰看到的樓蘭城北烽火台,烽火台西北14公里處的鐵塔覘標,一一指點給他。據他講,由前進橋徒步至庫爾勒的計劃被攝製組否定了,因此他決定:由樓蘭返回土垠徒步穿過羅布泊,經過樓蘭到前進橋。其餘人員乘車按原路由土垠折返前進橋接應。
我畫給他的這張線路草圖,由樓蘭城北5公里處的烽火台(19號覘標)、該點西北大沙包上的15號覘標、15號標西北的烽火台、11號覘標連成一條線,全程約18公里。
畫好后,又給他做了詳細的解釋。樓蘭東南及其以北的雅丹分佈區,其雅丹同龍城高度20—25米的雅丹相比,相對高差較小,一般不超過41米。因此,地質專家們標為“皺形雅丹”。正是這些不算高大的雅丹,這條線路上的幾個覘標、幾個烽火台遠看十分醒目。它們相距4—5公里,一般天氣情況下,這幾個突兀而立的目標都很容易辯認,最後我告訴余純順,“萬一找不準要找的點,一定要記住往北走,也就是朝庫魯克塔格山的方向走。這樣,最北部那條幹涸的孔雀河,是你必經的,這樣再找前進橋就不難了。”
老彭,我走了八年了。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經驗和實力,從土垠過來到前進橋這段路,我兩天半就可以幹掉!”余純順胸有成竹的說。
上午9時45分,結束了在樓蘭的活動,我們就要返回土垠了。臨走前,我們8人把沒有喝完的20多瓶礦泉水集中在一起埋在佛塔南側的土坎中。時隔近一年以後,我們再次來到這裡,挖出了這些水,可惜水已變質不能飲用,只好帶走。後來全加進了汽車的水箱里。當時考慮如果余純順徒步走到這裡后,或許可以用它救急。
其它的生活垃圾收拾裝袋后,深埋在城東一公裡外的雅丹下。中午12點30分,大家先後安全抵達司機留守處(E89度58分12.9秒,N42度33分07秒),兩位師傅早已燒好了幾大盆肉粥,匆匆吃罷我們便開始撤離。今天的營地是土垠,明天余純順將從那裡出發,開始他孤身徒步穿越羅布泊的壯舉。
出發前,余純順在停車處不遠的河岸上,放置了礦泉水一箱,食品一箱,這些水和食物,足夠他去前進橋一天路程所需。隨後,在返回土垠的路上,我們每7公里埋6瓶礦泉水,隔35公里埋全天乾糧及飲用水。在湖盆丁字路口,我們停下車來,
攝製組再次拍攝了海市蜃樓景觀和地貌,並為余純順拍了一些行進中的鏡頭。余純順在路口以西2 3公里處,放置了一箱礦泉水和一箱食品。去土垠28公里路段,又設了3個埋水點,沿途的水和乾糧均由余純順自己用我每次外出帶著的那把工兵鍬挖坑埋入土中,再以白色塑料袋裝以沙土,放在上邊作為標識。為此,余純順常說:“老彭,你的小鐵鍬可幫了我們大忙了。”
下午18時20分,我們返回了土垠。因為天氣太熱,無法搭帳篷,只好躲在高台下背陰處等待太陽落下。幾天的熬煎使我們幾乎盡疲力竭,每個人的臉龐都被曬的黑里透紅。身上的襯衣被汗浸透了不知道多少次。
晚上,攝製組在為余純順、趙子充兩人拍攝了談話情節后,我們為余純順開了個壯行會,來時我們帶了一箱(12瓶)“樓蘭干白葡萄酒”,這回正好派上用場。菜很簡單,只有幾聽罐頭。我們幾個人圍坐一圈,每人依次給余純順敬酒,祝願他穿越成功。
余純順似乎有重重心事,以往談鋒很鍵的他,此時卻變得寡言少語。交杯換盞間,有人勸他放棄徒步穿越計劃,也有人提議他擇季進行穿越行動。還有人說彭加木失蹤也在6月份,不為別的只是為了找水,擔心餘純順耐不住高溫,產生斷水的嚴重後果。這時早有人按捺不住厲聲道:“彭加木又怎麼樣?我們老余走了8年了!”
聽了這話,余純順未動色,端起酒杯,一仰脖喝下,然後說:“如果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余純順的穿越線路,全長約107公里,根據他的行走速度和路況,用3天時間和我們在前進橋會合是很有把握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完全沒有問題。”
1996年6月11日9時,拒絕車輛、人員隨行的余純順大步流星離開土垠向南邊羅布泊走去。身上背著的背包里裝著他的帳篷、防潮墊、筆記本、睡袋以及西洋參(切片)一盒。我們目送他,直到他的身影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中,隱沒在零星分佈的雅丹里。
按原定計劃,送走了余純順,我們應按原路返回前進橋大本營接應點。由土垠到前進橋以南大本營全程139公里,全是鹽殼下覆蓋著虛土、細沙的地貌,而且根本沒有路。汽車要馬不停蹄地跑一整天,太陽升起,陽光無遮無攔地直射下來,讓人覺得暈暈乎乎,眼前不時出現重影。在汽車上,宋導對我說:“去前進橋時間推后,下午三點以後追余純順,只要他感到身體不適,就把他拽上車,拖回來!”
中午過後,氣溫直線上升,至少在45—50左右。著名考古家,新疆考古所名譽所長穆舜英教授,1979年4月曾進入羅布泊北岸一帶,尋找進入樓蘭的道路。她在《神秘的古城樓蘭》一書中,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這裡的氣候異常乾燥……
雖是四月,但氣溫已達到攝氏38度至40度,熱的人揮汗如雨……
余純順在6月份,硬要隻身闖入羅布泊,他的初衷,是要以此行“打破6月中旬不能走羅布泊的說法”。他在1996年6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宋老師在拍片前曾專程到烏魯木齊去訪問了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炳華及給彭加木開車的王師傅,均說:羅布泊湖心在6月10號最高溫度達到75度,十二時到十七時,人只能躲在車底下,根本無法行動,6月份根本不能進……”。可見他對這裡惡劣的氣候是事先已有所了解。
午後3時,我們登車了。發現了余純順的埋水點,沿著昨天返回土垠的路,追趕余純順。駛出約8公里,發現他出發后的第一個埋水點停車以後,上海電視台的小孫等和我相繼下車,小土堆上裝有沙土的白色塑料袋原封未動,小孫拔開土堆向下挖時,挖出了昨天和余純順埋的6瓶礦泉水。很可能這段路他並不覺得缺水,在早上出發時,他褲子兜里一左一右各裝了一瓶水。第二個埋水點是在一叢紅柳下,這裡扔有兩隻空水瓶和幾隻煙蒂。附近有凌亂的軍用膠鞋印和一處坐痕。
下午4時25分,我們終於在湖盆中攆上了他。里長程表在離開土垠時,顯示為3305,此時正指向3338公里。余純順用8個小時,孤身徒步33公里,平均每小時4.125公里!這裡距他徒步計劃中的第一個宿營補給點還有3公里不到。我們爭先恐後跳下車,圍住他問這問那。只見他滿頭大汗,汗水浸濕了衣服和背包,黑紅的臉龐上,汗水不住的流淌。宋導關切地問他,身體能不能吃的消?他緊握雙拳上下揮動工著說:“我沒事的!身體這麼結實,絕對沒有問題。從出發后,我一次沒休息,一氣走到這裡的。”“我這不是走過來了嗎?我就要打破6月份不能進入羅布泊的神話。再走兩三公里就到第一個營地了,到了以後我就扎帳篷休息。
今天早點睡覺,明天趕早走,你們趕快回吧!”為在黃昏前趕到土垠以北的戈壁上紮營,為後天儘早趕到前進橋大本營節省時間,我們又一次同餘純順分手了。
臨上車時,他說:“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幹掉。”坐進了悶熱的駕駛室,只見余純順右手揮動著草帽,大聲喊道:“咱們前進橋見!”這是他在羅布泊湖盆中,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從此,他走向了一條不歸之路。
1996年6月12日,天才蒙蒙亮,我們就起來了。昨晚充電時,攝製組不慎燒壞了一隻進口的充電器,聽說價值在五萬元人民幣以上,大家的心情不大好,早飯也懶得做,急急忙忙就上路了。
上午11時45分,我們越過孔雀河上的前進橋,又往南行進10公里,到了11號覘標下的接應點。余純順如無意外,13日將和我們在這裡會合,然後一同返回庫爾勒。
天氣很熱,我們9個人有的坐在汽車陰影里,有的在身子下邊鋪上破紙箱只穿條短褲躺在汽車底下。每個人都不住地喊熱,不停地喝水,空水瓶扔了一地。
羅布泊是極旱地區,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而蒸發量卻高達3000毫米。在這裡水就是生命,縱有黃金萬兩,也難買清水一滴。但是光有水喝還不行,必須加入少許碘鹽以及時補充體內大量隨汗水流失的鉀鹽。否則渾身就像棉花一樣綿軟,沒有一點氣力。
日落時分,氣溫稍稍降低。我們趕緊取出一頂紅、黃、白三色尼龍布帳篷捆綁在聳立於大丘上的11號覘標上。余純順13日朝這個方向徒步走來時,一定能看到它。
天氣突變
搭好了各自的帳篷,簡單的晚飯也做好了。正準備分發飯菜時,剛剛透著光亮的天空,突然間昏暗起來。它象一口倒置的大鍋,半邊一片灰黃、半邊現出白色。
緊接著一陣掠地風襲來,捲起陣陣沙塵,漸漸形成一堵厚重的“土牆”,直向我們撲來。沙暴來了!這是一場來勢兇猛意想不到的沙塵暴。我們還沒來得及鑽進帳篷,鋪天蓋地的沙塵便隨風而至。剎那間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風聲呼嘯,飛沙走石。汽車很快被沙塵霧吞沒,沙粒打在車身上,發出噼噼叭叭的響聲。這一晚我始終在帳篷里縮守,其餘6人早已飛身鑽進了汽車,他們的帳篷全被狂風吹倒並埋入沙中,只好同兩位司機在車上過了一夜。
這場詛咒的風,從21時45分颳起,直到13日早晨,仍在肆虐。我們不由替余純順的處境擔憂起來。8時30分,我和趙子允等三人,決定去5公里以外13號覘標下,迎候余純順。
造成影響
11號覘標上捆綁的那頂為余純順指示方位的帳篷,嘩啦啦發出巨響,我真擔心大風會把它撕成碎片。好不容易來到13號覘標底下,我們三人輪流用望遠鏡向正南的樓蘭方向觀察。大風中我們把身體緊貼在覘標的木柱上,雙臂還是不停抖動,望遠鏡完全失去了功能。大風裹挾著沙塵帶著陣陣悶雷般的響聲,不時從耳畔掠過。
成千上萬噸的沙子和塵土被風拋向空中,又藉助風威,如同雨霧撲面而來,打在人臉上,胳膊上如同針扎一樣。
能見度越來越低,10米開外什麼也看不見。為了不使宋導他們著急,我們在下午7時措回了營地。捆綁在11號覘標上的帳篷已被狂風撕裂,象幾面碩大的彩旗飛舞,我感到情況不好。因為早上我們出發前,曾告訴過宋導:如果余純順從另外一個方向平安到了,就請把這項帳篷取下來。宋導大步前來迎接我們三人,從他的臉上的愁容很明白的看出:余純順沒有回來。傍晚8時左右,風終於停了。昨天我扎帳篷時,特意選了一塊有層厚沙的地方,大風過後,沙子蕩然無存,裸露出了堅硬的黃土。帳篷空懸著,宋導顯得焦促不安,雙眉擰在一起,他提出14日由我帶一人進入樓蘭,接應余純順。已到了人命關天的地步了,大家都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各自嘴上都不說罷了。
這一夜,十分寧靜。但我心緒紛亂,根本無法入睡。早上5點多鐘,就借著手電筒光亮,準備好了乾糧和礦泉水,以便天一亮就出發。這裡距離樓蘭的直線距離為13.6公里。我們必須一天跑一個往返,當天下午趕回。如果幸運,途中能夠同餘純順不期而遇,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14日,我和上海電視台孫鷺於7時準時出發了。我們各背了12瓶礦泉水、4聽八寶粥、4聽魚罐頭、4隻饢餅和兩大包餅乾,外加望遠鏡、GPS。
一路上我們依次經過了15號覘標緻19號覘標(烽火台)。12時,抵達樓蘭城東北小佛塔下。在這裡除了我倆的腳印外,有一些不知什麼人丟棄的酸黃瓜包裝袋。我小心翼翼把它裝進衣袋,打算帶回去讓大家進一步確認是誰人所留。周圍再也沒有其它有價值的痕迹,我們失望了。
下午2時我們開始返回。在15號覘標下休息時,一片烏雲遮住了頭頂的驕陽,隨即一陣稀稀落落的雨滴落下。當時我光著背,便趕忙穿上衣服,誰知另一隻袖子還沒穿好,雨競驟然停了!這微不足道的小雨,真令人難忘!
我們出發后,大本營派出趙子充等2人,去10公裡外的前進橋接應余純順未果。他們在那裡為余放置了礦泉水、罐頭和一頂太陽帽后,由北向南返回。傍晚8時,我這一路同他們幾乎同時回到大本營。
天黑前,我們決定把大本營北移至前進橋,後來考慮那裡地勢較低,不利觀察。於是選擇了前進橋以南約6公里處的9號覘標。覘標豎在高約7米的土丘上,以北14公里處,庫魯克塔格山黑色的山體清晰可見,東南為樓蘭方向。居高臨下,視野較為開闊。我們抬出了發電機,由我攀上三角架,在頂端固定了兩隻電燈泡,三角架上又裹上了一頂帳篷,大紅大綠,格外醒目。大本營不遠處的幾株枯死的胡楊也被點燃,以便為余純順指示方向。
電燈徹夜未熄,胡楊直到早晨還冒著青煙,但是仍不見余純順的蹤影。宋導頭戴草帽,雙手背後,在帳篷間踱來踱去,嘴裡不住念叨:“余純順呀、余純順,你到哪裡去了?!”
上午,我們開通了電台,向庫爾勒方面報告了同餘純順失去聯繫的情況,提出:余純順五天音信杳然、處境危急,請求派出部隊或直升飛機尋找;我們除了十箱礦泉水外,生活用水已滴水無存,急需補充。
當天下午6時和晚上10時,通過兩次電台聯繫,得知巴州黨委、政府,已向自治區人民政府緊急報告,爭取飛機出動。
這天我們派出三個搜尋小組,分別沿孔雀河東南、東北和前進橋方向,尋找了一天。下午6時,幾路人員一無所獲返回營地。
同餘純順11日分手后5天里,沙塵暴颳了兩天,其餘為高溫天氣,他的乾糧和飲用水也該消耗殆盡了,處境令人擔憂。我們幾人一方面經受著精神上的重壓,一方面要兵分幾路外出尋找,體力幾乎到了極限。滿腦子只有五個字:“找到余純順!”
15日晚上,又颳起了大風。
16日上午10時,電台開通。我們被告知:為便於救援,確保聯繫暢通,大本營的人員、車輛原地不動;已派出兩台汽車,裝載食品、飲用水、蔬菜前往參加救援,並派出後援人員7名;凌晨2時,自治區人民政府已開始協調直升飛機出動一事。晚間通話時,我詳細報告了土垠、湖心T字路口、樓蘭、大本營的經緯度。全天通話結束后,我們立即召開會議,決定:一、後援人員明早到來后,人、車均立即出動,由趙子允帶路經龍城、土垠至湖心T字路口一線尋找余純順。二、繼續派人去樓蘭城的小佛塔,1996年6月9日兩位司機留守處(余純順第二個食宿點)尋找。三、我和上海電視台的另二位留在大本營守候電台。一旦直升機到來,便參加空中搜尋。
空中搜尋
17日上午9時,昨天下午由庫爾勒出發的後援人員未能趕到。時不我待,我們當即派出4人分兩組去樓蘭方向尋找余純順。10時整,電台再次開通。庫爾勒方面通知說:新疆軍區陸航某團的一架直升飛機,已由烏魯木齊起飛抵鄯善起飛,因遇暴雨,起飛時間延至中午12時。預計下午14時到達前進橋。另外要求我們,立即在大本營附近,尋找一塊50×100米的場地供直升機機降落;停機坪四角以紅旗做標記;飛機到來后在下風處點明火,飛機降落時將火熄滅。關閉了電台,我和兩位司機等人,立即從車上取下鐵鍬,灌好柴油,朝營地以西200米處的一塊空地飛奔而去。這塊場地很平坦,鏟去幾叢羅布麻后,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停機坪。沒有紅旗,用刀子把一頂帳紅色分成4塊的,4人各執一塊,問題就解決了。
忙碌中,一陣輕微的馬達聲隱隱傳來。“來了!”“來了!”叫喊聲中,飛機已經飛到了頭頂,藍、白兩色的機身十分清楚。它盤旋兩周又在停機坪上空懸停片刻后,隨即緩緩落下。漿葉煽起漫天塵土,除了震耳欲聾的馬達轟鳴聲,此時已看不見機身。這是下午13時35分。印有“LH93793”字樣的蘇制米17穩穩地了落地。
經歷過程
艙門打開后,依次走下4位身材健碩的軍人,他們是特級飛行員陸航三團副參謀長、機長孫剛,領航股長宋國平,副駕駛員及另一位機組人員。16年前,孫副參某長曾經連同另直升機在羅布泊地區參加過尋找彭加木的行動。“飛機油料不夠,恐怕只能給30分鐘時間。”孫副參謀長快人快語。見我們幾人沒一個應聲,又接著說,“這樣吧,我給你們40分鐘時間!”10分鐘后,我們登機。飛機朝南又折向東,直飛樓蘭一帶。我們在緊靠艙門的舷窗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地面。身下是孔雀河兩岸無邊無際的雅丹地貌,幾條古河道蜿蜒曲折,河岸上的死胡楊枝都能清楚的看到。快到樓蘭時,地面上有4個人,正向飛機揮手致意。這是早晨從大本營出發去樓蘭古城尋找余純順的4人,其中的2人到樓蘭后,還要往東走近7公里,去東經89°58'12.9''、北緯40°33'07'',余純順第二個宿營補給尋找。即日,兩位司機留營處尋找。9日撤出樓蘭去土垠時,余純順曾在這裡放置了水和食品各一箱,里作為縱穿羅布泊的第二個營地。
飛過樓蘭城偏南處,飛機繼續向東飛行。只見樓蘭城中高大的佛塔此時象個小土丘,1996年6月9日我們乘車去樓蘭時,在乾涸的河道里留下了汽車的車轍印此時也都十分清晰。這裡正是9日停車留守的地方,地面的一切都靜止不動,如同月球一般死寂,又象遠古一樣荒涼。
飛機在這裡掉轉方向回返,飛臨樓蘭時,又兜了兩個大圈,仍然沒有任何結果。
下午2時45分,我們在前進橋大本營降落。飛機很快又起飛,返回庫爾勒某部機場保養加油。我們打開電台,等候通話。下午6時30分,庫爾勒通知說:明早飛機8點起飛,大約9時30分飛抵前進橋,作第二次空中搜尋。
帳篷里悶熱異常,不得已我們幾個人乾脆赤裸上身,躺在汽車蔽蔭處。朦朦朧朧有一陣汽車引擎聲由遠漸近,隱隱傳來。起身一望,競是久等不來的後援人員和,後援物資的越野車。車一路上總是拋描,天黑后,司機錯過了前進橋的路口,天亮才發現走錯了路,這才趕忙回頭。
他們帶來了足夠的食品和水,使我們這天的晚餐十分豐富。可是余純順生死未卜,使每個人的心頭都沉甸甸的,根本吃不下去。這時,早上徒步去樓蘭的4個人中的兩個人灰頭土臉的回來了。他們說,6月9日早上離開樓蘭前,我埋的20多瓶礦泉水原封不動,還在那裡,余純順沒有到樓蘭!大家在萬分焦急中渡過了又一個不眠之夜。
18日上午9時30分,孫剛機組再次飛抵前進橋。同餘純順失去聯繫已經7天了,但我們堅信,只要他不被風沙掩埋,我們就一定要找到他!
概況
18日9時45分,我們隨機組人員登機。飛機起飛后,沿著營地北側的孔雀河干河道朝東飛去。龍城雅丹群、土垠遺址依次從機身下閃過。飛過土垠,深入羅布泊湖心的大路變得清晰起來,在無邊無際的湖盆里,它象一條白色的飄帶,直向南邊伸展開去。
10時15分,機組一位同志拍了拍我的肩頭,示意我去駕駛艙門口。駕駛艙開著門,他倚著艙門向前方伸出右手,“那個藍點是什麼?”清楚地看到在褐色的湖盆里,有一個指甲差不多大小的亮點。
我順著他的手臂往前望去,“那是余純順的帳篷!”我脫口驚叫起來。飛機開始改變航向稍向西往目標處靠近,同時降低盤旋著,準備選擇地點降落。
10時20分左右,飛機已經在目標以南約20米處降落。這時,機輪還沒有接地,機身左右搖擺著,我拉開艙門跳下,直奔目標而去。一邊跑一邊喊著“余老師!余老師!”
遇難
果然是余純順那頂藍色的帳篷。但周圍不見他的身影子,帳篷里也不見有人回應。走近帳篷,只見它的一角已經塌落,隨即,一股惡臭撲鼻而來。一把脫鞘的藏刀扔在帳篷門口,刀鞘已不知去向。躬著朝帳篷里一望,我們頓時驚呆了:余純順頭東腳西仰面躺著,頭部腫脹的連五官也失去了比例。他的頭髮象洗過一樣,長而濃密的鬍鬚也濕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滿水泡,右胸部的一個大小如乒乓球,尤其醒目。他的右臂朝上略微彎曲,肘下壓著草帽,捆紮成一卷的藍色睡墊放在胯部。余純順遇難了。

余純順
他遇難的地方,距羅布泊湖心土路僅50多米。緊接著是一個平均高約1.5米,寬不到2米,長約10餘米的鹽鹼丘。表層為堅硬的鹽殼,下部為混合的沙土鹽粒。離飛機不遠處鹽鹼丘有個余純順挖的坑,約洗臉盆大小,深約50厘米。驕陽似火,腳下熱氣升騰。我們在帳篷前肅立,向長眠羅布泊的余純順致意。太殘酷了,一個鮮活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擊!
10時45分,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上了飛機,飛向前進橋。從飛機艙窗回首看去,余純順那頂藍色帳篷,真象汪洋中一隻孤立無援的小船。余純順壯志未酬不幸遇難的消息,很快傳遍前進橋大本營,大家難以抑制悲痛的心情,有人禁不住掩面痛哭起來。
11時,飛機飛回庫爾勒。16時,庫爾勒方面通過電台通知:按照慣例,余純順遺體就地安葬;法醫前往余純順遇難地,對他進行解剖,並對現場進行勘驗;飛機下午17時起飛去前進橋。我們要求順便帶幾把鐵鍬和十字鎬,用於挖掘墓穴。
18時10分,飛機由庫爾勒飛來降落在前進橋。在此之前一個小時,前天一早去樓蘭以東7公里處尋找余純順的最後兩人趙子充和孫鷺,平安返回。年過花甲的趙,聽到余純順遇難的噩耗,頓時淚流滿面。這次乘機前來的有巴州公安局偵支隊政委尹寶林、副支隊長艾里哈木以及兩位法醫。飛機還帶來了花圈、墓碑和工具。
18時15分,我和中午趕到的刑偵人員及3名後援人員走進機艙,去羅布泊勘驗現場掩埋余純順遺體。
飛行約25分鐘后,余純順遇難地到了。因為預報大風即將來臨,飛機在這裡只能停留45分鐘。我用紅漆在閃礫的機艙上寫好了墓碑上“余純順壯士遇難地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立”幾個字。同一位機組同志一起把木碑扛下飛機。大家揮汗如雨很快為余純順挖好了墓穴,它長2米、寬1米、深1米,就在他遇難處的西北角,正處於背風處。法醫正緊張地勘驗現場,對余純順的遺體進行解剖。機長不住地看著手錶,輕聲告訴我們抓緊時間,我甚至來不及和同機趕來的戰友、老偵察員孫國際多說兩句話。忙碌中下葬的時間到了。余純順的遺體被放在一條雪白的被單上,由法醫等4人各提一角越過鹽鹼丘,輕輕放入墓穴中。上面蓋著他那條綠色睡袋,他穿了一路的白底紅條T恤、背包、草帽、紅色太陽鏡、睡墊、膠鞋和那把藏刀,被一起放入墓穴,同餘純順一樣,永遠留在了羅布泊。
一鍬鍬沙土一塊塊鹼殼不斷堆積,終於成為一個墳墓。我們幾個人口乾舌燥、大汗淋漓,渾身上下沾滿了沙土。到了和余純順告別的時候了。上海電視台和巴州旅遊局敬獻的兩隻花圈分別放在兩邊。花圈上的紙花和輓聯在微風中發出輕微的響聲,彷彿在悲泣低唱著一首輓歌。
19時35分,安葬了余純順后,飛機返回前進橋,考慮到趙子充年過花甲又連日奔波,決定讓他乘飛機返回。我和其他人在清理營地后,立即乘汽車撤離這裡。
遇難原因
迷路和高溫,導致余純順遇難
余純順在羅布泊不幸遇難的地點,坐標為E90°19'09'',N40°33'90'',彭加木失蹤地的坐標為E91°46'71'',N40°11'29''。一個在羅布泊西北,一位在羅布泊東南,兩地距離160公里左右。他們的遇難和失蹤整整16年,這給原本就波詭雲譎撲朔迷離的羅布泊又罩上了神秘的光環。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種種推斷、猜測不一而足。
1996年6月19日上午,我們在由前進橋乘車返回庫爾勒途中,攤開了地圖、余純順穿越羅布泊線路圖、筆記本。對幾個重要坐標點的經緯度進行了認真核對比較。
我們發現:余純順遇難地的經緯為E90°18'44'',N40°34'34''處時,應向右拐西行。兩組數字一對比,事情就再清楚不過了。余純順走過了T字口,徑直往南偏東方向走了,顯然他在判斷方向上產生了致命的失誤。
從飛機上看,距余純順遇難地約50米的那條路一直向南延伸。余純順如果沿T字口向西再走至多3公里,就能到他6月10日放置一箱水和一箱乾糧的第一個宿營地。
他錯過了T字路口,也使自己錯過了生還的機會。
十多天還在庫爾勒時,余純順曾說有個朋友將要從美國帶給他一部GPS。但直到他遇難,也沒帶到,倒是上海電視台帶來了3部。出發前我們建議他隨身帶一部,他苦笑著說:“我走了8年,從來沒有用過這玩藝兒。現在又有這麼多事,哪有功夫擺弄?如果給我3天時間,我一定學會用它!”羅布泊盆地沒有任何參照物,除非使用GPS或者有豐富的經驗,常規的辨向手段,在這裡不起任何作用。這恐怕是余純順始料不及的。
在《關於對余純順屍體檢驗報告》中,結論為:“……余純順的死因,系在高溫環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脫水,全身衰竭而死亡。”解剖后:“胃內未見食物殘留及胃液,胃粘膜有小片狀褐色出血。”這說明,余純順自6月11日早飯後只補充了少量的水,而沒有補充任何食物。
不容置疑,正是迷路,常人難以忍耐的高溫,最終導致了余純順的死亡。如果他能按照預定路線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麼,滿滿一箱礦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飲用和補充食品,而且也會有剩餘的水能夠用來降溫。這樣他就可以免遭厄運。
將近一個世紀,羅布泊探險的先行者斯文·赫定,曾在羅布泊經歷了九死一生,幾遭滅頂之災;20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彭加木、余純順不幸永遠留在了這裡。
深居內陸,長期與世隔絕,加上風沙乾旱,冬滲奇寒,夏蒸酷暑的惡劣氣候,在5月和6月進入這裡,在季節的選擇上,余純順是缺乏科學性。
羅布泊為“生命禁區”,並被冠以乾旱不毛的“死亡地域”的惡名。然而探險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從來就是密不可分的。伴隨著1997年秋季“百名中國人徒步穿越羅布泊荒漠”大規模探險旅遊活動圓滿成功的腳步,“到羅布泊去”的熱浪正興起。1998年新春之際,又有兩批南方遊客,在隆冬季節進入羅布泊。1998年10月,由50名台灣同胞、5名廣東遊客組成的“港澳徒步縱穿羅布泊的探險團”,經過長徒跋涉,到羅布泊湖中心,身臨余純順墓地,為壯士獻上了紙花、香煙和他們節省下來的礦泉水。
1988年7月1日開始孤身徒步全中國的旅行、探險之舉。行程達4萬多公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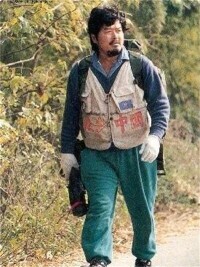 足跡踏遍23個省市自治區。已訪問過33個少數民族,發表遊記40餘萬字。沿途拍攝照片8千餘張,為沿途人們作了150餘場題為“壯心獻給父母之邦”的演講。尤其是完成了人類首次孤身徒步穿過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征服“世界第三極”的壯舉。
足跡踏遍23個省市自治區。已訪問過33個少數民族,發表遊記40餘萬字。沿途拍攝照片8千餘張,為沿途人們作了150餘場題為“壯心獻給父母之邦”的演講。尤其是完成了人類首次孤身徒步穿過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征服“世界第三極”的壯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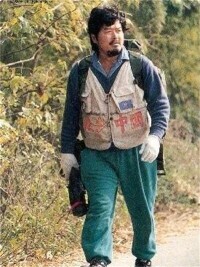
余純順個人照
1996年6月13日在即將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羅布泊全境的壯舉時,不幸在羅布泊西遇難。
在羅布泊縱深處的余純順墓前,人們無不為余純順壯志未酬,英年早逝深感痛惜。同時耳邊也不斷響起一位大智大勇的行者,對中國探險族的一席忠告:“探險應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精神,物質條件、科學的智慧而進行的行動。”
余純順長長的鬍鬚,紅而發亮的臉膛,說話坦率流暢而富有激情;他那豐富多彩的探險生活,但這已是以前的往事。他已經離開了我們。
余純順是一個十分看重名聲的人,也許這同長期受到歧視和壓抑有關,他太想出人頭地了。 他想體面地生活,想讀書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自學考到大學也沒人用他,妻子又同他離了婚,自卑到了極點。他想通過非常的舉動,非凡意志力來證明他作為男子漢的存在價值。徒步走中華,遍訪55個少數民族,這是擺脫困境,表明他的價值的最佳選擇。講實話,走羅布泊也是追逐名聲的結果。
他想體面地生活,想讀書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自學考到大學也沒人用他,妻子又同他離了婚,自卑到了極點。他想通過非常的舉動,非凡意志力來證明他作為男子漢的存在價值。徒步走中華,遍訪55個少數民族,這是擺脫困境,表明他的價值的最佳選擇。講實話,走羅布泊也是追逐名聲的結果。

余純順旅行圖
余純順是極講義氣的人,走到哪裡總給我來信報平安,每年新春總收到他的賀年卡。余純順是個多情的人,英雄愛美人,也算人世間佳話了。他在漫長而孤獨的徒步生涯中,有沒有紅顏知己?當然有了,在起初一二年,他特別謹慎,後來幾次從死亡線上掙扎歸來后,就順其自然了,有女人喜歡他,他也喜歡人家,這是他們的私事,無損於作為“壯士”的形象。
余純順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征服慾望,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走遍西藏的人,非常了不起。他常愛說征服什麼什麼。有人登上珠峰,就說征服珠峰,其實不妥當,你不過走一走而已,珠峰不是照樣昂首挺胸嗎?也許余純順多次死裡逃生使他變得過於自信,以至於誇大人的生存能力。余純順是一位誠實的旅行家,走了8.4萬華里,沒有一點虛頭,他的腳從41碼變成43碼就是最好的見證。不管怎麼說,作為旅行探險家也是當之無愧的,這也是至今人們懷念他的緣由。
此時距余純順羅布泊遇難已經23年之遙了,時空給了我們足夠的空間去思考,我們也因此能夠審視而不是仰視地對待這個已經離開我們的探險家,他不再是被新聞媒介炒作包裝出來的神話,他有著與普通人不一樣的偉大,也有著和常人一樣的缺點。雖然關於那次遇難曾經眾說紛紜,但現在看來它早已沒有意義。我們能夠記住的,是他帶給我們的徒步穿越荒涼之地的韌性、萬里山河的雄奇以及虛幻背後的真實,人性的複雜與單純、人生的殘酷與美好和長久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