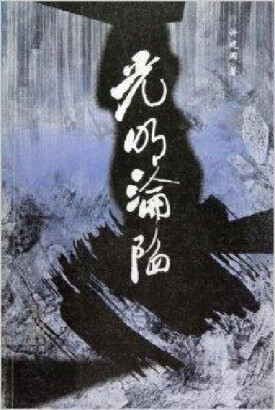光明淪陷
光明淪陷
《光明淪陷》是許建國同志的中短篇小說集,收錄有《鄉鎮換屆》、《光明淪陷》、《災年》、《一路順風》、《水火相容》、《福兮福兮》、《真皮馬甲》、《良莠》、《鄉間故事三題》等9篇作品,近12萬字。語言自然簡練,卻不乏生動,很有幾分老到。
許建國,男,1967年生於湖北省谷城縣,1986年參加工作,當過教師,做過鄉鎮幹部。2002年起從事專業創作,有小說、劇本、報告文學見於報刊。
光明淪陷
福兮福兮
真皮馬甲
一路順風
災年
水火相容
鄉間故事
鄉鎮換屆
良莠
廖紅梅喊楊鐵牛起來吃飯的時候,鐵牛正把腦袋窩在被子里。廖紅梅以為男人悄悄起了床,轉身欲走,隱約間卻聽到一陣呼嚕聲,她一把掀開被子,揪住男人的耳朵,把那顆腦袋拎了出來。鐵牛故意裝睡,腦袋耷拉著,不做絲毫動彈。廖紅梅便尖了聲調說:“黑子的媳婦昨晚跟人睡了,黑子薅住她的頭髮往死里揍呢。不起來看看?”
鐵牛一下子睜開了眼,他覺得這消息就像媳婦隨身帶進來的油煙子一樣還有些滋味。他嬉笑著問:“跟哪個?”媳婦拉長了臉不答,鐵牛便收了腦袋,蜷縮在被窩裡想象黑子媳婦那兩條像剝了皮的青蛙一般細嫩白凈的大腿,想著想著竟來了興緻,就喊媳婦過來。媳婦迴轉身問啥事,鐵牛一本正經地說:“你不是說今天上街嗎,也不換換衣服?”說著伸出胳膊拽過媳婦,要脫她的衣服。媳婦臉一板說:“邪貨兒,只要送了電,人家也跟你睡。”說罷,屁股一扭,走了。夫妻私事,媳婦並不遷就鐵牛,這令鐵牛很失望。鐵牛常想,逮住機會了,一定給她點顏色看看。然而,真到了那一刻,依舊是猴急猴急地完成任務了事。
鐵牛懶洋洋地起來,把飯扒到嘴裡,才覺得沒有胃口,便丟了碗,抬腳出了門。媳婦喊住他說:“天陰這很,不弄點兒柴火好過年?”鐵牛很誇張地抖了抖披在肩上的褂子,歪著頭啾了瞅像支在四圍山上的天幕,說:“冬天的太陽就像我一樣愛睡懶覺,過一會兒它就會起來的。”媳婦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沒屙泡稀屎把自己照照,也敢比太陽。”見媳婦收了脾氣,鐵牛趕緊說:“我去打聽一下黑子的媳婦跟哪個睡了。”說罷,不等媳婦答話,拔腿就走。
鐵牛惶急地走到公路上,就有人迎著他說:“電老虎兒,黑子的媳婦跟人睡了,黑子沒去找你的事兒?”鐵牛並沒在意,只問:“咋就跟人睡了呢?”那人說:“還不是沒有電?”鐵牛一驚,想說偷情咋就跟沒電扯到一塊兒了呢,怕有推卸責任之嫌,便沒說出口,只在心裡抱怨媳婦沒把話說清楚。這時,又有人圍了過來,鐵牛方才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要說這事也是怪黑子,誰叫他恁迷《水滸傳》?停電以後,黑子的心裡就一直懸著林教頭的去向,想來想去,就想到了陳半仙,偏偏陳半仙是個半拉子,書看得半懂不懂,頭腦中的一部《水滸》大部分是自己的創造,說出來的自然是牛頭不對馬嘴。黑子不聽倒還罷了,越聽心裡越懸。昨天晚上,黑子實在熬不住了,就騎了車子上街看電視。黑子的媳婦估摸黑子不會回來了,就留了一個男人在自己被窩裡過夜。沒想到,黑子看畢電視又摸黑回來了。
幾個男人把一個平常的偷情故事極富主觀色彩地演繹一番之後,都忍不住笑彎了腰。笑畢,便問鐵牛哈時候來電。鐵牛裝出不懷好意的神情,說:“等你們的媳婦都跟人睡了再來。”有人就說:“我又不喜歡看電視。”鐵牛沒想到竟是這麼瓷實的男人,便調侃道:“死守不是辦法,我倒有個防止媳婦跟人睡的小竅門。”那人眯了眼睛問:“啥竅門?”鐵牛神秘兮兮地說:“耳朵使過來,我悄悄跟你說。”鐵牛說一句,那人笑一聲,說完之後,兩人都是哈哈大笑。
眾人忍不住,便說是鐵牛的經驗,應該好好推廣。鐵牛大大咧咧地說:“推廣可以,你們哪個的電費交了就給哪個說。”眾人一聽,哄地一聲就要散開。鐵牛急急地喊道:“真不怕媳婦跟人睡呀?”有人問:“村幹部的電費都交了?”鐵牛又抖了抖褂子,把衣兜抖到面前來,摸出一本收據說:“我這就開票去的。”那人說:“我們看了收條自然會交的。”鐵牛便罵,惡狠狠的樣子:“就是來了電,也不給你們這些龜孫子送,非等你們的媳婦跟人睡了不可。”眾人不理,各自走開。
鐵牛邊往村長家裡走邊想著剛才的笑話。他覺得冬天的男人們除了滿足女人的需要外,實在無聊得很,扯閑話打麻將只是無可奈何的活兒,要是有一件像夏收夏種那樣緊急的事拴住他們的心,吃飯幹活,累得死去活來,黑子的媳婦就是跟人跑了也沒人注意的。
鐵牛到村長家的時候,村長正幫著他的媳婦往黃姜上潑開水。黃姜是一種藥材,山嶺溝壑多有生長。早幾年賣一兩毛錢一斤還要切片曬乾,如今挖出來的活根就賣到好幾塊。鐵牛知道黃姜的提取物皂素廣泛應用於醫藥及護膚製品,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污染太大,狗日的闊佬把廠子關了,沒錢的傢伙們就不管不顧地上馬投產。窮人常被腳背上的錢迷了眼呢。村長的媳婦自然不爬高下低到山上去挖黃姜,她收購別人的再用自行車馱到城裡去賣,從中耍點兒秤桿再賺點兒差價,加上潑水這些手腳,利潤倒也可觀。
村長門前的道場上鋪滿了黃姜,先是村長在前面潑水,村長的媳婦在後面撤土坷拉麵兒。村長的媳婦嫌村長潑得不均勻,土坷拉麵兒粘不住,就叫村長過來,她自己去潑。村長剛抓了一把土坷拉麵兒,就看見了鐵牛。村長臉一紅說:“就是女人心黑。”鐵牛應道:“城裡的收購部都是奸商,他們的錢不賺白不賺。”鐵牛雖不為商,卻不乏奸滑。他知道村長重利但更重面子,於是借驢下坡,照顧了村長的面子,又不使自己陷於難堪。果然,村長的媳婦把一張老臉笑成了一朵花:“看,還是人家楊電工想得開,哪像你,門板一塊。”
1982年,我15歲,正在懵懵懂懂憧憬未來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洗劫了家鄉的小山村。如果撇開破壞性不說,洪水的確是壯觀的。渾濁的浪頭掠地漫天,高亢的轟響振聾發聵,疾速的奔騰威猛無比。它帶給人的,是震撼,更是激情。
此後,洪水便時時在心頭澎湃,直到有一天我拿起筆,記錄下當時的情景。這,便是我創作的緣起。
然而,作品的淺薄是顯而易見的。小說,應該關在語言,巧在結構,厚在思想。這需要紮實的功底,豐富的閱歷。41年,我僅僅從小山村走到小縣城,步伐實在太小。我也設想過走出去,觸摸一下高樓大廈的光怪陸離,感知一下城市生活的燈紅酒綠。但是,就這個孱弱的身板,愚拙的腦袋,又能騰起多大的浪呢?因此,筆下都是身邊的小人物,思想也只是農民式的簡單質樸。真正貽笑讀者諸君了。
將零散的東西集結起來,緣於一個重要他人。我自小缺少父愛,溫軟有餘,陽剛不足。寫小說本是興之所致,聊以自慰或者發表在日漸式微的文學刊物上尚可,哪敢在鄉親面前獻醜?所幸,遇到一個可以將善良和醜陋都交付出去的人。他說,歸攏自己的作品,不是炫耀成績,而是梳理思想。我方有勇氣回眸十多年的創作。
我是相信緣分的。否則,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哪兒有恁多巧合呢?金秋時節,去拜訪湖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羅丹青先生,幸遇著名書法家楊斌慶先生。楊先生曾經擔任省市重要領導,我輩只能仰視,怎敢設想有此機緣呢?當先生問起我的工作時,我說正打算出一本小說集,並貿然懇求先生惠賜墨寶,不想先生滿口應承,隔日競書好寄我。
陳懷國先生是谷城的驕傲,是我仰慕的文學導師。陳先生的小說代表作《毛雪》,蕩氣迴腸,我是躺在被窩裡一口氣讀完的;先生編劇的電影《橫空出世》,氣勢恢弘,讓無數人嘆為觀止。托朋友張少軍先生將書稿呈送陳懷國先生,並師友陳波先生電話聯繫,陳懷國先生擱下萬忙的工作,欣然提筆,為本書作序。
散海明先生長我六歲,他在鄉鎮任黨委書記時,我是普通工作人員。散先生正直的品行、儒雅的風範、幹練的作風令我受益匪淺。為本書的出版,散先生操心勞頓,給予了我無私的關懷。
四川人民出版社也為本書付出了辛勤勞動,尤其是蔣躍梅老師,為了核正一個方言或典故,她不惜翻閱大量資料,直到找到出處為止。小說在刊物發表時,有些篇什的對話用了引號,有些為了閱讀方便,沒有使用。為規範起見,蔣老師一一將其改正過來。
謹此,向所有關心我的老師、朋友道一聲:謝謝!您的恩情猶如浩浩洪水,我無以為報,只有不懈努力,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許建國
2008年12月於谷城
許建國是一位做人與作文都十分真誠的作家,收錄在這本集子中沉甸甸的九篇作品,便是這種真誠最好的印證。許建國至今仍生活在離他出生不遠的谷城縣城裡,與他作品中的一干人物朝夕相處,稍不注意,便會招來各種麻煩。但他卻始終執著於他認準的“現實”,或恨或愛,寫得毫無顧忌,其做人的真誠可見一斑。許建國的創作始於上世紀80年代。20多年裡,中國文學潮起潮落,幾度興衰,如今早已風光不再,作家更是如昨日黃花般的落寞了,而他卻還是那樣端坐於小縣城的書桌前,守著清靜,也守著清貧,寫他的小說,寫他的一個個中篇或短篇。無論如何,在今天這樣一個喧囂的時代,這份對文學的虔誠讓人感動。
今天的作家寫影視的多了,寫小說的少了。寫小說的作家中,寫長篇的多,寫中短篇的少了。原因主要是經濟利益所致,這一點作家和讀者都十分明白。小說比影視難寫,作家和讀者也明白,但中短篇比長篇難寫,這一點讀者就未必明白了。中短篇靠的是功力,也最容易讓一個作家露餡,而長篇則常常能為一個作家遮醜。官員作家、老闆作家,一本本出著長篇的同時,閑暇之餘寫詩填詞,唯獨和中短篇小說沒什麼瓜葛,不是不屑,恐怕是不能。寫中短篇苦、難、無名利可圖,總之是出力不討好的差事。許建國不可能不明白這些。明白了還要堅持,這就不僅僅是感動,而是讓人肅然起敬了。
《光明淪陷》收錄了許建國近年創作的9個中短篇小說。集子的選擇頗具匠心,清一色的鄉村題材,清一色的小人物,囊括了目前鄉村的方方面面和各色人等,呈現出一幅完整的鄉村圖畫。但和許多人云亦云的鄉村題材不同,許建國筆下的鄉村沒有轟轟烈烈、虛張聲勢的所謂改革,只有寧靜中的一點喧囂,貧窮中的掙扎與奮鬥,時代的烙印被內斂了,更多地體現在人與人或人與自身靈魂的搏鬥中。說實話,我更相信這樣的鄉村。在看慣了被文學作品不斷現代化、城市化、乃至洋化了的中國農村和農民之後,許建國帶給了我們一種久違的真實。
許建國的作品有一種質樸的真實,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小說,他的人物都是有“道德靈魂”的。這很符合中國小說的傳統。許建國曾是一名鄉村教師,把“道德靈魂”由學生而延伸到小說,在他也是順理成章的。的確,他的小說都有一個可以納入道德範疇去衡量的主題,他的人物或俊或丑、或狡詐或世故,但都是有著道德良心底線的。他的人物大多都有些“一根筋”,如電工楊鐵牛,為了村裡通電費盡周折,甚至連命都搭上了;為了讓村民能過個好年,村支書用盡手段;還有拿不到報酬的民辦教師,不惜花錢買來城市戶口轉為公辦教師,轉了還是沒報酬,但仍然筆直地站在講台上,站給上級看,站給“體制”看;甚至連公共汽車上的“我”,為了看一眼漂亮姑娘,一直跟隨到姑娘下車……許建國的手法簡單而有效,這些人物的“一根筋”反而有了彈性,有了張力,有了幾分質樸的可愛,也有了我們看后的會心一笑乃至過目不忘。
許建國是一位捨得在情節、細節和語言上下工夫的作家,尤其是語言,自然、簡練,卻不乏生動,很有幾分老到。
就這本集子中的作品而言,可以看出,許建國比較注重作品中的矛盾和戲劇化衝突,而且做的不錯。但我想說的是另一種矛盾:一個作家面對小說的矛盾。某種意義上說,作家寫小說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有限的文字和豐富的語言是矛盾,因此我們常常會有詞不達意的苦惱;豐富的語言和更豐富的大千世界是矛盾,因此我們常常會有“心中有,口中無”的尷尬;生活雜亂無章,小說卻必須要有結構,這更是矛盾,如此等等。這些矛盾牽涉到小說技術與藝術的方方面面。這些矛盾或許根本無法解決。作家要做的無非是多想一點辦法和找到一點自己的辦法而已。我想,這正是許建國在今後的創作中該下苦工夫的地方。好在許建國還年輕,有的是力氣,更有的是未來。
陳懷國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