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與諸甥侄書
獄中與諸甥侄書
《徠獄中與諸甥侄書》是由南朝·宋范曄所做,出自《宋書·范曄傳》,作品採用書信體裁,書寫了自己的一生。
吾狂釁 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庄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徠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者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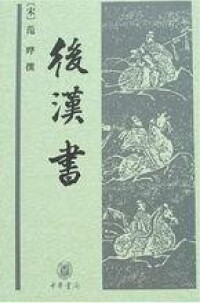
獄中與諸甥侄書
我小時候學習並不怎麼勤奮,成熟得亦比較晚,一直到了三十歲左右才開始樹立志向。從那以後,轉而中心感化,自己估計就是到老,也不會停止這一行動的。常常有些精微深刻的見解,難以用言語表達完整。我天性不喜歡鑽書本,腦子也不靈,稍微費些精力便頭昏腦脹,而又缺少能言善辯的口才,所以也難以因此取得功名。至於所獲得的一些見解,一般都出於內心對事物的領悟。文章寫得好些了,但缺少才氣,思維鈍澀,所以每每揮毫寫作,寫成的卻幾乎沒有一篇能完全令人滿意。
我常以作一個文士為恥。一般的文章常耽心或只求形似而缺少內涵,或急於言情而忽略文彩,或辭不達意而影響主題的表達,或過份注重音律而妨礙了文意。雖時有擅長於作文的人,但大多數都不免這些毛病,正好比技藝精妙的工匠在已有五彩花紋的圖像上再作畫,貌似好看,結果一無所得。我常以為,文章主要是用來表達情志的,因此應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若以意為主,文章的主旨必然會顯現於讀者面前;做到了以文傳意,那麼,就不會出現文不達意的現象。然後才能達到內容完美,聲調鏗鏘。這當中各人的情性旨趣,雖然各種各樣,名目繁多,但在這不同中有著一定的規律法度。我自己認為很懂得其中的方法奧妙,也曾經跟人談起,但大多數人都不能理解賞識,我以為這或許是各人看法不同的緣故罷。
我能夠識辨宮商五音,也能分得清清音濁音,這都是本已存在的語音現象。可是看來自古至今許多文人,卻往往不完全明白這一點;即使懂得一些,又未必從根本上理解。我說這些話都是有事實依據的,並非空談。比如年少一輩中的謝庄算是最能辨別區分宮商清濁的了,可是寫出來的文章卻並不如此,這是因為沒有注意,文不拘韻的緣故。而我的看法是拘韻與否並沒有固定的標準,只要能夠表達出難以言傳的情事,符合語音的頓挫抑揚、高低變化就可以了。但我所具有的天分,卻仍未能完全達到這一點,因為我自己寫的卻又大多是用於公事的不拘韻的實用文,很少有超出這一範圍以外的文字,常常以此為一大遺憾,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無意去追求文名。
本來我不曾涉獵史學,對於歷史政治問題常常覺得不能理解。我既完成了《後漢書》的編纂,便因此而掌握了其中的端緒。我仔細通觀古往今來的有關著作及其評論文字,幾乎很少有使人贊同的。班固最負盛名,但他按自己的想法著史,不能審辨、闡明各個歷史現象之發生、發展及其歸宿(不再遵守《史記》的先例而通古今之變)。《漢書》的贊文實際上一無足取,只有十志值得推崇讚揚。我所著的《後漢書》,內容的廣博宏富不一定比得上他;但史料的處理和編纂體例的創新,我不一定比之有愧。我所著的各種傳論,都含有精深的意蘊,因為帶有評判裁定的性質,所以就寫得簡明扼要了。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篇序論,更是筆勢縱橫自如,實在是天下少有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時弊的文字,往往不遜色於賈誼的《過秦論》。所以我曾經將《後漢書》與《漢書》作過比較,結果不僅是不感到慚愧而已。我曾想把諸志全部作成,凡是《漢書》中有的都撰寫完備。雖然史實不一定面面俱到,但要使人看後有十分詳盡的印象;又想就某些歷史事實發些議論,以匡正一代的得失,這一設想未能成為現實。《後漢書》里的贊文,應當說特別體現了我的見解與思想,幾乎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文字變幻無窮,同是議論文字卻內容各不相同,以至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來稱許它。這書刊行以後,一定會獲得知音讚賞的。《後漢書》的序例僅僅是舉其大概,還有一些細小具體的問題,實在太多了。自古以來,規模宏大,思慮精密,沒有哪一家能做到這樣的。因為怕世人貴古賤今,不一定能了解詳細,所以就恣意狂言,自誇自吹了一通。
我對於音樂,鑒賞審別能力比不上自家彈奏的能力,而又以所精通的不是正聲為憾事。不過真正達到了音樂的最高境界,雅與不雅又有甚麼區別呢!這當中的意趣,確非言語能表達完盡。那弦外之響,意外之音,真令人不知其從何而來。雖說非雅之音很少有值得稱許的地方,但其中的意蘊神韻卻並無窮盡。我也曾以此授人,可惜一般從學的士子和百姓中,竟無一個酷似神肖的。這一技法恐怕將永遠失傳了!
我的信雖然稍有深意,但行文畢竟不暢快。我到底沒有成功。我常常感到痛恨羞愧。

范曄
這是范曄在獄中寫給甥侄約、謝緯等的一封信,也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信中雖說“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而事實上這“狂釁”正反映了他無視封建禮法的叛逆精神和雖殺身而無悔的進取態度。
范曄以《後漢書》垂名青史,然而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貢獻也不容忽視。本文關於文學特點、宮商聲律以及文筆之分的論述,雖然比較簡略,語焉未詳,卻開了文學概念由先秦兩漢的尚實崇用轉變為六朝的緣情綺麗的先聲,在文學批評史上,無疑應佔有重要地位。
因為是書信,故全文侃侃而談,平易親近,讀來真切感人。至於文中自詡《後漢書》為“天下之奇作”,“殆無一字空設”,以至“乃自不知所以稱之”,則表明他的自負之高。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人。南北朝時期著名史學家。范曄早年曾任鼓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后官至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因事觸怒劉義康,左遷為宣城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太守。後來他又幾次升遷,官於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有人告發他密謀擁立劉義康,於是以謀反的罪名被處以死刑。
范曄一生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則是撰寫了被後人稱之為前四史之一的《後漢書》。范曄以《東觀漢記》為藍本,對其它各家撰著博採眾長,斟酌取捨,並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刪繁補略,寫成《後漢書》。由於他的“後漢書”文約事詳,逐漸取代了前人的著作。
《後漢書》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紀傳體例,敘事簡明而周詳,記事有重點而不遺漏。其敘事的特點是以類相從而不記年代的先後。有些篇目的內容頗有增益,如《東夷列傳》就較詳細的記述了當時朝鮮半島諸國和日本(當時稱倭國)的情況,又《南蠻傳》也為前所未載。《後漢書》又新立了一些類傳,如《逸民》、《列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