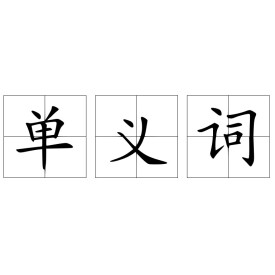單義詞
漢語詞語
單義詞被認為是辭彙里的純金,是辭彙里的晶體,絕對的原裝貨,僅僅指稱人們自古以來要它指稱的意義。如今,這樣的詞已是鳳毛麟角了。我們用的詞大都是混合詞,是由古老的,用過的舊詞湊合成的,這湊合的過程就像是廢品的回收利用。我們周圍四處堆滿了棄置不用的詞,丟棄在我們頭腦的四郊,像一堆堆破銅爛鐵。語言中的每一個詞都有一定的意義。比如“學校”,指“專門進行教育的機構”;“學者”,指“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等等
當你真的邂逅在一個原湯原味兒的單詞時,那體驗就有些驚喜參半了,好像在箱篋里的舊中學年刊中看到了一個朋友的照片。那些詞都非常老,而那些最意味深長的詞,都可上溯到印歐語中的詞根,它們後來成了不同語言里同源詞的祖先。這些不同語言有梵語,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還有很久以後形成的英語的大部。Sen意為舊的,老的(Old);spreg意思是講話(Speak);swem是游泳(swim);nomen是名字(name);porko是頭小豬(pig);dent是一顆牙(tooth)。Eg是我(I)和我的自我(my ego), tu是你(you) , me則是我(me)。Nek是死亡(death) 。Mormor是低語(murmur)。Mater,pater,bhrater和swesor是最親近的親屬(父、母,兄弟,姐妹),而nepots則是甥侄和甥侄女兒(nephews和nieces) 。 Yero是一年(a year) 。Wopsa是一隻黃蜂(wasp),aspa是棵楊樹(aspen)。Deru是棵樹(tree),同時也是某種耐久而真實(true)的東西。Gno是知(to know) 。Akwa是水(water),而bhreu則是沸(boil)。使用基本的印歐語,再加上揮手,你可以走遍天下,差不多跟用紐約英語一樣方便。
當然,也有些最初的辭彙徹底地改變了意思。Bhedh是今天珠子(bead)的前身,但它的本義是要求或吩咐(bid);bead一開始意指祈禱。Dheye意為看和見,到了梵語里成為dhyana,意為靜思,到了巴利語中為jhana,到了中國語里為禪,到日語而為zen(禪)。
你可能認為,現代科學大概一直在創造簇新的單義詞以滿足其需要,可事情並非如此。我們的大多數表示新事物的辭彙是翻新的舊詞。一百年前開始使用的詞熱動力學(thermodynamics) ,是一家古董鋪子:印歐語的gwher,意為熱,後來成為希臘語里的thermos,而印歐語里的deu,意為做,成為希臘語里的dtunesthai,意為能做什麼,於是有了能動的(dynamic) 〔dynamite(甘油炸藥)、 bonus(獎金、禮品)和bonbon(夾心糖)來自同一個deu〕。計算機行話里的二進位數碼(bit) ,儘管造的時候意思最不含糊。其組成部件是binary(二進位的)和digit(手指、數字),然而,它的來源卻有著糾結不清的意義: binary來自dwo,意為二(two)。這個詞還生出twig(小枝),double(成雙)和doubt(懷疑);digit起源於deik,意為展示或教導,後來跟另一些詞結伴來到英語,它們是token(記號),paradigm(範例),ditto(同上),還有toe(腳趾頭)。
核酸(nucleic acid,來自ken,後來是knu,加上ak)是某種堅果,跟某種鋒利的東西結了對兒。
霍亂病毒(cholera toxin) ,讓一個初識我們文字的外人翻譯出來,可能是一副錚明瓦亮的弓箭。Ghel最初的意思是明亮的,後來意為黃色;它先後成了希臘語里的ghola和khole,意為膽汁,後來成為英語里的choler(膽汁症)和cholera(霍亂)。Toxin起初是tekw,意為跑或逃,後來成為波斯語里的toxsa和希臘語里的toxon,意為弓和箭;病毒的意思大概來自塗在箭上的毒,或者,如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所說,來自紫杉樹taxus,其木可制最好的箭,而其漿果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有毒的。
指稱毒(poison)的那個詞來路更為曲折,頗像一個耽擱已久的轉念。它來自poi,意為喝,後來成為拉丁語里的potare,由此又生成potion(一服麻藥)〔還有symposium(研討會) ,來自sun,意為在一起,加上posis,意為喝〕。那個有毒的含義是隨著媚葯這個概念而出現的,此後,毒這個觀念才進入意識當中。
在venom(毒,毒液)背後,也有段類似的稀奇古怪的歷史。這個詞一開始是wen,意為希望或意願,或多或少直接導致了win(贏得)。在演化的途中,它的一枝通往venus(性愛),venery(性慾)和venerate(尊崇),這些都是愛的變種。媚葯稱作venin,不知怎麼,這個詞漸漸有了今天的毒或毒液的意思。
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毒和毒液能來自媚葯。或許,當時的藥理學還很原始,很玄乎,跟毒物學只隔一層窗戶紙。或者,當時在常識上大家有個共識,就是,任何意在引誘虛假的愛的化學添加劑,在本質上都是某種毒物。這透露了初民的一點重要的可愛之處,他們憎恨弄虛作假的愛,於是就把毒液和毒物從那些愛情騙子那裡剝奪了來,還給蟲豸的毒刺和蛇的毒牙。
病毒(virus)的概念對我們來說雖然很新鮮,可virus這個詞卻很古老。它的詞根是weis,意為流動,是徐徐流出、分泌(ooze)那個意思。那個詞先是從古英語的wase到了中古英語的wose,於是就成了ooze本身。後來,它派生出一個意思,指某種彎曲曲滑溜溜的東西,由此,鼬鼠得到了它的名字。此後產生的聯想更令人不快,意指某種討厭的,不衛生的,有毒的東西(noxious),結果有了viruses(毒素,毒害)的virulence(毒性)。湊巧,noxious來自nek,意為死亡,是從拉丁語里的necare和nocere來的,這些詞為我們提供了necropsy(屍檢)及其同源詞。甘露(nectar)是神的飲品,因為它是防止死亡的(tar的意思是克服)。
聽起來這像是一系列的偶然事故,也許,語言的進化大體上是種碰運氣的事,就像動物的進化一樣。儘管這檔子事里包含的許多事實已被兩百年來探微索隱的語言學蓋棺定論,可是,在這整個行當中,還是有些普遍的、不可避免的、高度不可思議的性質。假如這就是辭彙的進化方式,那麼,這種進化似乎是依賴很多純粹的運氣,或者,像法國人說的,是hazard(古法語,擲骰子賭博;英語,碰巧,意外,危險,冒險,擲骰子賭博)。
運氣(chance) ,現在終於有個詞表達它了。帕特里奇(Partridge)給了它近兩欄的篇幅、最小的小號字排印的,但不只是在這一個詞條下。如果你要查到chance,你得找到cadence,那個詞最接近一個單義詞,可離單義詞還是相距甚遠。Cadence來自kad,意為倒下,落下(to fall, falling)。Kad導致了拉丁語里的cadere和梵語里的cad,意思還是倒下,有時意為死亡,從這兒,來了一大串意為冒險和暫時的詞:cadaver(解剖用的屍體),decay(腐爛),casualty(事故,死傷),deciduous(脫落的,暫時的)和casuistry(決疑法)。
如下的概念生髮出一些詞,如cadence(節拍),cadenza(華彩樂段,終止)和cascade(瀑布) 。Chance一詞,你大概已經猜到了,來自骰子(dice)的落地(falling)。
碰巧,hazard也來自dice,是經由古法語hazard和西班牙語azar(來自阿拉伯語yasara、意為玩骰子戲)來的。Dice得名於遊戲中用的骰子(die)。Die一詞來自印歐語do,最初意為給與,後來變成了donation(捐贈) ,dowry(嫁資),endow(捐贈),dose(劑量)和antidote(解毒劑)。在俗拉丁語中,動詞dare後來意為遊戲,生髮出一種遊戲用具datum,到了古英語為dee,後來成了die和dice。
很明顯,這類事情是不可能通過人的心智有意作成的。今天的語言,乃是無休無止的一系列小錯誤的結果。這些小小的錯誤一個接一個,把我們引回到遙無盡期的從前。這些辭彙只是被我們放了出去,讓它們在那片黑暗中飛翔,互相碰撞,以亂七八糟的方式配對兒,生出些野種,生出些隨機的雜種(混合詞),理性對之無可奈何。
試想如果我們在這上頭用了心思,我們將會作得多麼好吧。這裡需要的,就是更好、更清醒的組織,並且對於人類言語有更加有效的行管控制。一直缺少的就是管理。事情似乎是這樣的,有時還是可悲的:假如今天的大多數辭彙是通過這一不可思議的雜交過程造出的,那麼,雜交就是我們現在要加以控制的。我們需要學會的,是怎樣使一個詞與另一個詞結對兒,使交配能夠發生,然後選出我們所想要的小崽子。政府將需要參與其事,因為我們將需要在全球建立整個新的研究機構,在各國的首都佔據很大的地面,專門從事辭彙的養殖,就像上個世紀的那些農業實驗站一樣。辭彙養殖可以成為未來官僚機構的當務之急,像過去一樣,不過比從前組織得更好,委員會也更多。給以大堆儲備好的生育新詞兒的室內創造性,在可行時盡量把字母輸入改為數字輸入,由計算機賦予的能力加以財政上的優化,切中要害,針對目標,分清輕重緩急,我們最終會擺脫對過去的依賴。新的雜種,在我們本地的代理機構合成的混合詞,到時候就會取代那些印歐語詞,而帶有它們所有的原始性,前文化性,和叫人難為情的共鳴。
首先,我們應該用另一個詞來取代hybrid(雜種,混合詞)這個詞。並不是因為它沒有滿意地描述自己,而是它有那麼點不夠直截了當,不足以擔當我們要它擔當的科學任務。Hybrid是個較新的詞,很容易被不動感情地處置掉。然而,在它的背後,站著一個面色凜然的拉丁語詞hybrida,指的是野公豬和家母豬所生的不合意的崽子。這個詞在英語里毫無用處,直到大約17世紀,有人不經意地提到了雜種,指稱野豬和家豬的不正當婚配。可直到19世紀中葉,它才真正進入英語這一語言。那時,植物學和動物學都需要這個詞了。迅速發展的語言學也需要它,甚至連政治學上也用到了它(如國會裡的混合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