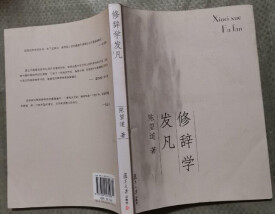修辭學發凡
修辭學發凡
《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巨著,作者陳望道先生,初版由大江書鋪於1932年分上下兩冊正式出版。全書12篇,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被學界奉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之作。
《修辭徠學發凡》把存在於漢語語文中的種種修辭方法、方式以及運用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則加以系統的闡釋,並且指明它的發展趨向。在闡釋和說明中,引用了豐富、適切的白話和文言的例證。對於系統地研究修辭學,對於古今作品的閱讀理解欣賞和練習寫作,都有助益。
一是引例豐富。所引用的書約250部,單篇論文約170篇,方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並蓄。
二是歸納系統,闡釋詳明。該書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系統而詳盡地分析歸納了漢語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全面概括了漢語語文中的修辭格式
全書共分十二篇。
第一篇概括地述說修辭現象和修辭學的全貌。指出修辭現象有消極和積極兩大分野,又指出修辭所可利用的語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辭所須適合的題旨和情境。
第二篇述說修辭所可利用的語言文字的可能性。
第三篇述說消極和積極兩大修辭分野的互相區別和互相聯繫。
第徠四篇述說消極修辭的一般情況。
第五篇至第九篇述說積極修辭,其中第五至第八篇述說積極修辭中的辭格,第九篇述說積極修辭中的辭趣。
第十篇述說修辭現象隨種種不同情況而變化,以及它的統一的線索。
第十一篇述說語文的種種體式,特別詳述了體性方面的體式。
第十二篇結語,述說修辭學的變遷、發展,並指出研究修辭學應有的努力。
《修辭學發凡》全書共有兩大特色:
一是引例豐富。所引用的書約250部,單篇論文約170篇,方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並蓄。
二是歸納系統,闡釋詳明。該書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系統而詳盡地分析歸納了漢語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全面概括了漢語語文中的修辭格式。
《修辭學發凡》初版於1932年,分上下兩冊,由大江書鋪在上海刊行。此後多次再版重印,至抗戰前已出八版,1976年本書刊行至第十五版;進入新世紀,2001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又將其列入“世紀文庫”第一輯加以刊行。
作者生前在本書再版重印時不斷有所修訂,其中作者特別予以說明的有:1945年本(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54年本(新文藝出版社),1962年本(上海文藝出版社)和1976年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修辭學發凡》的出版為標誌著中國修辭學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文論附庸狀態,並開始逐步建立起科學而完整的獨立的現代修辭學學科體系。該書是中國學術界最早引進和運用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的著作之一,並在修辭學研究中確立了“以語言為本位”的觀念,指明了修辭研究的語言學性質;創立了題旨情境說,指出了“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的理論綱領,開了現代語境學理論的先聲;建構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修辭學體系,對漢語辭格進行了全面總結。可以說該書擔當了完成中國修辭學研究重要轉型的歷史使命,引領中國修辭學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並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繁榮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石”和“現代修辭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評價則是修辭學界對《修辭學發凡》的共識。
雖然中國現代修辭學研究始於1905年湯撮常的《修詞學教科書》和龍伯純的《文字發凡·修辭卷》,但中國修辭學研究真正走向科學,卻是從《修辭學發凡》開始的。此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而完整的修辭學體系,回答了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現代修辭學已經走向成熟。《修辭學發凡》的影響,在修辭學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它不僅建國前被各大學用作教材,建國后也被多所學校採用,此後再版達十餘次。第二,它的修辭學體系和研究方法影響後世數十年,被許多著作所仿效和學習。第三,它培養出一批批修辭學研究人材。如著名學者鄭子瑜、張志公、倪寶元、吳士文等都聲稱是讀了《發凡》,才走上修辭學研究道路的。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和中國修辭學的傳承關係也於此可見。
劉大白在為《修辭學發凡》初版作的序言中說,正如《馬氏文通》(1898)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著作一樣,《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為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為初學者之津梁。”。葉聖陶先生評價:“有了這部書,修辭法上的問題差不多都已頭頭是道地解決了。”新加坡鄭子瑜教授說陳望道先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修辭學家”。張志公先生說:“這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使我認識到:修辭學是一個寬廣的、很值得探索的領域,是一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的學問。”
吳培恭在2004年12月29日的文匯報《筆會》上撰文回憶:我曾聽說,毛澤東主席非常關心望道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主席邀見他時,親切地對他說:“已看過《修辭學發凡》這本書,寫得很好,不過許多例子陳舊了些。”並問他是否繼續在研究。毛主席的關心更給了他信心和鼓勵。
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修辭學發凡》將“題旨、情境”分立而談,指出“消極手法側重在應合題旨,積極手法側重在應合情境。”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其“修辭的兩大分野理論”對修辭學的重大貢獻,使辭格理論系統化,但同時,其名稱卻存在著一些疏漏。《修辭學發凡》中將之命名為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詞典中對其解釋分別為:“積極,①肯定的,正面的;②進取的,熱心的。消極,①否定的,反面的,阻礙發展的;②不求進取的,消沉。”依此推之,用此對反義詞命名的兩大類別,顯然有失常理,並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及存在辭格概念不清、分類不準等情況。
不過,雖然《修辭學發凡》有著一定的不足,但一般認為,它所取得的成就及它給學術研究帶來的重大成果,還有他對修辭理論的非凡影響,都是舉足輕重的,是有著巨大價值的,而且是超過它的不足的。

陳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