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君遠
許君遠
許君遠(1902—1962),河北安國人;1928年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任《庸報》編輯,1936年擔任上海版《大公報》要聞編輯,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後擔任《文匯報》、《大公報》編輯。1941年香港淪陷后,轉赴重慶擔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后在重慶美國新聞處工作;1946年出任上海《大公報》編輯主任,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講授報刊編輯學。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調任《大公報》資料組組長。1953年調上海四聯出版社任編輯,1955年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病逝。

許君遠先生與夫人合影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后入英文系就讀,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與廢名、梁遇春、石民、張友松等同學。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藝界較為活躍,深得丁西林、陳西瀅、楊振聲、沈從文等人賞識,被一些史家稱為“京派代表人物”。後轉入報界,深得張琴南、陳博生、張季鸞、胡政之等賞識、提攜,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大公報》、《文匯報》、《中央日報》等擔任編輯主任、副總編輯等職,為《大公報》第二代高層領導之一,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國大學、上海新聞學校、暨南大學等擔任講師、教授。
1945年曾以《益世報》特派員身份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1946年至1953年,擔任上海《大公報》編輯主任、資料組長。1949年上海解放,許君遠被調到《大公報》資料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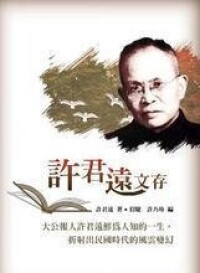
後人編輯的《許君遠文存》封面
1957年,在大鳴大放期間,許君遠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一個老報人的身份對當時的報紙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結果招來嚴厲的批判和粗暴的對待。許君遠和徐鑄成、陸詒被定為上海新聞系統三大右派。父親因此被發配到青浦縣飼養場勞動改造,並受到降職降薪處分,工資降八級,后改為降7級,才60元。一家數口,日子十分難過。
1958年,許君遠被調回原單位(上海文化出版社)當校對。1958年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除了精神壓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難奈,有時只能靠變賣所存書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他始終沒有放下筆。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了多篇散文、遊記。還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上發表了多篇《文心雕龍》等學術研究、考證方面的文章。可惜這些文章大多一時難以查到。
1959年,在黃素封先生邀請下,許君遠花了大半年時間修改和校對了黃素封先生翻譯的英國古典文學巨著《亞瑟王之死》。該書於1960年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後許君遠又翻譯了美國舞蹈家鄧肯的《鄧肯自傳》。很可惜這部三十多萬字的譯稿在文革初期被焚毀。
1962年,許君遠做了白內障剝離手術,結果手術失敗,術后引起半身及手腳癱瘓,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合併肺炎,不幸於1962年9月9日與世長辭,終年60歲。
許君遠著有小說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譯有《斯托沙里農莊》、《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後人輯為《許君遠文集》(許杏林、許乃玲編)、《許君遠譯文集》(許乃玲編)、《許君遠文存》。
許君遠是《大公報》人,曾是上海版編輯主任,一個在新聞史上留下過痕迹的人。他1928年畢業於北大,先後在北平《晨報》《益世報》《大公報》等報紙服務,1945年曾代表《益世報》見證了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他大半生事業的成就都在民國時代,可以說是典型的民國人。想到“民國神話說”,我想說,民國不是神話,也沒有被神化。那個時代的教育和媒體不是神話:《大公報》不是神話,《獨立評論》、《觀察》周刊不是神話,那些挺立在動蕩亂世中的報人更不是神話。他們認真地生活過、工作過,是那個時代具體的活的見證。許君遠就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葉公超等人的學生,他投身新聞界,尤其多年在《大公報》工作,在胡政之、張季鸞他們的身邊,親身體會過做報人的喜與憂。他沒有顯赫的名聲,作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國時代本土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
許君遠曾寫過一個北大系列,回憶北大的師長、同學,北大的生活,真實感人。那時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蔣夢麟在苦苦支撐,老師中有許多學術界的精英,但“老一輩的同學都在太息於拖小辮子的辜鴻銘輩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學術精神之逐漸消逝。”他說自己只趕上北大全盛時期的尾巴,“雖然是一個尾巴,北大卻始終維持著一貫的寬宏大量的校風,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個專門,你可以選擇你的導師,圖書館陳列著你所應當參考的書籍。在表面看來是雜亂無章,實際上很造就了許多專家學者。”他的興趣在文藝方面,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理解,雖未出洋留學,他實際上已窺見西方文化的真諦,他翻譯的文字也清新耐讀。
他進入《大公報》,在這家人才濟濟的報館,能脫穎而出,做到編輯主任,一度主持編輯事務,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與他的務實、認真、負責的態度有關,也與他下筆獨有個性有關。胡政之他們畢竟是識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張季鸞、胡政之的那些文章,充滿深情和敬意。他回憶自己的新聞生涯,認為《大公報》也有缺點,但它的優點卻比別的報紙多,造成了報業領軍的地位,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大公報》能培養人才,這是一個報紙成功的資本。他說,“一個全才的新聞記者,實在應該具備文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條件,頭腦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鋒利,交際手腕要靈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報》得到成長,很多方面,他都堅守著張季鸞留下的傳統,特別是不站在某個黨派、集團的立場上,而是保持報紙自身的獨立性。
1947年,國民黨製造了一個“北塔山事件”,全國報紙都登在要聞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報》竟然只當作普通消息來處理。第二天,國民黨特務包圍了編輯部,辱罵了半天,還在牆上寫下大字:“大公不公,正義不存”,總編輯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責他失職。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個報紙的編輯事務交給他。等王芸生們重返上海接管《大公報》時,又把“為國民黨服務的罪惡”加在他一個人的頭上,他只能去資料室。
在許君遠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養育出來的知識者是一種什麼狀態,他們的眼光、心態、氣度,他們對世界和社會人生的看法,處處都能令我們感受到民國的氣息。那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在沒有走上激進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們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許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裡,也能依稀感受到。血與火的廝殺、你死我活的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動蕩,都沒有改變他們,讓他們隨波逐流,變得浮躁不安。在亂世外象之下,掩蓋不住民國骨子裡的那種安靜,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他們身上有一種確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讀他的文字,我們處處能聞見一種平靜、冷靜而富有人味的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