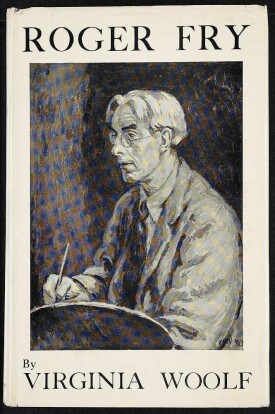羅傑·弗萊
羅傑·弗萊
羅傑·弗萊(1866-1934),英國形式主義批評家,西方現代主義美術的開山鼻祖。英國著名藝術史家和美學家,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批評家之一。早年從事博物館學,屬於歐洲頂級鑒藏圈子的鑒定大師,後來興趣轉向現代藝術,成為後印象派繪畫運動的命名者和主要詮釋者。他提出的形式主義美學觀構成現代美學史的主導思想。著有:《貝利尼》(1899)、《視覺與設計》(1920)、《變形》(1926)、《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1927)等。

弗萊《自畫像》
弗萊出生於倫敦一個富裕的教友派信徒家庭,父親愛德華·弗萊(Edward Fry)是一位法官。在去劍橋之前,弗萊就學於克利夫頓學院(Clifton College)。隨後他前往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成為劍橋秘密精英社團“劍橋使徒會”的一員。他起初學習自然科學,後來又去巴黎,再後來去義大利學習藝術,最後成為一名畫家。
1911年,弗萊與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墜入愛河,當時她正因為流產而處於艱難的康復期。弗萊給了她無微不致的關懷和照顧,而這些卻是她覺得無法從其先生、藝術批評家和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那裡得到的。弗萊與凡妮莎保持了終生的友情,儘管當1913年,凡妮莎愛上畫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並決定終生跟他一起生活時,弗萊早已心碎。
在經歷與妮娜·漢姆奈(Nina Hamnett)、喬賽特·科特梅萊克(Josette Coatmellec)等藝術家短暫的戀愛后,弗萊終於從海倫·阿恩雷普(Helen Maitland Anrep)那裡找到了幸福。她成了弗萊餘生最安全的感情港灣,儘管他倆一直沒有正式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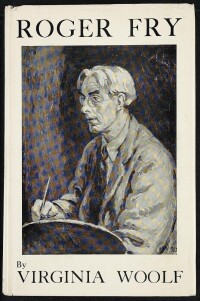
弗吉妮亞·伍爾夫《弗萊傳》英文版封面
弗萊的學術生涯是從義大利古典畫家的研究者與鑒定專家開始的。1899年,他發表了第一本專著《喬瓦尼·貝貝里尼》(Giovanni Bellini)。一直以來,弗萊都定期為《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及《雅典雅神殿》(The Athenaeum)供稿。1903年,他介入了《伯靈頓雜誌》(Burlington Magazine)的創建工作,並於1909-1918年間成為該雜誌的編輯,使它成為全英最重要的藝術史期刊之一。
與此同時,弗萊開始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史萊德美術學院講授藝術史。1906年,他被任命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in New York)繪畫部主任。也是在同一年,弗萊發現了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的繪畫,開始將其學術興趣從義大利古典繪畫轉向法國現代藝術。
1910與1912年,弗萊先後兩次在倫敦格拉夫頓美術館舉辦了“後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t)畫展,使得封閉的英倫三島藝術界跟上了歐洲現代藝術的步伐。但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公眾、媒體與批評家的猛烈攻擊。他們認為法國現代藝術是垃圾,稱弗萊是“騙子”和“詐騙犯”。弗萊不得不寫作一系列論文,舉辦講座,來為後印象派畫家辯護。這些辯護如今已成為美術史與批評史上最傑出的現代藝術辯護文獻。弗萊以獨立批評家身份,以獨立美學理念組織、舉辦畫展,也在現代藝術策展制度與批評制度方面,發揮了開創性作用。(參拙作《現代藝術批評的黃金時代:從羅傑·弗萊到格林伯格》,載《藝術時代》,2009年第8期;關於兩屆後印象派畫展,以及弗萊為之辯護的一般史實,詳見拙著《20世紀藝術批評》第一章“羅傑·弗萊與形式主義批評”,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0頁。)
1913年,弗萊創建了“奧米加”工場(Omega Workshops)。這是一家設計公司兼公司化經營的藝術創作工作室。成員包括凡妮莎·貝爾、鄧肯·格蘭特等等。
1920年,弗萊重新編輯並出版了由他最著名的藝評文章構成的《視覺與設計》(Vision and Design),取得了空前成功。這進一步強化了他在英國批評界的領袖地位。該書迄今仍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最傑出的貢獻之一。
在這本書里,弗萊強調了“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也就是說,一件藝術作品的視覺特徵,其重要性要超過它的主題內容。他認為,藝術家應該運用色彩與形式的安排,而不是主題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而這樣的作品不應該從它們是否精確地再現了現實的角度來加以評判。
1926年,弗萊應法國《愛藝》(l’Amour de l’art)雜誌之約,為大收藏家佩萊倫(Pellerin)所收藏的塞尚作品集撰寫評論,並於翌年出版英文版,這就是他的生平力作《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Ce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此書是羅傑·弗萊對塞尚藝術的經典研究,它清晰、敏銳,具有高度的原創性,現在已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典範之作。弗萊本人就是一位畫家,他拒絕當時流行的批評模式,提出形式而非內容才是藝術最基本的表達元素。塞尚的作品最切合弗萊的理想——對自然的一切方面賦予形式的表達。在此書中,弗萊既努力探究塞尚藝術風格的發展進程,同時也精密細緻地推敲個別作品的內在構造機制。其結果是一部文采斐然、生動活潑的書,對畫家和學習繪畫的學生而言它擁有技法方面的價值,它還為普通讀者提供了一種充滿真知灼見的洞察,展示了塞尚藝術不可思議的魅力。弗萊的生前至友弗吉妮亞·伍爾芙認為此書是弗萊最偉大的作品。
1933年,弗萊被任命為嚮往已久的劍橋大學史萊德講席教授,並在劍橋開始了系列藝術史講座,但講座還沒有結束,他就悲劇性地撒手人寰。其後,講稿在弗萊的後繼者、英國著名藝術史家肯尼思·克拉克爵士的整理下,以《最後的演講錄》(Last Lectures)為題,於1939年出版。
羅傑·弗萊是國際公認的形式主義批評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而形式主義則是現代主義藝術觀的基礎之一。弗萊本人的理論來源大略有三個:一個是德奧藝術史中的形式分析法,主要來自沃爾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另一個是義大利藝術史中的藝術鑒定法,主要來自莫雷利(Morelli);再一個是東方的美學資源,來自弗萊的朋友、著名漢學家勞倫斯·賓雍(Lawrence Binyon)。從沃爾夫林那裡,弗萊學會了以嚴格的視覺形式術語來分析藝術作品的風格結構、風格遞嬗與演化的規律;從莫雷利那裡,弗萊學會了近乎外科醫生般的嚴苛的鑒定技術,特別善於從一般觀眾所忽略、通常也是畫家無意識的流露處,捕捉畫面的技術信息和形式特徵;從賓雍那裡,弗萊學會了東方藝術家(尤其是中國藝術家)對繪畫的物質質地、材料性能、筆觸與書法價值的體認。
將這些不同的學理資源綜合起來,弗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形式主義-現代主義批評理論體系。然而,弗萊的思想體系,並不是鐵板一塊、毫無演化的,而是可以明顯地讓人感覺到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始於1906直到《藝術與設計》出版),弗萊重在為以後印象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辯護。而後一個階段(大約始於《變形》出版直至晚年),則當形式主義(特別是純粹抽象藝術)已成為其時的主流時,他努力修葺其理論基礎,從而竭力把自己的理論從教條化與學院化的趨勢中拯救出來。
前一階段的主體思想,特別集中地體現在弗萊為兩屆後印象派畫展所作的辯護,以及《藝術與設計》中。我們不妨最簡單地予以概括如下:
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表達人性中最為深沉、最為普遍的情感,因此它在人的感官(視覺)的基礎上必定還會訴諸人的知性(或理解力),從而趨向於某種程度的設計或賦形。但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卻以人類心智中更為重要的側面的表達為代價,不斷追求精確化的再現科學,這種再現科學的最晚近的形態就是印象派。以塞尚為代表的後印象派堅持個人表達的重要性,從而開創了現代藝術的賦形語言:以一定程度的變形或者甚至抽象取代照相式的寫實主義,以純粹色彩與線條的造型,取代了光影與明暗法。(參見沈語冰:《形式主義者如何介入生活:弗萊與他的時代》,載《新美術》雜誌,2009年第6期)
但是,在弗萊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他越來越強烈地質疑作為現代主義基礎的形式主義原理,或者不妨說,他事實上已經走到了與那種被簡化了形式主義理論相對立的程度。甚至在戰前,弗萊的現代主義也以其對“古典性”的強調,從未放棄過藝術史的傳統遺產。弗萊本人放棄了——或者至少是修正了——一度在他看是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形式主義原理,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出版於1926年的文集《變形》(Transformations)的導論中。在界定“再現在造型藝術中的意義與目的”時,弗萊說:“這始終是這樣一種令人困惑的性質的癥結所在,對此,我並不羞於承認,在不同的時候,我提出過不同的解決方案。我肯定不同於彼時的立場——那時我堅持純粹造型方面的絕對重要性,而且幾乎是暗示,沒有別的東西需要考慮進來,而這時,我強調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繪畫的戲劇性可能的東西。”(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p.13.)
放棄了這種嚴格的形式主義后,弗萊坦承自己準備“調和,或至少是解釋,這兩個表面上看起來矛盾的態度”。於是,這就成了弗萊晚期寫作的計劃:通過將再現與形式主義範式綜合起來而又不放棄純粹審美經驗的理想,從而將現代主義重新整合進更廣闊的藝術史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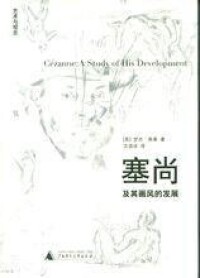
弗萊《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中文版封面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稍稍提一下弗萊傳記中的幾個事實:作為出身在七代教友派信徒(Quakers)之家的兒子,弗萊違背父願,選擇了藝術作為終生職業;作為歐洲最傑出的美術鑒定家,他卻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之間面臨兩難選擇,結果卻一無所獲;作為英國當時最著名的藝術批評家,他舉辦了兩屆後印象畫派展,卻成為名流和公眾責難的火山中心;作為劍橋最年輕有為的學者之一,他卻遲遲得不到期待已久的史萊德講席教授的職位(Slade Professorship),直到他生命晚年才如願以償。(關於弗萊的生平,參Virginia Woolf,Roger Fry: A Biography, London: Hogarth Press,[1940]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ces Spalding, London, 1991;以及Frances Spalding,Roger Fry: Art and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從1906年初識塞尚的繪畫,到1926年撰寫《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一書,整整20年過去了。因此弗萊的這一塞尚專論,成了他等待了大半輩子的機會。一位科學家的劍橋學習生涯,一位畫家的技法訓練,一位鑒定家的敏銳眼光,一位美術史家的知識積累,一位藝術批評家的洞察力,最後,一位塞尚藝術的狂熱愛好者和學習者,一切的一切,都風雲際會,水到渠成(關於弗萊生平及其批評理論的簡要介紹,詳見拙作《羅傑·弗萊的批評理論》,載《美術研究》2008年第4期,並作為附錄,收入中文版《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乃是弗萊一生事業的最高峰,是他留給世人的一份總結,一份遺囑。儘管此後他還有著作出版,但它們無論在達到的高度,還是對後世的影響力,均無法跟眼前這本書相比。雖說《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只是一本小冊子(譯成中文不足六萬字),它卻為塞尚研究樹立起了一座難於逾越的豐碑。從風格上看,我們也可以識別它與塞尚繪畫的同質性,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結晶體,各個層面都晶瑩剔透,熠熠發光。論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之:或從他對塞尚繪畫的風格分期研究著手,或從他對塞尚繪畫的介質(油畫/水彩)探索入門;或以其對塞尚藝術世界的宏觀結構(拜占廷對抗巴洛克、古典壓抑浪漫)的剖分登堂,或以其對塞尚個別作品具體而微的分析入室;或從他最富特質的形式分析法擇路,以趨近其主要批評手法,或取道他對塞尚生平、性情氣質及其心理的分析,以探求其超形式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所有這些角度無疑都是可能的,事實上,這些可能性恰恰構成了弗萊之後塞尚研究的主要趨勢(詳見拙作《弗萊之後的塞尚研究管窺》,載《世界美術》2008年第3期;並作為附錄收入中文版《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

塞尚《高腳果盤》
然而,弗萊並不滿足於僅僅為西方形式主義藝術史和藝術批評奠基,他還在1918至1934年的文章中,從他原有的批評理論中剔除了大量東西;而這個批評理論卻是他戰前經歷千辛萬苦才得以創立的。但是我們不得不認為,弗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全部事業的終極效果,遠不是變化多端、零碎任意的,相反,某些因素貫穿於他的批評生涯的始終。
即使是在敵意的包圍中為現代主義辯護時期,弗萊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後印象派繪畫,特別是塞尚的“古典性”的強調。在他進一步深化其批評理論時,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了他深深地介入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程度。而在後期對原有理論進行調整與修繕時,他的早期思想不是被推倒了重來,而是明細化、精確化了:該捨棄的被捨棄,該突出的更加突出了。事實上,新一代的讀者在弗萊的疑惑、他的社會目的感,或是在他蔑視一切權威的性格中,能夠發現一個更加令人同情的人物的誕生,而不是一個被臉譜化了的“形式主義之父”的形象。
目前,筆者正在整理、選編並翻譯《弗萊藝術批評文選》(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即將出版)。文選既囊括了弗萊早期為兩屆後印象派畫展所作的著名的辯護文章,也包括他晚年的重要論文(例如《線條之為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段》、《繪畫的雙重性質》、《倫勃朗:一個解釋》等等)。我希望,隨個這個文選的出版,我們一方面能提高對弗萊寫作的多樣性及其範圍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能認清在所謂的後現代語境中,現代主義的複數性質,以及從它的誕生到被宣布下課的階段中的種種衍變與發展。
特別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對弗萊晚年思想的重新梳理,絲毫也沒有削弱我們對這位偉大的現代主義理論的奠基者的尊敬,相反,在意識到他是怎樣一個偶像毀壞者的同時,他還是怎樣一個真誠的求知者和愛美者,我們反而會油然而生敬仰。畢竟,對他來說,捍衛對真美的追求,要比冒著被學院化和教條化的風險,去提供一個封閉而又貌似圓滿的體系,重要得多。說到底,弗萊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倚重現場感覺的批評家,一個相信自己直覺與經驗的畫家,同時也是一個蔑視一切外部權威,信任自己的理性與內心律令的學者。即使在其60歲以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當他站在羅浮宮內,他也能夠“忘掉我的所有理論,我寫過以及想過的所有東西,並試著絕對遵從自己的印象”。(Quoted in Jacqelin V. Falkenheim,Roger F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Formalist Art Criticism, Ann Arber, Michigan: UMI Reserch Press, 1980, p.127)與時同時,發自內心的強大信念與理智力量,最終使他成為一位改變了20世紀思想進程與審美趣味的偉大的知識分子,足以與同時代的劍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Keynes)相提並論。
1.Roger Fry,Vision and Desig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視覺與設計》,易英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Roger Fry,Transforma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6.
3.Roger Fry,Cé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7;《塞尚及畫畫風的發展》,沈語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4.Roger Fry,Last Lectures, introduced by Kenneth Clark,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39
5.Christopher Reed,A Roger Fry Rea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6.羅傑·弗萊:《弗萊藝術批評文選》,沈語冰編選並翻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
7.Clive Bell,Art,London: Chatto & Windus, 1914; J. B. Bullen, ed., Oxford, 1987.
8.Clive Bell,Old Friends: Personal Recollect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6.
9.Clive Bell,Since Cezanne,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22
10. Jacqueline V. Falkenheim,Roger F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Formalist Art Criticism,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0.
11. Solomon R. Fishman,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 Essays on the Art Criticism of John Ruskin, Walter Pater, Clive Bell, Roger Fry and Herbert Read,1963
12. Christopher Green, ed.Art Made Modern: Roger Fry’s Vision of Art, London, The Courtauld Gallery,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1999.
13. Donald A. Laing,Roger Fr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Published Writing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
14. Frances Spalding,Roger Fry, art and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5. Virginia Woolf,Roger Fry: a biography, Lodnon: Horgath Press, 1940.
(本文原載於《榮寶齋(當代藝術版)》,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