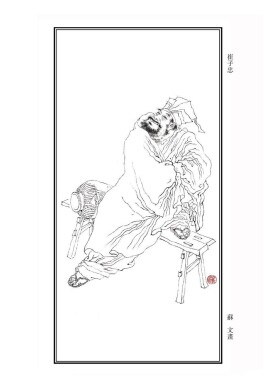崔子忠
明代畫家
崔子忠,1644年逝世,明畫家,初名丹,字開予:改名子忠,字道母,號北海,青蚓(一作青引),生員,曾游董其昌之門,李自成克北京后,絕食死。
崔子忠,明畫家,初名丹,字開予:改名子忠,字道母,號北海,青蚓(一作青引),梁清標《畫譜序》亦作“道毋”,約生於1574年,卒於1644年。原籍北海(山東省萊陽市)人,后移居順天(即北京)。其好友梁清標在其所輯刻崔子忠所繪《息影軒畫譜》序中稱崔子忠:“天啟時為(順天)府庠生,當生於萬曆年間。”又說他“甲申之變,走入土室而死”。
崔子忠可以說是一位愛國畫家,居住於順天府(今北京),曾經師從董其昌。在農民起義軍李自成的隊伍攻入北京后,躲在自己的密室當中,後面因缺少糧食而餓死。善畫人物,仕女,題材多佛畫及傳說故事,取法唐宋,頗具古意。他在當時與陳洪綬齊名,有“南陳北崔”之稱。
周亮工記他“年五十病,幾廢之。后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當生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前後,根據《書畫記》和《神州國光集》等史料著錄,崔子忠的繪畫作品涉及面很廣,在人物、山水、花鳥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長,與陳洪綬並稱為“南陳北崔”。他作畫用紙或絹素,沒有定數,或為捲軸,為中幅冊頁,為扇面,似乎很隨便。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稱:“萊陽崔子忠,號青蚓,人物稱絕技。人慾得其畫者,強之不肯。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后竟以餓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筆意超邁,神氣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製小贊,字與畫皆儒筆墨。”(見《美術叢書》第一集第七輯)。周亮工《書影擇錄》稱:“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為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逾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見《美術叢書》初集第四輯二三七頁)崔子忠的書畫,孔尚任推為“儒者筆墨”,而亮工以貶低丁南羽、吳文中、鄭千里等人物畫家,來提高陳、崔兩家的繪畫地位,雖有可值得商榷之處,但在明清以來以仿古為能畫,筆筆講出處,處處要師承,非某宗某派則為野狐禪,畫壇了無生氣,特別是山水畫。自明董其昌畫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畫,至清代的四王、吳惲等,把山水畫拔高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畫是不被重視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重陳老蓮、崔子忠,並把他倆並稱為“南陳北崔”,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畫史上都說崔子忠“善畫人物,規模顧、陸、閻、吳名跡,唐以下不復措手。白描設色能自出新意,與陳洪綬齊名,號南陳北崔”。這種評論是近乎實際的,他繪的《桐蔭論道說法圖》(亦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一看題記,有可能誤認為是陳洪綬畫的。其好友梁清標在其死後為其輯刻的《息影軒畫譜》,其人物造型、表現方法與陳洪綬的《水滸葉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陳北崔”之說。他們兩人在畫風上相似,卻不能相互代替,他們都以人物畫為主要特長,社會聲望也不分軒輊,但卻各有特色。陳洪綬的作品才氣橫溢,寓美於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卻樸實無華,寓意於內蘊。按梁清標的說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門卻掃”瀏覽史籍,每遇有忠考奇節人物,義使巾幗英雄,繪圖像,立傳贊,雖稱自娛,也可以起“頑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稱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畫極為注重立意,因此為當時的文人和畫家們所推崇。崔子忠善於表達歷史題材,尤其喜歡畫文人們的風流韻事,他的《雲中玉女圖》、《蘇軾留帶圖》、《桐蔭博古圖》、《臨池圖》以及羅漢道釋等圖,都是人物畫,也都具有來歷,題材不見得新鮮,但由於他構思畫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進自己的東西而成為新作,也是耐看的。《藏雲圖》即是此類典範,此圖以人物為主,襯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寫為刻畫人物服務。由畫中題識可知此畫是為玄胤同宗所作,畫中一團雲氣繚繞,是表現巫山濃雲虛幻之處,“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見前後。史稱李青蓮安平入地,負瓶瓿,而貯濃雲,歸來散之以內,日飲清泉卧白雲,即此事也。”畫面中唐代大詩人李白盤腿端坐四輪橢圓底盤車上,緩緩行於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視頭頂上的雲氣,神態閑適瀟灑;一稚童肩搭繩索,牽引車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導狀。在具體表現上,其衣紋作顫筆細描,虯折多變,折而不滯,顫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質料的柔軟質感和隨風飄的動勢,氣意超邁,神色如生,可謂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遺餘力地頌揚歷史上的隱逸君子,是其人生觀的曲折表現,同時亦是明末文人們走投無路,徘徊苦悶的心理狀態的真實反映。其本人雖居於“京師”,身居鬧市卻過著清苦無為的生活,很有隱者之風,由於他缺乏陶淵明的生活條件,又不肯寄人籬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餓死。不識時宜,懷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時,亦死得冤枉。
“孤傲絕俗”的評價,確實當之無愧,但以生命的結束為代價,其犧牲不可謂不大矣。歷史上有伯夷、叔齊因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崔子忠則因懷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寧肯餓死,也不願把畫賣給不識貨的庸人,寧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願意接受無禮者的援助,最終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採薇圖》。
《藏雲圖》、《杏園夜宴圖》、《雲中玉女圖》等。

崔子忠

崔子忠

崔子忠
崔子忠(約1595年——1644年),又名丹,字道母,號青蚓。原籍山東平度,占籍順天(北京)。(1)是中國繪畫史上大師級的名人。明朝末年,和南方的陳洪綬(陳老蓮)齊名,並稱“南陳北崔”。
現存有關崔子忠的資料,成書最早內容最多的是清初順治年間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周氏自稱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錢虞山曰”。按:王崇簡(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順天府學生員,崇禎初年都參加過江南文士組織“復社”的活動(見吳山纂輯的《復社姓氏傳略》卷一北直順天府)。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入清后,仕至禮部尚書,卒謚“文簡”。錢謙益(虞山),江南常熟人,明末東林黨領袖人物,詩文大家。崇禎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與崔子忠相識,崔以師禮事之。《書影》所引“錢虞山曰”文出錢著《列朝詩集小傳·崔秀才子忠》。周亮工,河南祥符(開封)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濰縣知縣。入清后,仕至戶部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書畫收藏家、鑒賞家。
據《書影》所記“王敬哉曰”,崔子忠,“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占籍順天(北京)。年青時考中秀才,因“為文崛奧”,不合科舉八股的要求,參加了幾次鄉試都未考中,便“棄舉子業”。
崔子忠中年時即蜚聲畫壇,住在北京南郊偏僻處一所簡陋的小院里, “蓽門土壁,灑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蒔花養魚,不知貧賤之可戚”。“妻布衣疏裳,黽勉操作”,兩個女兒“亦解誦讀”。每當興至,則欣然展紙揮毫,妻女“皆能點染設色”,一家四人“相與摩挲指示,共相娛悅”。有時也把得意之作贈給少數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錢虞山曰”也有相同內容)。崔子忠為人孤高,自甘清貧,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塵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當時貴人多折官位與之交,崔皆逃避不顧”。
明末文壇領袖書畫大師董其昌評崔子忠:“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見”。錢謙益則稱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錢評崔子忠的畫是:“慕顧、陸、閻、吳遺跡,關、范以下不復措手”。說他所追求和師法的是晉代顧愷之、陸探微、唐代閻立本、吳道子、五代關仝、北宋范寬這些前代的超級大師,而絕不與流俗之輩看齊。周亮工在《書影》另一則文字里稱:“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遠追(吳)道子,近逾丁、吳。”(見)當時的丁南羽、吳文中所畫佛像已經達到了“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的極高水平,崔子忠更超過他們,可以上追“畫聖”吳道子了。錢謙益文所記崔子忠軼事很生動:崔子忠少年時代的同窗好友宋應亨和宋玫都在崇禎年間考中進士。宋應亨任職吏部文選司時,曾授意一個“應選者”送給崔子忠一千兩銀子。崔子忠拒絕接受,並對宋應亨說:“你知道我窮,卻不拿自己的錢財贈送我,而要我接受‘應選者’的銀子。難道你不了解老同學的脾氣嗎?”宋玫任諫官,屢次向崔子忠求畫崔都不給。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請到府中,關上大門,對他說:“今天別怪老同學無理,如果不給我作畫,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裡養的魚、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無奈,只得畫了一幅。“畫成,別去,坐鄰家,使童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略簡,須增潤數筆’”。宋玫把畫交給來人帶回,崔子忠當即撕碎,揚長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卻又奈何不了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學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和孫承澤的《畿輔人物誌》,都有《崔文學子忠》傳,除了略述《書影》文中所記,還都記了“史可法贈馬”事。史可法和王崇簡、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學御史時拔識的順天生員。到崇禎後期,史可法已負天下重望。“一日過其舍,見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史可法是非常了解並敬重這位老同學的。崔子忠則把馬賣了四十兩銀子,“呼朋舊痛飲,一日而盡”。說“這酒是史道鄰所贈,清清白白,不是來自‘盜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類此。
由明入清的高承埏(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十五年曾任寶坻知縣)著《崇禎忠節錄》,《順天府學廩生崔子忠》條,稱“先世山東平度州人,其祖來講師,後人因家焉”。“通五經,督學御史左忠毅公光斗拔食餼。尚氣節,有文名,兼能詩,而畫奇絕。與諸暨陳洪綬章侯齊名,有‘南陳北崔’之稱”。
明末清初大史學家談遷的《北游錄》,記文壇泰斗吳梅村入清以後得到了一幅崔子忠畫的《洗象圖》,面對這幅表現宮廷里春日洗浴大象盛況的長卷,吳氏深為所畫場面的恢宏和人物的傳神而驚嘆不已,便在畫卷上題了一首長詩。“崔生布衣懷紙筆,仰見天街馴象來”,崔子忠是在冒著充犯“金吾卒”之險,親自觀看了“赤腳烏蠻縛雙帶,六街仕女車填咽”的實況,“歸來沉吟思十日”,苦心揣摩構思之後,才創作出這幅“生平得意《洗象圖》”的。當時,“圖成懸在長安市,道旁觀者呼奇絕”。可惜崔生為人孤潔,吳梅村無限惋惜地說:“嗟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草埋殘骨。一生心力付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