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居國
烏孫小昆彌的庇護地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跟當時的大月氏屬於同種,在漢朝初年國勢頗盛,擁有現在新疆北境以及中亞部分地區。到了晉朝之時,他們對於中國仍然十分歸順,曾經遣使入朝。唐代,這個國家仍然繼續存在,被稱為康國。
來自康居的胡旋女
長安宮廷歌舞之盛多半與玄宗的喜好有關,君有好,下必有所獻。其中就有來自西域康居國的一種舞蹈,叫作“胡旋舞”。
長安當時是亞洲的中心。中亞一帶基本都在大唐的統治下。中亞一帶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國也不例外,在長安樂師中,就有善彈琵琶的康崑崙來自康居。據白居易記載:“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新唐書·西域傳》也記載:“康國者,一曰薩末健……國人嗜酒好歌舞……開元初,貢……駝鳥及越南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國的歌舞早在開元之初就已經陸續進入長安。琵琶樂師康崑崙也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入大唐皇家樂隊的。
康居國跳“胡旋舞”的女孩們來到長安后,帶來了獨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並不喜歡這樣一種旋轉激烈的舞蹈,但是,楊玉環卻立刻喜歡上了胡旋舞。
《唐書·樂志》曰:“康居國樂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府雜錄》曰:“胡旋舞居一小圓球子上舞,縱橫騰擲,兩足終不離球上,其妙如此。”從上述記載與描述可知,只要看過維吾爾等新疆地區少數民族舞蹈的,幾乎就可以想象出這種旋轉舞蹈的形態來。少數民族的舞蹈很講究舞者之間的交流,表達的是一種個人的情感,與皇家根據禮儀所需編排的程式化的樂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對這種舞蹈感到不自在,顯然是與在這種舞蹈中舞者過於專註於自我表現,卻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關。
白居易的《胡旋女》詩中寫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兩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康居國來的胡旋舞女們在玄宗面前賣力地舞畢,原想得到玄宗的讚賞。結果,玄宗的表現卻是:
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爭能爾不如。
玄宗有這種態度,胡旋舞女想進入大唐皇家梨園顯然是不可能了。但長安畢竟是當時的國際大都市,混口飯吃並不困難。康居國胡旋女在長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間風行胡旋舞,就連內宮妃子宮女中間也流行胡旋舞,特別是貴妃楊玉環尤其痴迷,天天在長生殿上練習胡旋舞。後來,不但宮裡,就連官場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長安城里最受歡迎的交誼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鬧出了亂子。楊玉環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個會跳此舞的人,正是楊玉環的乾兒子安祿山。安祿山會跳胡旋舞,這正是他取悅唐玄宗和楊玉環的原因之一。安祿山造反,跟胡旋舞沒有直接聯繫,但唐人恨安祿山,連帶著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說: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令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在白居易看來,安史之亂的原因就在那一隊無辜的胡旋女身上,這確實是太過荒唐了。無獨有偶,元稹(zhěn)與白居易是一樣的看法:
關於康居國的詩詞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
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
驪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潛鯨暗噏笡波海,迴風亂舞當空霰。
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觀者相為言,承奉君恩在圓變。
是非好惡隨君口,南北東西逐君眄。柔軟依身著佩帶,徘徊繞指同環釧。
佞臣聞此心計回,熒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為鉤,君言好直舒為箭。
巧隨清影觸處行,妙學春鶯百般囀。傾天側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見。
翠華南幸萬里橋,玄宗始悟坤維轉。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其譴。
解釋
在元稹看來,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祿山趁機佔據了長安。而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胡旋舞教會眾人逢迎拍馬,以圓變之術侍奉君王,欺騙君王。元稹告誡人們,有國有家的人都應該遠離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楊玉環愛跳胡旋舞是史書記載了的,玄宗是否真的不喜歡就難說了。玄宗不喜歡胡旋舞的說法,恐怕也是後人刻意為玄宗掩飾的一種說法。大唐皇室本來就有胡人的血統,對於少數民族的舞蹈,向來是持開放心態的。況且玄宗之於歌舞的喜愛,沒有理由說他會不喜歡。如果在胡旋女舞隊的表演舞會上,玄宗沒有表示出欣賞,那也可能只是假臉色給康居國的使臣看,以顯示大唐天子的從容與見多識廣。
元白詩中自然有他們的良苦用心,無非借胡旋之舞進勸誡之言,勸誡皇帝不要被“旋目與旋心”。只是如此一來,不免委屈了康居國的胡旋女。
今天,康居國留下來的胡旋舞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跳,又有哪個國家因為胡旋舞而滅亡了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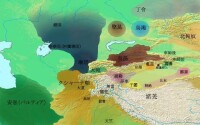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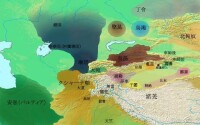
康居國
東漢時期,康居國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領地很大。據《後漢書》記載,康居國西南都城與安息國相鄰,東南與貴霜王朝的大月氏國相鄰,北部奄蔡國、嚴國均已臣屬康居,中部為康居國本土,形成中亞地區月氏、康居、安息三個大國鼎立的局面。
東漢時的西域,因東漢與西域三絕三通,西漢末的五十餘國到東漢初,經過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車、於闐、鄯善三國並立的局面,其中莎車勢力最大,中亞大宛國已經臣屬於莎車。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車又被於闐國攻滅。自西漢末王莽統治時,西域各國因對邊疆政策不滿,匈奴乘虛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龜茲國漸漸崛起,勢力擴展到疏勒。
早在公元前7~前54(漢宣帝五鳳年間),匈奴內亂,五單於並立爭奪霸主。亂世中,郅支單於向西擴展,後來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與烏孫國相鄰的地方,聯手對付烏孫,搞得烏孫西部千里空無人煙,顯然此時康居的勢力範圍逐漸擴大。《漢書·陳湯列傳》稱:“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於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
郅支單於西遷康居時期,已經有相當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單於的擴張也給康居提供了機遇。
郅支單於被漢朝剿滅后,康居在中亞的勢力範圍並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勢力大增。漢成帝年間,康居國成了烏孫小昆彌的庇護地。當時,小昆彌子拊的弟弟日貳殺兄篡位后,因恐漢朝討伐而逃往康居避難。公元前11年(元延二年),烏孫小昆彌末振將曾率八萬餘眾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兩昆彌。
到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被東漢擊潰,而且鮮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遷康居,與郅支單於的殘部會合。在北匈奴西遷浪潮的衝擊下,康居被迫南遷到索格狄亞那地區,故而以後的漢文史料中往往將康居、粟特並稱,並說康國為“康居之後”。北匈奴大規模西遷烏孫、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紀中期。在康居南遷時,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隨著而來。這個時期,康居國北部的領土大為縮小,錫爾河以北地區被西遷的匈奴人佔據。
班超平定西域各國叛亂期間,康居國對班超和東漢政權有過幫助,也有過阻撓。那時,班超率疏勒、於闐、紆彌等國兵一萬餘人攻破龜茲國姑墨石城。此時的康居、月氏、烏孫等國都有歸附漢朝的願望,想幫助班超并力攻滅龜茲,打通與漢朝往來的通道。後來,莎車王勾結疏勒王反叛漢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導致班超久攻不下。這個時期的康居和貴霜剛剛和親結盟,班超派使者給月氏王送去厚禮,通過月氏王向康居王勸諭,康居退兵,並將疏勒王押到月氏,轉送漢朝。三年後,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來,佔據一些地方,並與龜茲國密謀詐降,被班超識破詭計,遂將疏勒王處斬。此後,康居與漢朝之間相安無事。
東漢時期,康居國的強大時間並不太長,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後。康居國的強大比起同時期的貴霜帝國來要略遜一籌。
公元三世紀時,貴霜帝國開始衰落,淪為波斯薩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貴霜帝國在印度的領土也逐漸縮小。
公元265~274年(晉武帝泰始年間),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晉朝獻馬,希望與新崛起的西晉王朝結交。
公元三世紀后,康居國已沒有清晰的國界,史書中對康居自三國時就已稱其為“粟弋”,專指當地居民的種類和地名了。
南北朝時期,嚈噠勢力崛起,康居相對衰弱。嚈噠人西遷后,康居國就不復存在了。

公元3世紀的西域
公元357~367年間,由於柔然的崛起並爭奪西域,嚈噠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湧入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區,攻滅粟特、政府索格狄亞那就顯得輕而易舉。到公元四世紀20年代,嚈噠匈奴人又南攻滅貴霜,從而成為中亞的強國,居於中國和波斯薩珊之間,這時的康居、安息、烏孫、花剌子模、罽賓、大宛等等漢代國家名稱全都不見了。原來居住在中亞地區的匈奴人、康居人、烏孫人、月氏人逐漸融合同化。隨著突厥人的湧入和突厥語的廣泛流行,中亞各族都以作為各個因子被突厥這個龐雜部族所涵蓋。中亞各國的昭武族人在臣屬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權和民族根源,形成了“昭武九姓”諸國。
康居國近五百年的歷史上,由於古漢字記載西域康居國的史料非常少,同時對西域粟特文史料研究的缺乏,我們甚至不知道康居國的君王叫什麼名字?他們曾經割下古波斯王居魯士頭顱、令波斯王大流士遠征慘敗、令亞歷山大大帝被迫穿上中亞服飾採用懷柔政策的中亞尙武民族。曾經壟斷古絲綢之路中間商貿易的善賈民族!這個中亞文明古國,為東西方文明的交融和促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給當今社會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並獻善馬。
《漢書·西域傳》載:“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關於卑闐城的位置,新近出版的《西域地名考錄》認為,其具體地望應在澤拉夫尚河,即那密水南岸,可實際上它應該在更北的地方。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張芝聯等主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都將之標在錫爾河北岸,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亦認為卑闐城應在此範圍。這是現今所能接受的觀點。下面還要結合對五小王都城的考證進行討論。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這是就漢里而言。根據漢代尺度,每漢里415.8米。“萬二千三百里”等於5114千米,這是從長安到卑闐城的里距。我們從長安出發,沿312國道西進新疆,然後沿314國道到喀什,其里程是3835千米。再從喀什到吐爾尕特口岸165千米,總計4000千米。境外,從吐爾尕特口岸進入吉爾吉斯斯坦,經費爾干納盆地北轉,到錫爾河北岸的廣闊草原,當還有1000多千米的路程,全程與《漢書·西域傳》所記從長安到卑闐城的距離基本是吻合的。當然,古今道里不同,即使是同一個地方,路程的坎坷迂曲也不可同日而語,和現今的道路長短不可能完全相符。
康居是中亞大國,其地域和人口在西域諸國中舉足輕重。《漢書·西域傳》所記戶口勝兵,最少的三個國家:單桓,戶27,口194,勝兵45;烏貪訾離,戶41,口231,勝兵57人;車師都尉國,戶40,口333,勝兵84人。而最多的三個國家:烏孫,戶120000,口630000,勝兵188800人;康居,戶120000,口600000,勝兵120000人;大月氏,戶100000,口400000,勝兵100000人。可見,除烏孫外,康居是西域的第二號大國。而且同烏孫不相上下。還可看出,大國與小國之間,天壤之別,幾乎不可相提並論。《史記·張騫列傳》所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人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這是張騫在西域時看到的公元前2世紀的康居。有人以此為根據,認為康居開始極其弱小,後來才壯大起來。顯然,和月氏、匈奴相比,康居當時可能處在弱勢,所以才“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但“控弦者八九萬人”,仍不失為西域大國。按前面的記載,康居戶出1兵,而每戶平均5口。如此,“控弦者八九萬人”,其總人口至少在40萬到45萬之間,這在當時的西域,仍為位居一、二的大國。
《漢書·西域傳》載:“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這段記載里,分別以都護治地和陽關為坐標,給出兩個里程數據,以確定五小王都城分別與上述兩地的遠近。但五小王治地究竟何在,歷來語焉不詳。只有《新唐書·西域傳》有一些記載,可以輾轉考得其位置。
華嚴宗是唐初繼法相宗之後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華嚴經》為宗經,主要發揮“法界緣起”的意旨。
華嚴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北方的地論學者和南方的三論學者,華嚴宗人自稱的學統傳承關係則以隋唐之際的法順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儼為二祖,法藏為三祖。其實,法順和智儼只是華嚴宗的先驅者,法順基本上是一位禪僧,曾勸人讀《華嚴經》,相傳作有《華嚴五教止觀》,在其止觀法門中把《華嚴》擺在最高的圓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儼著述較多,大力闡述《華嚴》思想,並提出了“十玄門”這一華嚴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華嚴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闡明的;華嚴宗的判教學說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國各地建立華嚴寺院,並普遍締結宗奉《華嚴》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動促成的。所以,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國相,祖父遷來長安定居,從此入籍中國長安。所以說,法藏原本是康居人。
法藏生於公元643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17歲時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陝西郿縣南)修行,學習佛經,回京后從雲華寺華嚴大師智儼聽講《華嚴經》,前後9年。深受智儼賞識。公元668年(總章元年)智儼臨終時,曾囑門徒提攜法藏,認為他專心鑽研《華嚴經》,是紹隆遺法的希望所在。兩年後,武則天的生母楊氏去世,武則天將母親的府邸改為太原寺,下詔剃度僧人。經過道成、薄塵推薦,法藏獲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時,法藏只受了沙彌戒,在公元674年(上元元年)奉詔在太原寺講《華嚴經》。後來,又在雲華寺開講。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法藏授具足戒,並把《華嚴經》中賢首菩薩的名字賜給他作稱號,稱為賢首國師。自此以後,法藏經常參加翻譯、廣事講說和著述,大振華嚴的宗風。
公元680年(高宗永隆元年),中印度沙門地婆訶羅來到長安,法藏往問西方的古德有沒有關於佛一代教法的判釋。據地婆訶羅說:印度那爛陀寺同時有兩大論師,一位是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繼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立有、空、中三時教判;另一位是智光,遠承文殊、龍樹,近稟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時教判。地婆訶羅從印度帶來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親自和他對校,果然獲得“善財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識”和“文殊伸手按善財頂”兩段,立即請地婆訶羅在西太原寺譯出,這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此後,法藏又奉詔和地婆訶羅及道成、薄塵等同譯《密嚴》、《顯識》等經論十餘部,合共20卷。
公元690年(武后天授二年),於闐沙門提雲般若在魏國東寺譯經,法藏也列席譯場。提雲般若譯出《大乘法界無差別論》,法藏特為該書作疏,發揮新義。
公元695年(證聖元年),於闐沙門實叉難陀在洛陽大遍空寺重新翻譯《華嚴經》,法藏奉詔筆受,後來補入日照法師所譯兩段。
公元699年(武后聖歷二年),重新翻譯的《華嚴經》告成,詔令法藏在洛陽佛授記寺宣講。他曾為武后講新《華嚴經》,講到“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等。武后聽了茫然不解。法藏於是指著殿旁的金獅子作譬喻,武後於是豁然領悟。法藏把當時所說集錄成文,叫作《金獅子章》。他還為了讓不了解剎海涉入重重無盡義的學者開悟,拿十面鏡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對,中間安置一尊佛像,然後燃燒一支火炬去照著他,使學者通曉剎海涉入重重無盡的義旨。
公元703年(長安三年),義凈等華梵十四人先後在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共同翻譯《金光明最勝王經》等21部,法藏奉詔證義。
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南印度沙門提流志在大內林光殿翻譯《大寶積經》,法藏也奉詔為證義。新譯的《華嚴經》,雖然增加了《如來現相》、《普賢三昧》、《華嚴世界》及《十定》等品,卻脫漏地婆訶羅所補譯的“文殊伸手過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文。法藏用晉唐兩譯對勘梵本,把地婆訶羅的譯文補在實叉難陀的脫漏處,於是得以文續義連,現行即此本。總之,法藏對於當時的譯事,特別是《華嚴經》的翻譯是有貢獻的。
法藏前後講新舊《華嚴經》30餘遍,中宗、睿宗都曾請他作菩薩戒師。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長安大薦福寺圓寂,享年70歲,葬在神禾原華嚴寺的南邊。秘書少監閻朝隱為其作碑文,概略地陳述了他一生的事迹,這就是現存的“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
智儼所創教相和觀行的新說,得到法藏詳盡的發揮,才使一宗的教觀建立周備。所以法藏是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世稱他為華嚴宗三祖。
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又西遷康居,康居被迫南遷到索格狄亞那地區。
公元265~274年(晉武帝泰始年間),康居王遣使到晉朝獻馬,希望與新崛起的西晉王朝結交。
南北朝時期,嚈噠勢力崛起,康居相對衰弱。嚈噠人西遷后,康居國不復存在。
2006年,哈薩克考古學家在南哈薩克州庫爾托別遺址進行發掘時,發現了刻在黏土磚上的古康居國文獻。
指揮發掘的考古小組負責人波杜什金對新聞界表示,這些珍貴的文獻刻在燒制的黏土磚上,呈現出阿拉美亞文獻的特徵,比安息、花剌子模的墨寫文獻要早得多。波杜什金說,近三年來在庫爾托別遺址共發現了10塊刻有古代文獻的黏土磚。就其重要性來講,此次發現的黏土磚位居第二,上面分6行刻有44個字元。這些字元里隱藏著與古康居國歷史和文化有關的極其珍貴的信息。據波杜什金介紹,近年來一些知名學者已著手釋譯這些文獻。根據他們得出的結論,古康居國時期布拉哈綠洲的首府是諾沃阿克梅坦,意即“新居處”。此外文獻中還提到一些古老的城市如恰奇、納赫沙布、撒馬爾罕和克什等。它們都位於今天的烏茲別克境內。哈薩克國家博物館高級研究員阿基舍夫也高度評價了這些古文獻的價值。他認為,黏土磚上記載的大量文獻將改寫整個地區的歷史。據史書記載,康居早在公元前3世紀便作為一個國家名稱出現在中亞地區,康居人同哈薩克族人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