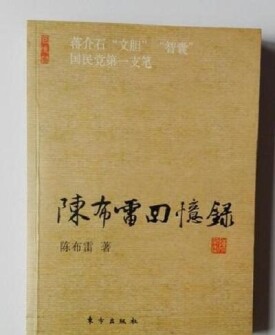陳布雷回憶錄
2009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陳布雷回憶錄》是2009年9月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布雷。
2009年9月,《陳布雷回憶錄》在大陸出版,此距陳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過去。這次東方版的《陳布雷回憶錄》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紀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根據影印手稿重新校讎排印的版本,在附錄內容上有更多的擴展與充實,對於大陸讀者來說,可謂是一個翔實豐富的新穎版本,尤其在某些關鍵處,適以“按語”而延伸閱讀,從中亦可見編者之用心良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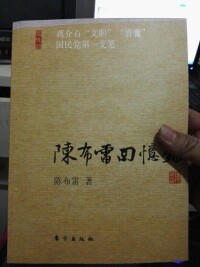
陳布雷回憶錄
陳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原名陳訓恩,號畏壘,字彥及。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1911年任上海《天鐸報》記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會;1920年任《商報》主編;1927年加入國民黨,歷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35年後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秘書長、最高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介石草擬文件。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殺。
前記
自序
自序
回憶錄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一歲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二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三歲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四歲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歲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歲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一八九九)十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十一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十二歲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二)十三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三)十四歲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四)十五歲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五)十六歲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六)十七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七)十八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八)十九歲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九)二十歲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二十一歲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二十二歲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二十三歲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二十四歲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二十五歲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六歲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七歲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九歲
民國八年已未(一九一九)三十歲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三十一歲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三十二歲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民國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四十一歲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歲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四十九歲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歲
附錄一 政論
附錄二 書信
附錄三 遺言
附錄四 論陳布雷
後記
評《陳布雷回憶錄》:不得不死的陳布雷
從政不是他的始願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陳布雷其人與事,仍不能簡單地從其作為蔣介石的高級幕僚這一特殊經歷來加以認知或解讀,從他的回憶錄以及諸多友人的懷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聞記者而從政,“可以說不是他的始願”,“志在言論報國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滄波語)是他的志趣所在,陳氏後來確實是被徵召才離開了當時中國的言論界。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葉,中國的內戰混亂已極,知識分子對時局的看法和呼聲,已成為“時代的指針”。就言論界而言,後來有“南陳北張”之稱,“南陳”即上海商報主筆的陳佈雷,“北張”乃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鸞。一般認為,陳布雷“以敢言與文筆犀利著稱”,雖然商報只是商界人士創辦的一份報紙,論實力、背景,既不能與國民黨的報紙《民國日報》相比,也無法與當年的進步黨或改良派主辦的報紙《時事新報》一時競逐,“但是商報便憑著布雷先生的一枝筆,在上海輿論界橫掃千軍,獨樹一幟,使當時上海的有識之士,除了披閱各報之外,非翻開商報,看看今天‘畏壘’做的什麼文章……”“畏壘”、“布雷”是陳佈雷的常用筆名,其本名訓恩,字彥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當然,陳布雷以報人而從政,除被徵召這一特定因素,與他本人的政治態度也有一定關係。我一直有個看法,文人從政即所謂“思出其位”,其中既有個人理念信仰追求、現實環境嬗變、實際能力等因素,同時亦取決於政府的態度。也就是說,並非每一個想從政的人都可以從政的,儘管機緣與動機各不相同。陳布雷對北伐及中國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認知,他的秘書蔣君章就認為“先生對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運動中,沒有實際參加,惟對革命運動,則贊助甚力”(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4期,第9頁)。所謂“贊助甚力”,無論從政前或其後,無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雖屬不易,卻亦殫精竭慮,死而後已。陶希聖說過這樣一個細節:1934年前後,陳布雷還在浙江省教育廳長任上,“蔣委員長要發表文告,一個電話或電報,布雷先生就拎著一個小包,帶著他自個用的文房四寶到南京來了,寫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實際上,從陳布雷與蔣介石的關係,或可透視蔣介石對待學術界及報界人士的基本態度。以陶希聖的個人看法:蔣介石對教授學者是一種態度,對文官與武官是一種態度,對從政的報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對後者可說是“禮遇有加”,如對陳佈雷、程滄波、胡健中、潘公展、黃少谷等人。1927年初,陳布雷和商報同仁潘公展與蔣在南昌初晤,蔣即“堅勸余及公展入黨”,並對所提出的問題,“蔣公一一解答之”。這年2月,陳布雷與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陳布雷之於蔣介石,如影隨形,至抗戰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過,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1928年,蔣曾問陳:“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甚至屬意總部秘書長一職。陳氏則答:“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
報人的本色,即有開闊的視野、客觀的思考和獨立的批判精神。進入權力中樞之後,往往體現在忠於職守,則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靜的頭腦,並非為做官而去,這一點在陳布雷身上尤為突出,一般人很難做到,或許也是他後來仰藥自殉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人曾問陳布雷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和貢獻,他淡然表示“有時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難免沒有危險。我的作用,就等於‘剎車’,必要時可使速度稍減,保持平穩”。這種“看似消極其實積極”的說法,實則是一種對國家和民生負責的心態。
權力中的超然立場
陳布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實際上就是他的“陳公館”,即他的住宅,“只有兩三個職員,有一個字寫得極好的金先生,一個辦事的職員和一個副官,後來增加一位秘書翁先生,一直到重慶,還是陳公館。……他不想擴大,始終保持原來的體制”。據蔣君章回憶,陳布雷經常對他們說:“一個人要做二個人或三個人的事,對外要嚴守機密,個人最好斷絕社會關係,凡進侍二處工作的人,一律要較原來職級低兩級,以磨鍊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無名英雄的決心。”所以,從政后的陳布雷“名字不願見報”,與之前判若兩人,“過去他與一般報人一樣,也能喝幾杯酒,也打幾圈牌,他主持商報的筆政,也有許多交往的人,但是這麼一個豪爽的人,負起侍從室的職責,掌管蔣委員長的機要,一改過去豪放的生活,為人處事,非常謹慎,非常嚴肅”(陶希聖語)。
陳布雷在國民黨中是一個“超然分子”,這也是報人書生本色使然。陳布雷作為最高領袖股肱二十年,從不恃權,從不建立所謂的勢力圈,這在派系紛爭的國民黨內部是極為少見的。“當時政治場合有關人事的流行語,是‘誰是誰的人’,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誰是陳佈雷的人,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結果”(蔣君章語)。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當時大會中有三派一團,即組織部陳果夫立夫派、朱家驊派、吳鐵城派及青年團,激烈的爭奪中央委員的名額”(參見《陶希聖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後人提供),各方面推薦的候選人名單中,“很多既非對黨有何貢獻,也非為黨延納人才,而只是出於人事關係,你爭我奪,以致總裁很難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擊這樣的情況,心情沉痛到極點”(唐縱語)。蔣介石與陳布雷談話,希望他能推薦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陳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態度,同時也“不忍再增加總裁的困擾,所以一個人也沒有提”。
時任重慶《新民報》採訪部主任的浦熙修通過陳立夫的關係採訪陳佈雷,問其屬於國民黨中何種派系?陳對這個問題雖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這個問題好比待字閨中的少女,有人問她你的愛人是誰?她勢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訴你,國民黨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張群先生,吳鐵城先生,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陳誠先生,朱家驊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國民黨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則屬黨內各個派系,“這個迫人的問題,便在輕鬆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為陳布雷在權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場,故能調和各方意見,甚至運用個人的影響力妥善處理一些緊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聯大學潮即為一例。這次學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對陳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語焉不詳。依慣例,處理學潮在行政上屬教育部,新聞發布屬中央宣傳部,青年思想工作則屬三青團中央,蔣介石對此頗不放心,特命陳布雷召集一個小組,主持處理各項問題。
小組成員中有中宣部部長吳國楨、青年團書記劉健群等人,至事態最嚴重時,蔣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聯大,朱家驊時為教育部長,對此令似有不同意見,借出巡而離開了重慶,“先生對此頗感懊惱,因為這個命令的如何執行和教育部與軍事機關有關,教育部的意見尤為重要”(蔣君章語)。實際上,陳布雷深知蔣的這一命令“只是在啟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聯大”,遂提出幾點意見:其一,西南聯大問題正在設法疏導,請暫緩解散;其二,此次學潮之癥結為少數職業學生與左翼教授所煽動,大多數人則冷靜對待,可做說服工作,請學生家長協助召其子弟暫時返家,等複課時再回,同時請駐昆明部隊做臨時接管學校的準備……此時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這是重慶談判之後,對國共兩黨都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其事態只能平息而不能擴大,陳佈雷的意見得到認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們為了學校的前途,不能不曉諭學生,發生極大作用,最後只餘下極少數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風潮得以解決”。
陳布雷處事之謹慎與細密,大率類此。從中也可見在處理公務時的擔當,因而深得蔣介石的信任,總是稱他“布雷先生”。
最後主持的機構
陳布雷最後的正式職務,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其會長由蔣介石兼任。不過,他還另外主持一個小機構,即宣傳小組,“罕為外間所知”。
抗戰結束后,1946年底的“制憲會議”,國共分歧很大。“從那時起,宣傳方面的問題便日益嚴重”,蔣介石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經常與一些重要人士會談。蔣介石主持的這個會議習慣被稱之為“官邸會議”,而宣傳小組則為“官邸會議”做準備,本質上是“官邸會議”的秘書室。
這個機構十分簡單,也正是陳佈雷的一貫作風。陳作為召集人,參加會議的人均為組織機構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包括陳立夫(組織部長)、董顯光(行政院新聞局長)、鄧文儀(國防部政工局局長)、李唯果(中宣部部長)、黃少谷(後任中宣部長)、張道藩(文化委員會主委)、陶希聖(中宣部副部長)等人,主任秘書是徐復觀,秘書謝然之、蔣君章,地點在南京湖南路五百零八號陳布雷公館。這個小組會議前後持續有一年多時間,“除了有關係的人之外,外間始終無人知道”。
有個細節仍可見陳佈雷的書生本色。這個小組雖屬幕僚性質,並不負責執行任務,但有時也要支援具體的行動。1947年秋冬之交,蔣介石特撥一筆款項,交陳布雷宣傳小組使用。其時正值法幣幣值急劇下降,有人建議陳布雷把這筆錢換成黃金或美鈔,或可發揮更大的效力。陳布雷無論如何都不肯答應,稱與國家的法令法規相抵觸,只同意把這筆款項以“宣克成”的名義存入某些銀行。第二年秋,翁文灝政府推行幣制改革,金圓券代替法幣,這筆巨大的資金兌換成金圓券不過區區數千元,陳布雷感嘆:“我們為了守法,犧牲了國家利益,卻便宜了金融家。”
其時國民黨政權正面臨兩個重大危機,一為軍事上的挫敗,二為經濟上的恐慌,即金圓券實施后的限價政策,已發生動搖,“國統區”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見紛然而起,多想經陳布雷而上達蔣介石。有的用書面陳述,有的當面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1976年,蔣君章在台北傳記文學社舉辦的“陳布雷專題”座談會上這樣回憶:“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闥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們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恆鬱鬱不樂。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的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吶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無任何預兆之下,陳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藥,氣絕於次日凌晨,終年五十九歲。陳死後,這一小組由中宣部長黃少谷主持,程天放繼任中宣部長時,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傳小組事實上已經停頓”。
政權的悲劇
陳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脫,這一悲劇實際上也是那個政權的悲劇。
以陶希聖的日記(1948年11月16日),當時“流言盛行,謂布公主和,或反對某些政策等”,可見陳之死所引起的震動和種種揣測。後來有人謂之“屍諫”,這一推斷,不知有何根據,連留在大陸的張治中也表示懷疑。那麼,陳布雷究竟為何要自殉,僅僅因為“觸目傷心,心中抑鬱,不能自解”、“體力日衰,報國無從”?抑或次女陳璉(前妻楊氏所出)和女婿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其實,這本回憶錄並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回憶錄一冊、二冊僅至民國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餘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較之於“畏壘室日記”,其記述言簡意賅,不動聲色,嚴謹有度,實難見出其內心之軌跡。
其弟陳訓慈(叔諒)和外甥翁植耘(陳氏五妹之子,早年做過郭沫若的秘書)等人有過這方面的追憶文字,但這一類的史料顯然需要進行甄別與分析,否則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陳訓慈寫過一篇《先兄陳布雷雜憶》,台灣《傳記文學》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談及陳布雷與CC的往事,稱其兄曾遭遇陳立夫的一次脅迫。從美返台定居的陳立夫即撰文(第71卷第3期)反駁,認為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點出“有人稱其為共產黨員”。而跟隨陳布雷七年的秘書蔣君章則針對翁植耘在香港報刊發表的文章,以及滯留大陸的陳的副官陶永標之口述(由他人筆錄),同樣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針對所謂“屍諫”一說,認為“與事實完全不合”,是對陳佈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見,不論大陸或台灣,倘若意識形態色彩不褪,對歷史人物就很難有客觀的判斷。
這次出版的《陳布雷回憶錄》,增添了許多內容,如陳佈雷的政論、書信等,這是我所看到的台灣版本沒有的。友人回憶、評說部分與台灣版本也略見出入,有刪也有增,編者大概有自己的考慮。而編者後記中有一段話,“希望俟該書再版時,有一個更為詳盡的本子呈現給讀者,同時也期待著陳布雷日記早日出版”,表明有關陳佈雷的史料還有待進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從這一點看,目前存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兩蔣日記,國民黨大溪檔案、國民黨黨史會檔案資料、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資料,台灣《傳記文學》中一些尚未採用的史料,包括大陸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資料,等等,或許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陳布雷在那個時代的全貌。我相信,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