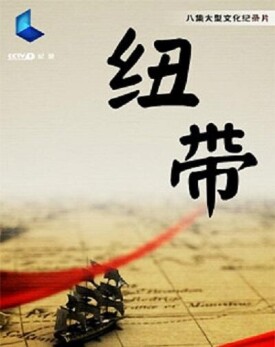紐帶
央視紀錄片
徠地球是圓的,這是近代化以來人類才逐漸認清的事實。在此之前,世界,曾經是一個個各自獨立的文明體。隨著跨文明交流的深入,世界,才真正成為世界。而其它文明體與中國之間對話的紐帶,就是漢學或中國學。
Sinology,漢學,是世界各國關於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研究。
本片重在講述中外文明交流過程中的跌宕歷程。全片近50個故事,通過對一個個漢學家與中國的交往以及他們的命運的生動刻畫,描摹出漢學(中國學)產生、發展和變異的宏大歷史圖景。
製片人:高曉蒙、韓雯;
總監製:胡恩;
監製:魏斌;
節目監製:史岩,石世侖。
• 2015年5月17日―24日,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9)《特別呈現》時段(每天20:00)(1—8集)
• 2015年6月8日,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CCTV-3)頻道特別編排(13:26―20:26)(1―8集)
• 2015年8月17日,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CCTV-3)頻道特別編排(10:34―18:00)(1―8集)
• 2015年8月20日,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CCTV-3)頻道特別編排(06:40―14:00)(1―8集)
編 筐——關於《紐帶》的糾結
《紐帶》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說得好聽,但片子,偏偏卻是拍出來、寫出來、編出來的!所以這句話,全當就是聽個樂子。
做片子,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折磨人。大氣候,小環境,都是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不過,這樣也好,夠刺激,也真有挑戰。
一拿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有人曾建議,你就挑什麼好玩兒往裡面擱什麼,反正,“紐帶”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想想也對,老大不小了,較什麼真呢?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既是做人本分,也是做片子的常識。
但糾結的是:真這樣做了,反倒卻無從下手。
萬事,總得有個先後。關於漢學或中國學,媒體很少有過鋪墊或知識普及,如果隨意挑一些感興趣的內容、獵奇的知識、另類的人物排列組合,也不是不能幹,甚至可能會有好的收視率。但我總覺得這樣的話,名不正,言不順,片子對未來的價值會大打折扣。好不容易有人出錢,能讓你關注一下冷門的漢學或中國學,如果不從學術價值的角度去考量、構建,似乎總感到有點對不起誰。
我是一個笨人,所以,還是實實在在地做點磚瓦工的活兒吧。哪怕只是搬塊磚呢,也好讓後人能踩著向上爬!於是,我們放棄了那個取巧的辦法(不過,也許是錯失了一個聰明的選擇,誰知道呢?)最終選擇了一個最累、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做法——直面漢學或中國學的前世今生、起承轉合。
累,首先累在邊框(編筐)。漢學或中國學雖然從來不是什麼顯學,但卻是學問中的學問,既深奧又瑣碎。起起落落四百多年了,人物一大堆,涉及到的學科也多不勝數。如何界定?如何分集?沒有現成的資料與模式可資借鑒。
其次,表現也不容易。畢竟是一門高冷的學問,在這樣一個碎片化、娛樂化當道的時代,要把它影像化,天然就是逆行、就有障礙。因為想好看,就得講故事;而要講故事,就得人物少。有故事的人物不見得有價值,有價值的人物也許沒故事。況且,價值如何衡量,也還是個大問題。
一個字:難!兩個字:太難!
一個字:煩!兩個字:太煩!
前前後後,專家見了一大堆。每個人都掌握著無數的故事、巨多的人物,但都是不可或缺,都是意義非凡。每一個專家,又都是那樣地固執與堅持,讓你敬佩。其實,這也是這些年每做一部新片子,我們都會面對的困惑。不想走常規路,往往就意味著無路可走,你得自己趟一條新路出來。
記得多年前拍《大國崛起》的時候,跟社科院的秦海波老師西班牙、葡萄牙走了一路,也吵了一路。不過,到今天,想起來大家都是好朋友。因為所有的目的都是為了一部好片子,否則你好我好大家好,何樂而不為?
楊煦生老師、孟華老師、耿升老師、張西平老師、許明龍老師、嚴紹璗老師、李明濱老師等等等等,我的腦子總是會想起每一位老師的懇切、每一位老師的語重心長、每一位老師的興高采烈,以及我潛意識裡與每一位老師的衝撞。
大家內心都有一個筐子,可匯聚在我們這裡,就是一團亂麻。
電視,說到底承擔不起那麼多。你們都是大學問家,我們充其量只是些手藝人。怎麼樣把一個個完整的筐子,撕裂了,擰成繩子,再重新編一個大筐子。我們需要說服你們,其實更需要說服我們自己。
來來往往中,成型的筐子前後編了三個。當前兩個被依次否定的時候,第三個筐子,我們已經很堅定。它既不是按照人物的重要性分類來的,也不是按照漢學或中國學的學科設置界定的,而是走了一條用大歷史的脈絡與國別相結合的分集方式。這大概是只有我們這些外行,才敢處理的方式了。
當一個個人物陸續在筐子里就位的時候,我已經看到了未來的片子。
接下來,該讓這個筐子接受專家們的質疑、審視和充實了。一切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大家首先表示的是抗拒和批評,但慢慢地,他們開始用自己的智慧,儘力去豐富、完善、美化著這個筐子。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結果。
又是一輪人物和故事的取捨。原本這個筐子,我們設定的容量是九集,專家們也很認可了。但因為種種原因,只能又壓縮至八集。這對於四百年來漢學或中國學整個體系的展示,多少有一點遺憾。我們,只能儘力彌補了……
最初片子立項的時候,紀錄頻道領導想像的是在描繪漢學的同時,儘可能涵蓋幾個大的文明體。應該說,這是一個很理想化的想法。一方面,能透過漢學或中國學,展示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關係;另一方面,從可視的角度考慮,多些不同的國家,畫面質感會更強、更豐富。
但遺憾的是,像阿拉伯地區,像印度,漢學或中國學的研究還比較少,數得上的專家也不多見。而且,以八集的篇幅勾勒漢學或中國學的全貌,筆墨已經是簡化得不能再簡化了,所以,一切只能等以後再說了!
做這部片子的時候,我的腦子裡老想起一個詞——國際主義。
這些漢學家也好、中國學家也好,最初的出發點,往往都是出於興趣,都超越了眼前的功利。當然,他們的學問,無疑豐富了他們母國當下的知識體系,但如果放到一個更長久的歷史時期去考量,這對中國文化也是一個極大的反哺,尤其是走到今天,他們的研究成果,更是人類文化基因庫的標本。
有時候想想,文化,還真是閑出來的。無目的,就是最大的目的。
一晃,兩年多過去了,甘苦自知。在編筐的過程中,無數的人給了我們幫助,你們的心血,自己從片子中去慢慢感覺吧!這個筐子編完了,這一段生命的體驗也就暫時告一段落了,新的煎熬已然開始,寫下這些文字,就當是把心中的那個筐子毛毛草草地收個尾,暫時或永久地封存吧!
編好的筐子,終究是給人看、給人用的,手藝如何盡心了。但它有沒有藝術價值?有多少?或者,它究竟算不算藝術品?我們,說了不算……
《紐帶》總導演 劉軍衛
為什麼要出發?
那天非常熱,幾個編導擠在一輛商務車裡,堵在西三環。我們正要去拜訪一位北大教授,沿途七嘴八舌,聊起了片子的構思。
“你知道漢學是什麼嗎?”
我一愣,漢學,不就是和中國有關係的學問嗎?
“那國學和漢學有什麼區別?”
天啊,好像是有區別,但區別在哪兒?同事的隨口一問,給了剛進組的我一個巨大的打擊。
“漢學,簡而言之就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學問,而國學,是中國人研究自己的學問。”
和每一個剛剛了解這些的人一樣,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外國人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學問?咱們又為什麼要去紀錄他們呢?同事說,你不知道么,外國人對中國的研究,某種程度上,比中國自己對自己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也專註得多。
憑此思路,我開始“順藤摸瓜”。外國人,為什麼研究中國?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四百年前的西方傳教士們,開啟了最初研究中國的熱潮,他們的出發點,是傳播教義;而在那之後,外國對中國資源、商品的覬覦,又促使了更多關於中國的研究;到了現代,崛起的中國實力,是否又是促進新一輪漢學研究的內在推動力呢?
當然,這些因素全都出自我的猜想,做片子、講故事,還得從最基礎的事實出發。我在心裡暗自憋了一股勁兒:倒要看看他們是為了什麼。
當年九月,同事們傾巢出動。我的任務是奔赴甘肅,一路跟拍一支國外的漢學家隊伍遊覽敦煌的過程。那是我第一次去敦煌。
路上,一位有著亞洲面孔,卻說著英文的女士,意欲和我交流。車微晃,我蹲在她邊上,聽她講父親的故事。
她說,他的父親是個普通的中國人,因為結識了李約瑟而來到敦煌。李約瑟,是英國近代著名的生物化學家,中國享譽世界的四大發明,有三個是他提出的。在她父親的眼中,李約瑟對於中國,完全有種如饑似渴的好奇態度,對於中國未曾被發掘的科學技術,對於上世紀初那些有著先進頭腦,卻淹沒在戰爭中的中國學子,他發自內心地同情,並在本不該他來承受的環境中,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他們。
如果推究他這麼做的原因,或許是巨大的好奇,更或許是來自對一位中國姑娘的愛慕。對於我的刨根問底,女士有些疑惑。因為我一直在想,如此簡單的理由,真的就能帶給他乘著簡陋的飛機前往中國,穿著破舊的棉大衣、拉著一條大狗走進荒漠與延邊的勇氣?
蹲累了,車外,遠遠能望到石窟。從入口到走進石窟,我們沒有再交流。但洞里嘆為觀止的石窟,給了我們默然的答案。
我忽然明白,為什麼出發,或許不重要,中國還是那個中國,可當你真的到達這裡,領略了這股神秘而厚重的力量,會發現,有些東西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國度,而是這世界文化基因庫里,難得的一員。
猜想那些漢學家們,也有同樣的感觸,但這種感觸,卻很難簡單表達。漢學家們選擇用畢生的研究來表達,而學識淺薄的我們,只能依附著他們的故事,悄悄透露一些自身的感觸。
朱允
2015年3月22日
朋友圈
我的微信朋友圈裡,和《紐帶》相關的外國人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在義大利的司機。他是都靈人,當時為了我們這單生意,特地坐了六個小時的火車到羅馬。他的義大利文名叫Francesco Davico,但他給自己起了一個發音完全不同、意思也毫無關聯的中文名:懷暖莫。按他的理解,含義是:心懷溫暖與冷漠。
為了不被矯情死,我們都叫他“莫莫”,和時下交友神器諧音。
一次,我們在羅馬國家檔案館拍攝羅明堅的地圖原稿,花了大約30分鐘結束拍攝,出來的時候,莫莫已經和兩個中國女遊客加上了微信,聊得火熱。於是,我們得出結論,莫莫就是個交友神器。
攝影潘老師說,莫莫就是一個可愛的“小人”。一口流利的京腔,不會成語,卻把中文的粗口學得很齊全,沒有正經工作,整天就尋思著把家鄉的各種東西賣給中國:傢具、紅酒、兔子皮。說起來,他對我們拍攝的內容還真沒什麼興趣,但他是真的喜歡中國姑娘。
拍攝第四天,我們驅車前往距離羅馬一百多公里的小鎮,拍攝一個家庭陶瓷作坊。把我們送到后,他就消失了,等回來的時候,身邊不出意外多了一個中國美女。她是莫莫在南京的時候認識的,正在佩魯賈讀研究生。佩魯賈離我們所在的小鎮不遠,看起來,莫莫早就計劃好了。
那天晚上,莫莫把她送回了佩魯賈。但奇怪的是,兩天以後,這個美女竟然出現在了羅馬。想必,莫莫是說了什麼動人的話將她“騙”來了,那之後,我們就開始偷偷討論,大致的內容就是他如何如何勾搭妹子,因為既有印象,甚至都會為妹子被這個“花花公子”欺騙而感到惋惜。
臨走前一天,我們吃了一頓大餐,義大利人上菜慢,我們吃到很晚。越晚我就越擔心,因為,我和莫莫一個房間,也許一會兒我會比較尷尬。但最後,事實證明都是我們心術不正:在接近凌晨的時候,莫莫把我們單獨叫出來,說堅持要開三個小時的車把美女送回佩魯賈,油費自付;還有剛才的餐費,女生的那份他出,算是他請的。
後來才知道,這個美女是莫莫的前女友。因為異國的關係,他們最終沒有在一起,得知她來義大利學習,莫莫始終沒有勇氣見她。當看到我們的行程上有離佩魯賈接近的城市,他毫不猶豫地接了活,因為這樣也許就有機會見哪怕一面。莫莫害怕,以後再沒有這種機會了。
我們在拍攝過程中,所有關於高羅佩的資料、採訪嘉賓的信息等等,都是她提供的。當我們在荷蘭的時候,她還將她的兩個舅舅和媽媽難得地聚在一起接受我們的採訪。
Marie-Anne從沒見過外公,所有關於外公的事,都是媽媽告訴她的,事實上,高羅佩當時哪怕在家裡,也沒有與孩子過多地交流。高羅佩的四個孩子,除了大兒子仍然在萊頓大學工作外(研究的是日本藝術史),
其他人都在做著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的工作,但這個三十齣頭的外孫女將自己的全部時間都貢獻給了外公:辦高羅佩展覽、為徐克的電影提供幫助、還與重慶的古琴社合作還原了高羅佩當時的辦公室。
每天都會刷朋友圈,都能看到Marie-Anne在各種奔波的同時,中文也越來越好,還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高若蘭”;我也能看到莫莫紅酒賣得越來越火,時不時地還有他日漸純熟的中文吐槽水平。
看他們的朋友圈的時候,我也有疑惑,這倆人如此痴迷中國是為什麼?後來想想,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也許只是因為身上流淌著1/4的中國血液,或者心裡有個忘不了的南方姑娘。
其實《紐帶》也沒那麼玄乎,漢學也沒那麼難懂,漢學家們,初衷和動機也許和莫莫、Marie-Anne沒什麼兩樣。當然這兩個故事,在《紐帶》里是看不到了,所以借這個機會寫出來,這是我能看到的活生生的紐帶。
《紐帶》導演 程方正
有一些地方很少有人知道
想起了一部電影片名《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很多人不懂這句矯情話什麼意思,但在拍攝《紐帶》的途中,我常常有和這個名字一樣的感受。
在澳門,城小車多,單行線的設置讓這裡很少堵車,但眼見很近的地方,打車卻要繞很多個彎坡。跟司機說去馬禮遜墓地,第一個師傅說不知道,拒載了。碰見第二個,猶豫了一下,問是不是基督教墳場啊?然後把我們拉到了墓地斜對面的另一所教堂。下車問了幾個當地人,拐來拐去,找到了拍攝地——馬禮遜小教堂,也是基督教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所教堂。
秋日陽光足,茂盛的樹影打在晃眼的白色圍牆上,映著滿園落地的雞蛋花。撿起幾朵走到後院,錯落有致的基督徒墓碑中,馬禮遜和夫人瑪麗靜謐地躺在一角。
現今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中有一份告示,是清政府頒布禁煙令后,貼出的一份驅逐在澳門的英國人名單。這份告示的英譯本,就是兩百年前,身在澳門的英國人馬禮遜所譯;在今天,遇到困難的中英生詞互譯,我們隨時可以查詢到任何版本的字詞典。但創造首部《華英詞典》的先輩,也正是躺在這裡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同樣在肇慶,我們還找到了埋藏在居民巷的利瑪竇舊居;在上川島,找到了為傳教士開闢前路的首位來華使者沙勿略;在杭州,找到了率先返回歐洲為中國禮儀申辯的衛匡國等等等等。在拍攝間隙,不時會遇見捧著花的外國人到教堂或是墓園禱告,也偶爾會遇見誤打誤撞的遊客覺得美麗來照相。在語言交流已沒有太多障礙的今天、在太多貌似熟悉的地方,為跨文化交流做出貢獻的人們,還有很多故事很少有人知道,還需要我們切身處地的去感知他們的存在。
《紐帶》導演 孟妍
邂逅伯希和
“傍晚六點,在走完這走不完的一程的最後一段,我們到達了千佛洞,我自然是那裡的不速之客。——伯希和,1908年2月25日
他,形容痩削,目光堅毅,鬍子拉碴,躊躇滿志;
他,從巴黎到敦煌,走過被歲月掩埋的絲綢之路,不辭萬里;
他,精通十餘種語言,憑著一口流利的北京腔,遊走於中國的文人墨客之間。
在有的人眼中,他是“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也有人說:“如果沒有他,漢學將成為孤兒”。
我是一個謹慎的人,在“擇偶”(選擇偶像)方面猶是如此。但是,當我得知這些元素濃縮於一位百餘年前的法國青年時,我的心底,埋下了一粒崇拜的種子。
他叫保羅·伯希和,名字後面總是掛著一串長長的頭銜:法國漢學家、法蘭西文學院院士、法國亞細亞協會主席、巴黎中國學院院長等……以及本片第四集《搶回去的學問》中的主人公。
於是,啟程。捕風捉影。
飛往歐洲的航班上,陷入了深思。從北京回巴黎,當年的伯希和先生,應該是會乘火車穿過茫茫西伯利亞。如今直飛的航班,與當年的路線並無二致。在深夜的機艙里凝視屏幕上那條的軌跡,心中感慨萬分。
世人常將伯希和與斯坦因、華爾納等人相提並論,殊不知,他們對敦煌的態度卻完全不同。
相比於斯坦因的貪婪、華爾納的殘忍,伯希和是一位真正的學者。除卻想把這些寶貴的遺產化為法國的財富以外,他真正是害怕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會遭受不測。在艱辛的歸途中,他甚至不顧勞累,將最有價值的部分抄錄下來。
縱然,回首這些往事,國人當然是心痛不已,可是百年前的中國,備受凌辱,哪裡又有保護先人遺產的餘力?
有信仰的人總帶著一顆朝聖者的心,憧憬著不經意間會有那麼一刻,與聖人在旅途中心有靈犀。
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與法國遠東學院,聆聽學者們津津樂道於伯希和先生人生中的精彩,也理性地分析他學術上的旨趣;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獲睹千餘年前的敦煌寫本至今完好如初,穿在卷子上的麻線仍然健在;
在吉美博物館,邂逅了每一件藏品的微笑,與古希臘遺跡中的神像何其相似,文明並不會因為語言、地域而被阻隔。
處於開拓期的學術時代,總是令人嚮往,不斷湧現的新領域點燃了人類的學術激情。伯希和與敦煌的邂逅,也為敦煌學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或許,有時會突然冒出生不逢時的念頭,但若生在那個時代,又如何知曉這些傳奇的人生。
如此人生,拿來回望,定要比親身體驗要合適得多。
《紐帶》導演 屈楚
記史華慈先生
“房子賣了,墓地也賣了,你懂的,我可是賺了一大筆錢啊!”這筆橫財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改變。
史華慈先生鬆開了襯衫領子,有些臃腫的脖子終於解放了。他那本就洪亮的笑聲,又放大了一倍。
採訪結束了,史華慈先生帶著攝製組,去向當天最後一站——墓地。
“原本的墓地,離這裡很近。當時他剛剛入土,地產商打電話告訴我,墓地升值了,一轉手就能賺四萬美元。”流淌著猶太血統的史華慈先生,似乎很善於理財。一路上,還在不停地傳授著他的理財經。
顯然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所以我試著轉移話題,“他曾經和你聊過什麼關於中國的事情嗎?”
“說過一些,但我們沒有興趣。你知道的,我們兄妹幾個人是標準的美國人,上班,下班,看橄欖球比賽。事實上,我們最多的話題是橄欖球賽。”
我終於還是見到他了,在那片墓地的角落裡,在那塊嶄新的墓碑上——本傑明·史華慈。
本傑明·史華慈,美國歷史學界的驕傲,中國學泰斗,其天才的研究獨闢蹊徑,堪稱中國研究界的“愛因斯坦”。在他有生之年,幾乎把學術生涯全部獻給了中國,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人愛中國,有人恨中國,我尊敬中國。”他是我此行的目的,從某種角度說,也是我此行的動力。
對史華慈先生而言,他只是一位慈愛而忙碌的父親。但,他幾乎都不知道父親在忙碌什麼。
事實上,在見到史華慈先生之前,我就已經從他父親的鄰居那裡聽說了另一個故事。在父親死後,在他賣掉父親的故居之前,他就把屋子裡所有父親珍藏的中國文物,全都扔進了垃圾桶。隨後不僅得到了史華慈先生的親口承認,而且還聽說了他倒賣父親墓地的故事,這更堅定了我的看法,倒霉催的敗家子!
此時此刻,站在本傑明·史華慈的墓前,我真不知道是該悲哀,還是該憤怒。作為一代大師的後人,就算不是將門虎子,至少也不應該是眼前這幅樣子吧?靠倒賣先人墓地,靠甩賣遺產,還是以甩為主,以賣為輔,過日子的史華慈先生。這要是放到中國,死人也得讓氣活了。
不!也許不是這樣。盛怒之餘,我反而冷靜了下來。
幸好這不是在中國。
理性的剋制,這是本傑明·史華慈最大的特點,從那句不愛不恨,只是尊敬中國,就不難看出。他愛自己的孩子,他也熱愛研究中國,但這只是他的愛。他沒有選擇把自己的愛強加給孩子們,從小就向他們灌輸關於中國的各種思想。中國對他很重要,但憑什麼就要對自己的孩子也重要?他的一生轟轟烈烈,但憑什麼自己的孩子就不能平平淡淡?
大師也罷,混子也好,人的一生哪裡又有什麼高下貴賤呢?作為一個父親,本傑明·史華慈送給孩子們最珍貴的禮物就是選擇的權利。也許他不僅是為學術大師,也是一位好父親。
我並沒有為我之前不太友好的態度,向史華慈先生道歉。一方面是我羞於啟齒,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無法向他解釋清楚我生氣的理論基礎——中國的孝道。幸好,史華慈先生顯然不需要我的道歉,他還在不停地講著只能逗樂他自己的笑話。
拍攝完成,臨別時分,史華慈先生面色嚴肅的走到我面前,問出了最後的一句話:“來時候的油費誰給我報銷?”
任志勛
2015年3月19日
拖 延
製片通知要寫導演手記,但我內心其實很抗拒。不想寫,是因為一直以來並不願意接受《紐帶》時候的自己。
2013年,從學校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懷著對影視的巨大熱情,卻驚訝地發現一個學電影理論的人並寫不會寫劇本。利瑪竇、羅明堅、衛三畏、費正清……,所有與漢學、中國學相關的人物和故事都靜靜地存在於各自的時間、空間里,要怎麼讓這些人物、故事、線索穿越紛雜、浮出水面是如此艱難。他們探討故事時在爭辯、總導演改稿時也蹙著眉頭,但我卻什麼忙也幫不上。
於是,懷著半分羞愧、半分堅持,開始從製片工作做起,做表格、寫郵件、列採訪對象、出採訪提綱,到之後制定拍攝計劃。走到今天《紐帶》快要收尾,回頭看,發現做好這些所謂的瑣碎也並不易。
花了兩天為第七集《中國學,別開生面》採訪嘉賓做一份表格,做完后卻被製片指著鼻子罵:你這做的是什麼?也抱怨過,但是邊抱怨邊調整,加粗、變化字體、標題居中,做完后拿著整齊、美觀又毫無瑕疵的表格,突然心中充滿對訓斥的感激。三多堂是一個對細節要求到苛刻的公司,被指著罵的不是一個人,也不止一次,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高要求,正是因為發自內心地感受到了細節完美的必要性,才會人人都習慣高標準。
還在讀書時,學校常常也會有知名製片人來開講座,但那些靠著每一次溝通掌握的經驗,很難有人能憑藉幾次講座就能說得清道得明。那些看似極其簡單的環節,稍微協調不周都會為項目進度帶來麻煩。整個項目中,這樣的挑戰無處不在,突髮狀況常常都有。魏斐德,著名的美國中國學家,在和他的妻子梁禾女士聯繫好所有拍攝后,整個加利福利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相關教師及圖書館工作人員都做好了拍攝準備,但是劇組人員卻因為突髮狀況未能到達,凌晨5點被隔洋電話叫醒,聽著梁禾老師略帶焦急話語,心裡亂作一團,她一直以來的熱心,中國研究中心的協助,每位採訪嘉賓的配合……人生中第一次欲哭無淚的突髮狀況,萬分歉意卻無法解釋。事實上,問題的環節只是因為溝通未暢達,銜接才不夠順利。連道歉都來不及細說,開始重新協調,好在之後一切順便。
上川島,傳教士沙勿略帶著終身遺憾長眠的地方。2013年11月,攝製組一行四人開始了香港、澳門、廣東開始拍攝。早五點、晚十二點,常有的事情,卻因為一路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一路歡笑並不覺得辛苦,何況到了上川島后,我們的拍攝已經進入了尾聲。回京后,就要準備12月份北京的漢學研討會拍攝了,這一次第七集《中國學,別開生面》中涉及到的重要學者都會出席,特別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朱政惠老師,作為“美國中國學”的第一人,從第七集初稿開始朱老師就不斷地給予意見,這一次也是希望有機會能當面感謝他。照例像往常一樣給他手機發了簡訊:“朱老師,12月我就回京了,期待和您北京見!”可是這一次,很久都沒有得到回復。
當第二天帶著疲倦回到賓館時,打開手機,跳進來一條簡訊:“朱政惠老師已經於11月13日去世。”那一晚上川島的賓館里,兩個女編導哭了一夜。
寫下上面這些話,也好像一次梳理,是兩年來第一次梳理清楚,我以為的拖延,是一種對自己尚不滿意的抗拒。但這一路我們也各自成長,承認不足也是我們人生道路上必須學會的技能,它也讓我收穫著與紀錄片的情感交匯。謝謝《紐帶》,帶我走進紀錄片。
唐毓珉
2015年3月22日
我認識的“理雅各”
我對英國,一直以來,都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或許是我曾在那裡求學三年的緣故吧。2013年,紀錄片《紐帶》的拍攝,讓我再一次踏上了大不列顛,這個令我神往已久的國度。
出國留學和出國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前者是抱著學習他者的心態,謙虛謹慎;後者自然也是謙虛謹慎,但莫名有了些成就感。
《紐帶》是一部有關漢學的紀錄片,在此之前,我對漢學了解甚少,英國漢學也只是聽說過李約瑟先生的事迹。半年的腳本創作,讓我對英國漢學,這個龐大的漢學體系其中的一支,有了全新的認識。馬禮遜,理雅各,翟理斯等英國漢學家同李約瑟先生一樣有著豐富而精彩人生經歷。
那麼問題來了,英國漢學的巔峰時代在19世紀,如何才能把這些已故英國漢學家們拍“活”呢?
在寫稿時期,我經常報名參加在北京的大小漢學會議,讓自己多受些漢學思想的熏陶。有一次,在北京郊區,有幸結識了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主任,費樂仁教授,茶餘飯後,得知費樂仁教授與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的後人關係甚好,經常有來往,於是便委託費老師聯繫理雅各後人的採訪拍攝,結果是令人欣喜的,對方很歡迎我們到他倫敦的家中做客。
寫到這裡,我的職業病就犯了,必須多廢話幾句,給大家腦補下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的歷史背景。首先他是一名“傳教士”,鴉片戰爭后在香港傳教並開辦英華書院,在中國生活20多年,用了前後25年翻譯《中國經典》,並因此獲得首個法蘭西文學院的“儒蓮獎”,回國后定居牛津,受聘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
接受採訪的是理雅各的重孫克里斯托弗·理雅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英國紳士,五十多歲的樣子,一進門他便面帶笑容用一口地道倫敦腔說道:“你們好,我是你們拍攝主人公理雅各的長子的長子的長子,歡迎你們。”說罷,便指了指樓道牆上掛著的理雅各畫像,又指了指自己,不得不佩服基因的微妙。由於克里斯托弗的健談和幽默,採訪在輕鬆愉快中完成了,隨後的紀實拍攝也正因他是理雅各後人的身份變得妙不可言。
傍晚的時候,拍攝結束了,他送我們到門口,車子剛要發動,他走向前來,我搖下車窗,他看著我,臉上沒了笑容:“我想你們可能想去拜訪我曾爺爺,他就在牛津城北的沃夫寇特公墓,住在那有些年頭了。”說完他便揮手作別,我卻被他認真的表情和詼諧的話語弄得哭笑不得。
數天後,早早結束了在牛津大學的拍攝,路邊小店買了一捧康乃馨,準備去拜訪理雅各先生。我平日有個癖好,喜歡在名人的墓前靜靜的呆上一會兒,國內外墓地去了不下百十個。駐足墓前,四周的寧謐將時間靜止了,剎那間有種與先人神聊的快感。
從牛津城北上,驅車十里,穿過一個小鎮便來到了理雅各先生的“住處”。這裡環境幽靜,密密麻麻的墓碑矗立在爬滿的青苔小路旁。沒走兩步,一座非常樸素的墓碑旁堆滿了鮮花和零零散散幾本《霍比特人》小說,詫異之餘便掃了一眼墓碑上的名字,Tolkien。當時我就聯想到英國著名小說家J.R.R.托爾金,更何況他正是在牛津大學教書啊,連忙湊上前去仔細看了看,果然是J.R.R.,這麼一位英國奇幻小說泰斗竟然這麼樸素的埋葬在這裡。
我走到理雅各先生的墓前,墓碑是用先生家鄉的阿伯丁花崗岩做成的,碑文中短短几行字努力的訴說著先生的生平。
我把那一捧康乃馨放在墓碑旁,深深地鞠了一躬。
魏慕軒
2015年3月23日
給漢學家畫像
《紐帶》,初聽這名字,似乎很難把握片子要講什麼。所以每每約專家採訪,或者給親朋好友介紹時,總要“轉述”闡釋為:講“海外漢學”的片子。而這樣一來,大抵又不得不解釋下什麼是“漢學”……學術循環,無窮匱也。一覺書齋氣濃厚,二覺好生隱晦——此處應有彈幕:無趣的談資,你們這名字還真給聊天拖時長啊!(對,若叫《中國通》什麼的,怎麼可能碼這麼多字?)
言歸正傳。時間到了2013年的尾巴,據傳急著播,所以大規模的剪輯製作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不舍晝夜。然而就在此時,還存在“缺醫少葯”的情況:這個畫面沒有,那個採訪沒說,等等。其中,很迫切的一個問題,就是不少故事主人公沒有適用的影像資料。怎麼辦?畫。把沒有的畫出來,把模糊的畫清楚,把年邁的畫年輕,把青春的畫老朽……而這個“重任”的一部分,也意外地落在了我身上。
2014年,元旦,網購的畫板、紙、筆到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五十多根不同型號的筆一字排開,十平米見方的小屋顯得更加擁擠。就這樣,帶著大家的信任,已經輟筆八年的我,在新年頭一天,重新拾起了畫畫的“童子功”。自此,白天公司剪,晚上回家畫,就成了隨後兩個月工作的基本節奏。
給漢學家畫像,這是一項多麼高尚的工作。因為通過前前後後數月的深入了解,甚至住他們住過的城,走他們曾走的路,翻看他們那些帶著歲月沉香的書稿,了解越深,欽佩也就越多,能為這樣一群有著特別情懷的人畫像,自然是幸運的。不同於拍攝、結構、剪輯這些人的故事,畫,需要直面,直面他們的眼、耳、口、鼻,直面他們的高、低、胖、瘦,這就要在了解的基礎上去體會,去想象,去丈量,去描摹,而在這個過程中,一筆一絲的把握,你都能感受到流露於這些漢學家眉宇間濃濃的“中國氣”,像孔飛力、像阿列克謝耶夫等等,雖然都典型的歐洲模樣,高高的鼻樑,深深的眼窩,但眼神似乎都是儒家式的、詩意的、平和舒緩的,或許不用多問,透過那雙眼睛,你就能知道他和中國必定有著某種關聯。
對,給漢學家畫像,需要表達這種關聯,需要絲絲入扣,需要超寫實主義的精緻。而回看,整個《紐帶》這部片子,又何嘗不是在“給漢學家畫像”,只是它不是某個具體面龐的描摹,它是速寫,是一個個漢學家所歷中國事的速寫,是一部群星璀璨的漢學研究史的速寫,在蒼茫的史料和現實故事間,擷取一二,然後要處著力!在這場速寫中,或許我們還不是合格的畫家,這個故事那麼大,誰說我們一定抓住了重點呢?努力吧,青年!
雲扎布
2015年3月24日
小心翼翼
2013年春,我剛剛接手《紐帶》日本一集的內容,興高采烈地開始了聯絡中日兩國專家學者的工作。
為《紐帶》日本這一集做歷史顧問的嚴紹璗教授,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所的所長,也是國內研究日本中國學史最權威的學者之一。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先生,大概是最能辯證地分析日本漢學或中國學的。然而,即便是嚴教授這樣專業的學者,至今也難以掌握談及中日關係時的尺度。一方面,他常常會苦澀地和我笑談道,作為中國人研究日本文化,甚至中日文化,即使辯證地為日本說一句好話,都有可能被罵成漢奸。為此,年事已高的他,推掉了很多中日文化研究的項目。而另一方面,在聽到一位中國學者在為近代以來的某位日本中國學家辯解的時候,他又會憤怒地指責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怎麼可以說出這樣的話。
我看得出,他在與我這個青年導演評價日本的時候,是小心翼翼的。
我在查找日本近代以來的漢學家的資料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名叫吉川幸次郎的先生。他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我為之動容。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長子,吉川忠夫先生,也是位著名的漢學家、日本東方學會的前任會長。在聯絡他之前,我是期待萬分的。我期待能夠與他聊聊吉川幸次郎先生,為什麼這麼熱愛中國;期待能夠與他聊聊他本人,為什麼子承父業也開始研究中國;期待他能夠和我在資料書籍里了解到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一樣,能夠讓我為之動容。我通過多方關係,聯絡了日本東方學會,聯絡了他曾任職的京都大學和東洋文庫,終於與他通上了電話。然而,他卻拒絕了我的採訪。幾個回合的電話交流,他總是以“時間不合適,最近比較忙”搪塞我。我試圖以各種各樣的方法與他溝通:改時間,改地點,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等等,最終都沒有成功。
我聽得出,他在與我這個中國記者交流的時候,是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中國學者,小心翼翼的日本學者,讓我這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也開始小心翼翼起來。回想起來,其實《紐帶》日本一集的拍攝與製作過程中,摻雜著很多很多的情緒,涵蓋在不同的故事和人物里。就嚴教授而言,這位不辭辛勞的老先生,最讓我欽佩與感動。再不列舉很多其他的日本學者,亦是對我們彬彬有禮,在拍攝上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然而至今起筆,我很抱歉,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所有人的小心翼翼。我也為小心翼翼的自己而感到難過。
我想,銘記歷史,不是應該要我們在當下活得更美好嗎?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活著?
也許,做《紐帶》的意義,正是想告訴我自己,也許唯有中外文化的不斷交融,才能夠讓我們的後代,不再活得如此小心翼翼吧。
《紐帶》導演 張萁
1.《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2.《中國來信(1716—1735)》
3.《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
4.《中國的猶太人》
5.《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
6.《拉班。掃馬和馬克西行記》
7.《上帝許給的土地——閔明我行記和禮儀之爭》
8.《中國圖說》
9.《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
當代海外漢學名著譯叢
10.《孔子與中國之道》
11.《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
12.《中國的使臣卜彌格》
13.《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
14.《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
15.《(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
16.《軸心時期的儒家倫理》
17.《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
18.《利瑪竇——鳳凰閣》
徠19.《俄羅斯漢學史》
20.《萊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國元素》
21.《馬利遜回憶錄》
22.《衛三畏生平與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