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佑
瞿佑
瞿佑(1347-1433),“佑”一作“祐”,字宗吉,號存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說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元末明初文學家。幼有詩名,為楊維楨所賞。洪武初,自訓導、國子助教官至周王府長史。永樂間,因詩獲罪,謫戍保安十年,遇赦放歸。
作品綺艷,著有傳奇小說《剪燈新話》。生卒詳見《明瞿佑等四詞人生卒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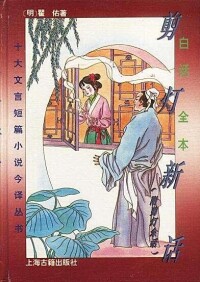
剪燈新話
洪武時期,由貢士薦授仁和訓導,歷任浙江臨安教諭、河南宜陽訓導,后升任周王府長史。永樂年間,因作詩獲罪,謫戍保安(今河北懷柔一帶)十年。洪熙元年(1425)英國公張輔奏請赦還,先在英國公家主持家塾三年,后官復原職,內閣辦事,后歸居故里,以著述度過余年。宣德八年(1433)卒。
瞿佑多才多藝,卻一生流落不遇,抑鬱不得志。他的著作有《存齋詩集》、《聞史管見》《香台集》、《詠物詩》、《存齋遺稿》、《樂府遺音》、《歸田詩話》、《剪燈新話》、《樂全集》等20餘種。
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元統治者的殘酷,社會的動亂他都親身經歷,而對明太祖朱元璋企圖杜絕文人批評時政而興起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如他在《剪燈新話》寫成之後“藏之書笥”,遲遲不敢發表,刊刻時還用“誨淫”“語怪”之類的話加以掩飾,這些都為他的創作奠定了生活和思想的基礎。而在明初嚴峻刑法而前,文人為避免與統治者直接牴牾而招來殺身之禍,便追慕唐人,借寫閨情艷遇、鬼怪神仙的傳奇小說來曲折表達自己的思想。《剪燈新話》就是在此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剪燈新話
《剪燈新話》成就並不算太高,但它和《剪燈余話》、《覓燈因話》等明代傳奇小說,上承唐宋傳奇的餘緒,下開《聊齋志異》的先河,因此在中國文言小說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剪燈新話》的故事情節,有助於談資,為明代擬話本和戲曲提供了許多素材。《金鳳釵記》、《翠翠傳》、《三山福地誌》被凌濛初改寫成話本,編入《二刻拍案驚奇》中;《寄梅記》被周德清改寫成話本,編入《西湖二集》中;金鳳釵記》還被沈璟改編成戲曲《墜釵記》;周朝俊的戲曲《紅梅記》採用了《綠衣人傳》一些情節。
《剪燈新話》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編訂成帙,以抄本流行。永樂十五年,瞿佑以七十五歲高齡在流放地保安重新校訂《剪燈新話》。據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記載,《剪燈新話》共四卷二十一段(即21篇),與今天我們所見的《剪燈新話》卷數篇數相同。本書有成化丁亥(1467)刻本,明末刻本,清乾隆辛亥(1791)刻本,同治辛未(1871)本,均二卷。1917年董康據日本藏本翻刻,《剪燈新話》足本始重歸我國。
《剪燈新話》在中國早已無足本流傳。明高儒《百川書志》所載《剪燈新話》4卷,附錄1卷,篇數還完全。同治年間出版的《剪燈叢話》里所收的《剪燈新話》只有2卷,篇數已不足。但在日本,卻有慶長、元和間所刊活字本,篇數最完備,董康誦芬堂曾據此翻刻。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近人周楞伽(署名周夷)的校注本,共4卷20篇,附錄2篇。附錄中的《寄梅記》,系周楞伽據《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增補。

瞿佑詩詞
瞿佑也善詞。其詞作多是一些描繪景物的作品,有清新氣息。如〔摸魚子〕《蘇堤春曉》在“蘇堤十里籠春曉,山色空濛難認”的背景下,突出“風漸順,忽聽得,鳴榔驚起沙鷗陣”這樣場景,頗有詩情畫意,在明人詞中有一定地位。
瞿佑還仿元遺山《唐詩鼓吹》的體例,編纂了《鼓吹續音》,取宋金元三朝七律1200首,分為12卷。在編纂此書時,他注意到世人過分宗唐貶宋的不妥,認為唐宋二朝詩歌各有所長,是較有見地的看法。但此書並未刊布。
有關瞿佑何時流放塞外的問題,前人對此言之不詳。李慶先生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瞿佑的《樂全稿·樂全詩集》之《至武定橋》一詩中的“自注”:“永樂六年四月,進周府表至京,拘留錦衣衛。自汴梁起取家小十二口至此,蒙撥房屋居住,至今二十一年矣”,從而認定為是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四月,可以信從。
至於瞿佑被貶的緣由,事主諱莫如深,只是說:“向以洪熙乙己冬,蒙太師英國張公奏請,自關外召還,即留樂西府,今又三載,又蒙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奏准,恩賜年老還鄉。”“自罹罪謫獨處困厄中,與妻即睽隔逾十寒暑矣。尚書趙公,指揮高公,太守馮公,長司鄭公及諸鄰友憐其窮苦獨居,皆勸以納妾。”言辭之間雖充滿怨氣,但對“罹罪”的真相卻又不置一辭。而前人對此說法不一,較有代表性的是如下兩種說法。一為郎瑛的《七修類稿》所云:“藩屏有過,先生以輔導失職,坐系錦衣衛。”一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所云:“以詩禍編管保安。”此外還有其它一些說法,與此大同小異而已。其實,這兩種說法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瞿佑之《歸田詩話》下卷“和獄中詩”條云:“永樂間,予閉錦衣衛獄,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同處囹圄中。子昂每誦東坡《系御史台獄》二詩索予和焉。予在困吝中,辭之不獲,勉為用韻作二首。”其中有兩句詩說,“一落危途又幾春,百狀交集未亡身”,反映了瞿佑在獄中的真實心境。這段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一句。瞿佑在此明確無誤地點明了自己罹罪的緣由是“詩禍”。倘我們聯想到明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的現實政治環境,瞿佑由詩而惹禍的命運,似乎也並不難以理解。問題在於:瞿佑是如何遭致“詩禍”的呢?有人懷疑他有反叛朝廷之意,似乎不確,從上引瞿佑的“自注”來看,他在“詔獄”期間,雖曾失去人身自由,但仍能“自汴梁起取家小十二口至此”,還“蒙撥房屋居住”,其物質待遇還算可以,與反叛朝廷的“政治犯”有顯著的判別。他僅僅是因為“輔導失職”而被“坐系錦衣衛”的。而這“輔導失職”,實也和周王朱橚有關。
張益《詠物新題詩序》得知,瞿佑在青年時期(元末明初),因明經而被薦為訓導,曾在仁和、臨安、宜陽等地任職。大約在洪武十一年(1378)他三十二歲時,在仁和縣結識了周王朱橚以後,兩人交往比較密切。如朱橚編有《袖珍方》四卷,專錄民間治病藥方,而瞿佑也著有《俗事方》一書,專事輯錄“民家必備”及“治生”之良方。此書今存,入藏日本東洋文庫。據明正德刊本《袖珍方》之朱《序》云:“予當弱冠之年,每念醫藥可以救夭傷之命,嘗令集《保生余錄》、《普濟》等方。”此“弱冠之年”,恰系他在杭州時和瞿佑相交之期。值得注意的是《千頃堂書目》卷十四著錄了李恆的《袖珍方》四卷,其注云:“恆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周府良醫,奉憲王(引者按:誤,應為“定王”)命集。恆,永樂間致仕,王親賦詩以餞,命長史瞿佑序其事。”可見瞿佑和朱橚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然而,這位周王朱橚不是個安分守己之人。據《明太宗(永樂)實錄》記載,他曾因編《元宮詞》忤觸皇旨,並且因護衛“拘軍民商旅之舟裝運王府米麥”等事得罪權貴。《明太宗實錄》卷七十八“永樂六年四月”條下說:“戊子,欽天監奏木星犯諸王星,上曰:‘前月木星犯諸王星,今復然。’天道不爽。遂悉賜諸王書,俾警省。有告言肅王木英聽百戶劉成言,輯罪平源衛軍者,上曰:‘此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敕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於王矣。故讒佞,德之蠢也,林無蟲有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出於家屬利益的考慮,永樂皇帝在表面上雖然維護了周王的威信,但他心裡一定對朱極其不滿:“今過則皆於王矣。”為此,他對當時的皇室以及諸王之側作了一次嚴厲的整肅。根據明代的法律,凡諸王有失,其過則在長史。其時,以長史之職伺奉在周王朱橚左右的瞿佑以“輔導失職”之罪,而趁其“進周府表至京”之際,把他“拘留錦衣衛”,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師師檀板》
千金一曲擅歌場,曾把新腔動帝王。
老大可憐人事改,縷衣檀板過湖湘。
《屠蘇酒》
紫府仙人授寶方,新正先許少年嘗。
八神奉命調金鼎,一氣回春滿絳囊。
金液夜流千尺井,春風曉入九霞觴。
便將鳳歷從頭數,日日持杯訪醉鄉。
《寄生草》
要路閑門兩不過,生來唯戀舊枝柯。
似嫌樹底泥塗滑,應愛梢頭雨露多。
冉冉欲遮螻蟻穴,萋萋得近風凰窠。
教坊樂府多新制,傳得佳名入艷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