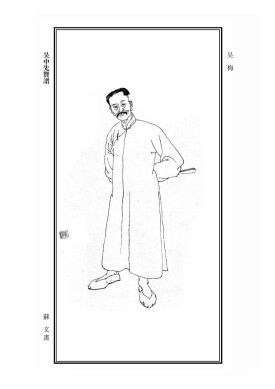共找到9條詞條名為吳梅的結果 展開
吳梅
戲曲理論家、教育家
吳梅(1884年—1939年),字瞿安,號霜厓,江蘇長洲(今蘇州)人。現代戲曲理論家和教育家,詩詞曲作家。度曲譜曲皆極為精通,對近代戲曲史有很深入的研究。
吳梅弟子很多,南京大學以研究戲曲聞名的諸位先生大抵都是吳梅門下後學。1922年秋至1927年春,在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后改為中央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任教五年。1928年秋至1932年春,1932年秋至1937年秋在中央大學任教8年半。培養了大量學有所成的戲曲研究家和教育家。吳梅在文學上有多方面成就,在戲曲創作、研究與教學方面成就尤為突出,被譽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學大師”。
吳梅一生致力於戲曲及其他聲律研究和教學。主要著作有《顧曲麈談》、《
曲學通論》、《中國戲曲概論》、《元劇研究》、《南北詞譜》等。又作有傳奇、雜劇十二種。培養了大量學有所成的戲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吳梅對古典詩、文、詞、曲研究精深,作有《霜崖詩錄》、《霜崖曲錄》、《霜崖詞錄》行世。又長於制曲、譜曲、度曲、演曲。作《風洞山》、《霜崖三劇》等傳奇、雜劇十餘種。老先生終生執教,自1905年至1916年,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堂、存古學堂、南京第四師範、上海民立中學任教。1917年至1937年間,在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台灣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光華大學、金陵大學任教授。他精通崑曲,他不但整理了唐宋以來的不少優秀劇目,還創作了不少崑曲,並且是第一個把崑曲這一民間藝術帶入大學的教授,在北京大學文學系教崑曲和戲劇。他的弟子既有名教授大作家又有梨園界的大師,如朱自清、田漢、鄭振鐸、齊燕銘,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俞振飛,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東京大學校長也是吳梅的弟子。可謂桃李滿天下,目前台灣的崑曲名家,都是吳梅的第二代弟子。1993年,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等在吳梅故里蘇州召開了吳梅誕生100周年學術討論會,海內外特別是寶島台灣,來了不少專家、學者。

《吳梅評傳》
吳梅先生在文學上有多方面成就,在戲曲創作、研究與教學方面成就尤為突出,被譽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學大師”(王玉璋《霜厓先生在曲學上之創見》)。先生終身執教,桃李滿園。

吳梅著述
創作方面,先生在十六歲時,就有傳奇《血花飛》之作,以紀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間,共創作十四個劇本,現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壽誕時自選的《霜崖三劇》為代表,曲律詞采俱工,案頭場上,兩擅其美,人物鮮明而情節曲折,達到了那一時代的最高境界。傳統戲曲本身就是一種綜合藝術,若非具有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多方面的較高修養,是不可能取得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顧曲麈談》、《曲學通論》、《南北詞簡譜》等專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藝術實踐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制、譜、唱、演的藝術規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國戲曲概論》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國戲曲通史;《元劇研究》和《曲海目疏證》對劇作家與作品的考證,也有承前啟後之功;《霜崖曲話》、《奢摩他室曲話》和《奢摩他室曲旨》等採取傳統的曲話形式,廣泛評述散曲、劇曲的形式與內容,既為作者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也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材料。吳梅先生在詞學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詣。朱祖謀先生曾四校《夢窗詞》,而吳梅先生重讀《夢窗詞》,還能有新的發現。他的專著《詞學通論》,寓史於論,史論結合,從格律到作法,多所創見。

吳梅著述
吳梅先生的詩,在生前寫定為《霜崖詩錄》四卷,以編年體存詩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數量較詞、曲尤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經歷、過從交往,以及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詩作始於1898年,終於1938年,對於四十年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洪憲復辟、軍閥混戰到日寇侵華、抗戰軍興,都有如實的反映,表現出詩人強烈的愛國精神;詠史懷人、評書讀畫之作,也無不寄寓真情實學;其七古風骨遒勁,歌行開闔流轉,絕句輕倩流麗,律詩工於對仗,各有特色。詩人的自我評價是:“不開風氣,不依門戶。獨往獨來,匪今匪古。”“不開風氣”有自知之貴,因為先生清醒地認識到,“詩文詞曲,頗難兼擅”,他在曲學上用力至深,詩作上再想開一時風氣是不現實的;但由於堅持了“不依門戶”,所以能達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吳梅先生的詞,大部分錄入《霜崖詞錄》。存詞一百三十七首。
吳梅先生的曲,有《霜崖曲錄》二卷,為先生高足盧前在1929年編次,后又有增補,現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數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為先生認識到“欲明曲理,須先唱曲”,曾從名師學唱,能夠邊唱邊寫,所以才情與格律有機統一,達到格律精嚴而才情橫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來散曲日見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異峰突起,並影響後學,釀成風氣,致時人有散曲“中興”之望。先生還為許多傳奇雜劇打下了聲情並茂、宜唱美聽的曲譜,使一些案頭名劇得以登上舞台,重煥青春。這也因為先生有唱曲的功底。魏良輔曾總結唱曲經驗說:“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聽過吳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為他是得到這份真傳的。

吳梅著述
桃李滿園

學者吳梅
吳梅先生培養出來的學生,對於老師的學業各有繼承,出現過一大批一流學者。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尚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訥、唐圭璋、王煥鑣、錢紹箕、王起、汪經昌、趙萬里、常任俠、游壽、潘承弼、陸維釗、胡士瑩等;其中約一半沒有再從事曲學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領域裡取得了重大成就。從事曲學研究的幾位,為世所重的,則只是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他們的創作卻默默無聞。

吳梅著述
雜劇:《軒亭秋》、《暖香樓》、《湘真閣》、《落茵記》、《雙淚碑》、《無價寶》、《惆悵爨》(內含短劇四種)七種。
戲曲論著:《中國戲曲概論》、《顧曲麈談》、《詞餘講義》、《南北詞簡譜》、《元劇研究ABC》等及數量可觀的曲話、序跋、散記、筆記等曲學論著,並輯有《奢摩他室曲叢》初、二集。其他著作有《霜厓詩錄》四卷、《霜厓詞錄》一卷、《遼金元文學史》等,并行於世。又有《文錄》二卷,未刊行。其散曲作品輯入《霜厓曲錄》二卷及《霜厓讀畫錄》一卷中。王衛民編有《吳梅戲曲論文集》,1983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吳梅全集》有四卷八冊三百餘萬字,吳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統地結為一集。書後附有王衛民先生所編《吳梅年譜》。其中且有《瞿安日記》二巨冊。
同時出版的還有王衛民先生重行修訂的《吳梅評傳》。同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梅先生的再傳弟子吳新雷先生主編的《中國崑劇大詞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就是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繼被發掘而紅極一時之際,吳梅先生的曲學成就卻依然無人問津,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就時中國的崑劇已經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吳梅先生獨步一時的曲學理論,成了屠龍之技。
這其中的原因,說複雜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簡而言之,大約有兩點。
其一:二十世紀初,應運而生的新文學,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為主流。這本應是好事,使中國文學的園地大為豐富;遺憾的是,由於某些人有意無意的努力,將思想以至政治領域的新舊之爭,推延到文學領域之中,而且只論形式,不論內容,更不論藝術,一入舊式,即在掃蕩之列。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葉為止,“同光體”已不入法眼,遑論其餘。
實則在大動蕩、大變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詩文詞曲,無論新體還是舊體,都不乏佳作,都曾達到一個不容忽視的高潮。作為南社的早期成員、一貫關心國事的吳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人學者,即使不能寫作舊體詩詞,欣賞舊體詩詞的人應當不會比欣賞新詩的人少。所以當時學人對於吳梅先生的成就才會有那樣高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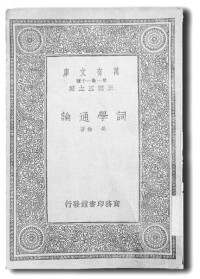
吳梅著述
吳門弟子中能制曲的有一位孫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後來在西安教書,霍松林先生曾從他受教。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印過一部《壺春樂府》,恐怕就更沒有什麼人知道了。此書三卷,卷上、卷中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雜劇,曾得盧前的盛讚。這或許竟是當代人崑曲創作的尾聲了。
崑劇藝術的後繼無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虛無主義的一度橫行,全民族的傳統文化修養的急劇下降,應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吳梅先生在《百嘉室遺囑》中,曾專門談到後輩的教育問題:“近日小學課程,殊不能滿人意。吾意身為中國人,經書不可不讀。每日課餘,宜別請一師,專授經書。大約《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左傳》,必須熟誦。既入中學后,則各史精華,亦宜摘讀;或主誦《群書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刪節處間有乖異,不必讀也。十六歲后,應略講經史源流。”這自是治國學者的經驗之談,但在近半個世紀中,如果有誰重彈

吳梅早期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吳梅先生對於新詩,就並不排斥。當徐志摩去世時,他曾代穆藕初作輓聯:“行路本來難,況上青天,孤注全身輕一擲;作詩在通俗,雅近白傅,別裁偽體倘千秋。”評價是相當高的,他對此聯也很滿意,“自覺頗工”,因此記入日記。
其實,人文文化的領域是一個累積的領域,一種作品對於另一種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沒有取代的可能。各人頭上一方天,並存共榮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將舊體文學的創作成果抹殺,才能顯示出新文學的成績,那這成績也就實在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