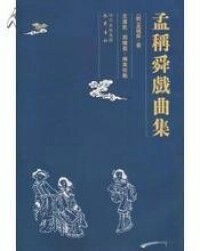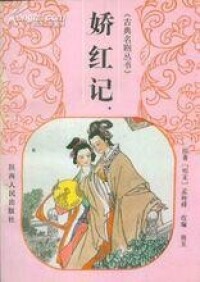孟稱舜
明朝劇作家
孟稱舜(約1599年-1684年),字子塞,又作子若或子適,號小蓬萊卧雲子、花嶼仙史,是明清之際的戲曲作家和戲曲理論家,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他被認為是戲曲“臨川派”繼湯顯祖之後最重要的作家,倪元璐稱他為“我朝填辭第一手”。他編撰的《古今名劇合選》,是公認元明雜劇的一部重要選集,收錄元明雜劇五十六種(包括他自己的《眼兒媚》、《桃源三訪》、《花前一笑》與《殘唐再創》四種),按照婉麗、豪放不同風格,分為《柳枝集》、《酹江集》,並詳加評點,有眉批六百零二條,旁批四十七條,內容深刻,見解精湛,是古典曲論的重要典籍之一。
孟稱舜撰寫的雜劇和傳奇有十種,現存八種,成就較高者有雜劇《桃源三訪》(亦名《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裡逃生》、《殘唐再創》及傳奇《節義鴛鴦冢嬌紅記》、《二胥記》、《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等。其中《嬌紅記》被評為“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
明末清初,描述愛情故事的戲劇《嬌紅記》的問世,奠定了明末清初時劇作家孟稱舜在戲劇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人認為,孟稱舜是繼元代關漢卿之後,清代洪升之前,在明代中國戲劇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崇禎年間,孟稱舜順利考上當地的秀才,但以後仕途坎坷,屢試不第。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孟稱舜加入了當時研究文學的“楓社”,成了臨川湯顯祖“玉茗堂派”(或“臨川派”)的重要成員。
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孟稱舜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撰寫成戲劇《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後來又更名為《貞文記》。作品一問世,當時受到轟動,後世人們把它和《西廂記》、《追魂記》、《嬌紅記》一起,全稱為“四美”劇本
《貞文記》是圍繞張玉娘和沈佺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展開的,其中的主要情節縮寫為以下內容:
南宋末年,浙江松陽縣城有一官員張懋,夫人臨盤,娩出一個女嬰。張懋和夫人劉氏均出身於官宦人家,系書香門第。張父為女嬰取名玉娘,字若瓊。
在此期間,松陽大戶人家沈元,也在同年同月同日娩出一個男嬰,叫沈佺。他是北宋狀元沈晦嫡系七世孫,與張玉娘是表兄表妹。張、沈兩家交誼甚厚,來往密切,雙方父母為他倆訂下了婚約。
小時候,張玉娘與沈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十幾年後,女大十八變,張玉娘不僅生得十分漂亮,並且能文善詩。沈佺風流倜儻,才華出眾。兩人常常一起遊玩、賦詩、作畫。
沈氏後來家道中落,張父悔婚,但張玉娘矢誓終身與沈佺相愛。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沈佺隨父北上京城赴試,幸運地考中了榜眼,成了松陽歷史上唯一的榜眼。
可是,命運並沒有使年青人一帆風順,不久,厄運突然降臨,沈佺由於勞累過度,不幸染病不起。張玉娘聞訊后十分擔憂,寄了《山之高》詩一首,安慰沈佺,其中有:“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
有情人難成眷屬,幾天後,沈佺病重而死,年僅二十二歲。
噩耗傳來,玉娘痛不欲生,滿腔悲傷化作詩句流露在紙上,其中就有悼亡詩《哭沈生》:“中路憐長別,無因復見聞。願將今日意,化作陽台雲。”
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玉娘父母欲替她另擇佳偶,找了一個有權有勢的公子王權。沈佺雖死,但玉娘不能忘記這段感情,所以對這門婚事堅決不從命。為了寄託哀思,玉娘把全部的精力致力於詩詞創作。

孟稱舜
張玉娘在短暫的一生中創作詩117首,詞16闋。其詩清麗上口,其詞每闋皆佳,後人把它收集在專著《蘭雪集》里。蘭即蘭花,天下第一香。雪即白雪,潔白無瑕。
孟稱舜為張玉娘撰寫了祭文《貞文祠記》。他又賦《鸚鵡墓》詩一首:“青雲夜載美人去,鸚鵡朝來墮翠樓。鸚鵡一去春寂寂,荒城千載雲悠悠。香魂欲問梨花月,幽思空餘芳杜洲。蘭雪有辭君莫唱,夕陽煙樹不勝愁。”
《嬌紅記》取材於北宋宣和年間一個真實的故事,並根據元代宋梅洞小說《嬌紅傳》改編。由明朝孟稱舜所寫,描述王嬌娘和書生申純的愛情因不被准許而雙雙殉情的悲劇。《嬌紅記》所表現的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主題,在元明間的戲曲中曾被反覆表現過。但是,《嬌紅記》沒有停留在它以前的愛情作品已達到的高度,無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閃爍著新的思想的光輝,被列為“中國古典十大悲劇”之一。
孟氏劇作全由陳洪綬評點,加上亦由陳氏點評的《節義鴛鴦冢嬌紅記》,陳洪綬堪稱目前所知點評孟氏劇作最多、用力最勤的批評家。陳氏的評語,既有宏觀的藝術特色、價值取向的剖析,更有微觀的鑄詞冶句、葉韻入律、傳情寫態、情節設置等的點評,如其評《桃源三訪》:“《桃源》諸劇舊有刻本,盛傳於世。評者皆謂當與(王)實甫、(關)漢卿並駕。此本齣子塞手自改,較視前本更為精當。與強改王維舊畫圖者自不同也”;評《嬌紅記》:“若鑄辭冶句,超凡入聖,而韻葉宮商,語含金石。較湯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進一格”、“此曲之妙,徹首徹尾一縷空描而幽酸秀艷,使讀者無不移情”;評《泣賦眼兒媚》:“蘊藉旖旎,綽有餘致,而凄清悲怨處,尤足逗人幽淚”等等,不一而足。《節義鴛鴦冢嬌紅記》是孟稱舜最著名的傳奇,曲苑有“臨川讓粹,宛陵讓才,松陵讓律”的美譽。
與祁彪佳、馬權奇等曲評家一樣,陳洪綬對《嬌紅記》極為讚賞,不但為其作了四幅精美絕倫的卷首插圖,更詳加評點,親作長序。在序言中,陳洪綬表達了對孟稱舜——也可以說是對當時曲作家們——的深刻理解:孟稱舜才華過人而以道氣自持,每每被“鄉里小兒”視為迂生腐儒,實則情深一往,他所追求的至情至性,“問諸當世之男子而不得,則以問之婦人女子;問諸當世之婦人女子而不得,則以問之天荒地老古今上下之人”。或有“老先生”見到孟氏所作的戲曲,呵斥其為“不正之書”,陳洪綬為他辯駁:“今有人焉聚徒講學,庄言正論,禁民為非,人無不笑且詆也。伶人獻俳,喜歡悲啼,使人之性情頓易,善者無不勸,而不善者無不怒。是百道學先生之訓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這又是對地位低下的伶人們的肯定與認同。陳洪綬一生醇酒婦人,放浪形骸,但其詩文卻多有沉鬱的家國之痛,至情至性,一往情深,他與孟稱舜性情相近,所以相知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