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是德國哈貝馬斯用語。指隱含在人類言語結構中並由所有能言談者共享的理性。
傳統理性觀通過我們關於對象的知識範式表現出來,而交往理性則在主體間相互理解的範式中被表達;這些主體能夠說話和行動,處於對一個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它是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理性,關注可靠主張的主體間性。它的有效性領域相應於人類言語的領域。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理性觀是交往行為的基礎。他稱交往行為代替策略行為的過程為“交往理性化”。
哈貝馬斯認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動的核心,而語言佔據特別重要的地位。交往行為是一種“主體—主體”遵循有效性規範,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而發生的交互性行為,其目的是達到主體間的理解和一致,並由此保持的社會一體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簡言之,勞動偏重的是人與自然的征服與順從的關係,交往偏重的是人與人的理解和取信的關係。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在現時代條件下,應該被賦予更為重要的價值表示和地位,因為勞動雖然也包含著人與人的關係,但其主導取向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以生產力的提高為尺度的。而就人自身的發展來說,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溝通是具有更為深遠和高尚的人本主義價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類是社會進步的方向。但是這種勞動與交往的總體合理關係並未建立。由於科技飛速發展,勞動的“合理化”不僅實現,而且在無以復加的迎合“科技意識形態”的需要。但是這種合理化脫離了主體間的合理關係,把人的關係降級為物的關係,使人無可挽回的淪為工具,屈從於技術社會的統治之下。勞動的工具理性結構壓倒並同化了交往的價值理性結構,使人與人的交往完全成為工具理性內部的一絲“默契”。因而,要想避免技術社會對人的異化,就要建立主體間的理解與溝通,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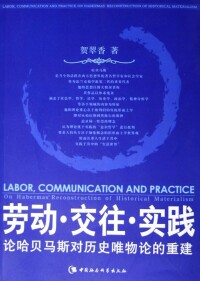
參考書目
哈貝馬斯從對語言的具體運用入手,指出目的論行動、規範行動、戲劇行動這三種不同語言構思的片面性,“第一種,把交往看成僅僅為了實現自己目的的人的間接理解;第二種,把交往看成僅僅為了體現已經存在的規範性的認可的人的爭取意見一致的行動;第三種,把交往看成吸引觀眾的自我表演。在這裡,往往只把語言的一種職能論題化了。”哈貝馬斯強調,應該吸取現當代思想家米德、維特根斯坦、奧斯丁和伽達默爾等的思想成果,“同時注意到語言的所有職能”,以有效地避免“語言往往是各按不同的角度被片面構思”情形。哈貝馬斯強調說:“對於交往行動模式來說,語言只有按照實用主義的觀點才是重要的,發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則下運用句子時,與世界發生了關係,而且這不僅象在目的論的行動,規範指導下的行動,或者戲劇行動中是直接的,而且也以一種反思的方式發生關係……。發言者把這三種形式的世界觀統一為一個體系”。在交往行動模式中,行動者把這個統一的體系作為解釋範圍的前提,在這個體系範圍內他們才能達到理解的目的。行動者的行動是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把語言作為參與者與世界發生關係”,從而相互提出可以接受也可以駁斥,以實現相互的理解與合作,並有效地表達自己,而“不再直接地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或主觀世界上的事物發生關係”,以語言為媒體的交往行動其本身就是那些尋求意見一致,並衡量真實性,正確性,確實性,一方面衡量語言行動之間一致關係,另一方面研究行動者與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這三種關係。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語言基礎之上確立起來的,這就使他擺脫了意識哲學由於僅限於概念、推論的抽象僵硬、獨白,而帶來的思想者與作為思想對象的主觀世界和作為思想對象的客觀世界以及思想者之間的對立,從而走出了意識哲學固有的對象性思維的陰影。而對於語用學的堅持與對語義學的限制,又使得他得以避免當代語言哲學中所表現出的某種唯名論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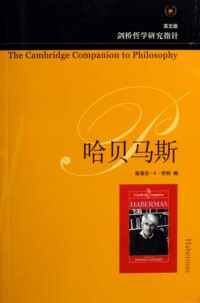
關於哈貝馬斯理論的書
工具理性體現了交往者對於客觀世界(而不是社會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種態度。把這種態度從其他態度中分化出來,有助於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人們就各自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經驗、知識和計劃進行溝通,也是整個交往行動的重要內容。所以,工具理性並不內在地就是一種壓制人的東西、破壞人與自然之間和諧關係的東西。
作為交往理性的一個環節,它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同時又受到理性的其他環節的制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出了毛病,並不在於工具理性本身,而在於工具理性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工具理性的發展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成果,但它逐漸脫離了理性——也就是交往理性的其它環節,獨立出來,越來越膨脹,甚至反過來壓制理性的其它環節,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支配地位。要克服這種局面,並不要求全盤放棄工具理性,而是要讓它回到自己的合法範圍內——用它來處理人和自然的關係、來提高社會行動的效率。但是,在處理這些工具性、技術性問題的時候,切不可忘記我們還有其它問題要解決,還有其它價值要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