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當代詩人,代表作《在遠方》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男,當代詩人,出生於北京(北平)一個職員家庭。1945年夏天,從小學進入中學。
邵燕祥的處女作是1946年4月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篇雜文《由口舌說起》,批評了習於飛短流長的社會現象。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記者,《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
著有詩集《到遠方去》《在遠方》《遲開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2020年8月1日,邵燕祥逝世,享年87歲。

邵燕祥活動照
1949年建國后,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記者。
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
1978年至1993年在《詩刊》工作,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曾任中國作協第三、第四屆理事,第四屆主席團委員。著有詩集《到遠方去》《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遲開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邵燕祥生活照
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終止了在大學一年級的學業,到北京電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詩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詩集《到遠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寫的抒情詩,其中一些表現了年輕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個性色彩的詩,為他贏得了讀者的最初的聲譽。
20世紀五十年代即為有影響力的青年詩人,後轉向散文,雜感寫作。但是不久,由於他的詩和雜文中觸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會現象,受到批評和鬥爭。
直到1978年,他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達20年之久。其間,在1962年春有些解凍的跡象,他得以寫了一個劇本,發表了幾首詩和一篇小說;這年秋天,那篇寫親子之情而不涉及階級鬥爭的小說又遭到公開抨擊。他在1979年初恢復政治名譽。
從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獻給歷史的情歌》《在遠方》《如花怒放》《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等八種詩集和詩選,還有詩評集《贈給十八歲的詩人》《晨昏隨筆》,雜文集《蜜和刺》 《憂樂百篇》。從1980年前後發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雜文開始,又寫了大量的雜文,批評各種社會弊病。現為中國作協理事和主席團委員,中國筆會中心會員。
《憂樂百篇》。從1980年前後發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雜文開始,又寫了大量的雜文,批評各種社會弊病。現為中國作協理事和主席團委員,中國筆會中心會員。

邵燕祥著作
2020年8月1日,邵燕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 名稱 |
| 《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 |
| 《遲開的花》 |
| 《歌唱北京城》 |
《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
| 名稱 |
| 《教科書外看歷史》 |
| 《大題小做集》 |
| 《熱話冷說集》 |
| 《邵燕祥文抄》 |
| 名稱 |
| 《沉船》 |
| 《人生敗筆》 |
|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
雲南驛懷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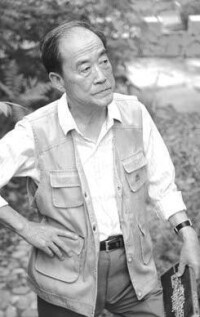
邵燕祥
沉默的芭蕉
芭蕉/你為什麼沉默/仁立在我窗前/枝葉離披/神態矜持而淡漠從前你不是這樣的/在李清照的中庭/在曹雪芹的院落/你舒捲有餘情/綠蠟上晴光如潑近黃昏,風雨乍起/敲打著竹籬瓦舍/有約不來/誰與我相伴/一直到酒酣耳熱呵,沉默的芭蕉/要談心請拿我當朋友/要爭論請拿我當對手/在這邊鄉風雨夜/打破費爾巴哈式的寂寞芭蕉啊我的朋友/你終於開口/款款地把幽思陳說/燈火也眨著眼睛/一邊聽,一邊思索芭蕉,芭蕉/且讓我暖了擱冷的酒/憑窗斟給你喝/夜雨不停話不斷/孤獨,不是生活
生命
只有不化的積雪/沒有不散的浮雲那千秋的積雪/在雪線之上凍結人說石林更長久/出現在海水乾涸的時候時間過去了二億七千萬年/從來一絲也沒有動彈多少皺紋是風雨所侵凌/不露一絲哀樂的表情從來不吃人間的煙火/滄桑冷暖,一句話也不說與其化為石林而不朽/不如化為一朵浪花隨著大海翻騰放聲隨著海浪喧嘩/投身陽光向長天蒸發化為雲,化為雨/化為不滅的種子滲進大地
無題
還是那個太陽,忙碌的太陽!/一天二十四小時照著地球——/不許鳥兒亂啄,這青青的蘋果/慢慢轉紅了,在初秋;/在初秋的陽光下,我發現大地走向成熟,/發現了自己,發現了眾多的朋友/……/枝頭懸掛著半熟的蘋果,/有什麼東西成熟在我心頭?還是那支歌,還是那歌喉,/閃光的歌聲像一匹閃光的薄綢——/繚繞著莊嚴的豎琴,柔韌的手指,/鋼琴、電吉他,錦瑟與箜篌;/歌聲流過,像日光和月光/流過我的心,你的明眸,/它曾觸亮我憂愁中的歡樂,/讓它融化你歡樂中的憂愁。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雙手,/心和心相印,手與手相求——/我的心迷戀著,迷戀著生活,/我的手召喚著,召喚著朋友;/生活啊,朋友啊,再不要背叛我!/恩情還沒報答,愛也還沒愛夠!/在天空,就一起歌唱著飛翔!歌唱!/在大地,就一起自由地奔走!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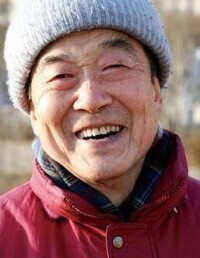
邵燕祥生活照
鮮明的啟蒙理性色彩
邵燕祥崇尚真理和理性。他說:“雜文的靈魂是真理的力量,邏輯的力量。”(《為陳小川雜文集作的序》)。在1980年所寫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人是有尾巴的嗎?》等多篇屬於這一題旨的雜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認為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好皇帝”再世,“隨之而來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義”,即便是那樣的“好皇帝”也整過良臣的黑材料,皇權的“民主作風”畢竟是大大有限的。因此不要在“好皇帝”和“壞皇帝”之間做選擇,而是要在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之間做選擇。《人是有尾巴的嗎?》一文中,首先,作者把“翹尾巴”、“夾尾巴”以及“脫了褲子割尾巴”同髒話、同人格侮辱聯繫起來,因為只有鳥獸蟲魚才有尾巴;繼而,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它的本質:“那動輒指責別人‘翹尾巴’者,正是自認為我翹則可,你翹則不可;動輒訓斥別人‘夾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翹’不‘夾’的特權;動輒勒令別人‘割尾巴’……其實可能恰恰忽視了自己拖著一條長長的封建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尾巴。”這與在《》中說過一句話:“現代的專制者喜歡割知識分子的‘尾巴’”不謀而合。作者堅強、新銳的理性和真正雜文家的素養使其作品一語中的而又老辣尖刻,至少在1980年那個時刻具有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邵燕祥的雜文就具有這種“將蒙蔽豁開,便見了光明”的特徵。《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是將“好皇帝”蒙蔽下的黑暗照亮了。又如,在《吳江老矣,猶著新書》中,邵燕祥借吳江的《社會主義前途與馬克思主義的命運》一書,照亮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的誤區。過去,我們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的基本點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然而,恩格斯在回答‘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什麼’時,突出地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這樣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吳江據此說,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它的‘基本思想’集中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這一點上。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首先表現在每個人獲得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如果說話的自由都沒有了,那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這一啟蒙,使我們重新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光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邵燕祥的雜文還豁開了當代社會兩個被蒙蔽的重要盲點或暗點:一是駐馬店和在1975年遭遇的洪水之災(因為一直秘而不宣,故為盲點),二是遂平縣因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導致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因為諉過於天以掩蓋人禍而成盲點)。邵燕祥的雜文中說,1975年,洪水來臨之際,“與沙河鎮僅一河之隔的遂平縣文成公社完全沒有得到警報……全公社36000人中有半數遭難,許多人家絕戶”,“僅一小時洪水就衝進45公裡外的遂平縣,城中40萬人半數漂在水中,一些人被中途的電線鐵絲勒死,一些人被沖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廣鐵路高坡時墜入漩渦淹死。”這是邵氏根據趙園《記憶洪水》一文中所引院士《千秋功罪話水壩》(清華大學、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里的文字。邵燕祥有感於遂平縣的災難,又想到這個縣“在1958年曾經是各級幹部放農業高產衛星最早的地方,也是因謊報產量高額徵糧以致口糧不足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9年、1960年、1961年過去習稱‘三年困難時期’,諉過於天以掩蓋人禍,全國餓死三四千萬其說不一……”“怨天怨地,其實老天是冤枉的,據查那三年的氣象記錄,就全國總體來說,是屬於風調雨順的”。當然,這裡的“豁蒙”或啟蒙,並非邵氏一人之功,其頭功還得歸於潘家錚院士。

詩人邵燕祥
邵燕祥的啟蒙理性不是單純從思想史方面做文章,而是從現實出發,以針砭時弊為目的。譬如對皇權意識的批判。在我國當下皇權意識仍然根深蒂固,不僅電影、電視題材一步步向皇家靠攏,把歷代皇帝尤其清代各帝一再競相美化,而且,萬眾矚目的城市景觀、賓館同樣競相以皇宮、皇后、公主等皇室人物命名,甚至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也動輒出自御廚和宮廷,連藥物也要美其名曰“宮廷秘方”。作者還看到了現實中“地方與基層的‘土皇帝’的產生”,與愚昧的“臣性”有關,所以他寫出了《“土皇帝”也不能要》之後,又在1987年寫出了《臣性》。邵先生在《臣性》中痛心疾首地說,“臣性悠悠,不絕如縷”,“有愚昧的地方,就有臣性,就有人要過皇帝癮,也還真有‘臣民’匍匐捧場呢。嗚呼!”。有一種說法是“雜文不說身邊事”,“魯迅雜文中直接針對現實說話的篇什也不是很多”,那麼,臣性,皇權意識不就是身邊事嗎?魯迅的《我之節烈觀》《春末閑談》《看鏡有感》和《文學與出汗》,哪一篇不是針對現實說話的?要雜文不說身邊事,也許是不讓作者被現實所傷,惟其如此,才顯示出邵燕祥秉承魯迅直面現實的戰鬥傳統,對於身邊的病態,容不得冷眼旁觀,他必然挾筆如橫刀,縱橫馳騁地和他們搏而戰之。惟其如此,才映現出繼魯迅之後,仍然不乏“刑天舞干戚”的鬥士風采。其三,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識。邵燕祥那把啟蒙理性地解剖刀並非一味向著外界,向著他人,他也以同樣嚴格的尺度解剖著自己。在這方面,1988年寫的《夢醒后的啟蒙》可以視為自我啟蒙的宣言。他寫道:“誰啟蒙?啟誰的蒙?所有意識到啟蒙的意義的人,都既是啟蒙者,又是被啟蒙者。不是少數自稱‘精英’的人充當啟蒙說教者,連這些自稱‘精英’其實也同整個知識界一樣身上帶著老傳統和新傳統深深淺淺的戳記的人們,也要跟‘非精英’們一起接受時代的啟蒙。”邵燕祥還在一個雜文集的附記里也說過類似的話,即雜文作者如果不能學習魯迅那種在解剖社會人事的同時也時時解剖自己,而只一味當“手電筒”——光照亮別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畫腳地進行說教,恐怕寫雜文將失去讀者,做人也將失去朋友的。自我解剖是源於不以自己為完人的清醒認識。在邵氏的雜文中,這種自我解剖是隨處可見的。多年以前評胡風的詩,他不忘記寫進“我也隨聲附和地寫過聲討的詩,傷害過曾經帶我上路的人”(《氣勢》),表示了對曾經從惡的懺悔;近年來評高爾泰的《尋找家園》,說自己當年成了右派“減少了我害人的機會”,“如果不成異類,依我的社會存在和思想狀況,則我會積極響應所有號召……縱橫衝殺,傷害好人……”把自己擺進去,並且無情地向讀者作解剖,這是自魯迅以來,中國現代雜文最為寶貴的傳統,也是邵燕祥著意要繼承的。他繼承的實際上也就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自己本位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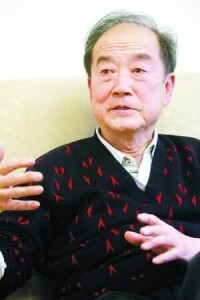
邵燕祥個人照
邵燕祥祖籍浙江蕭山,出生於北京,一九四七年讀中學時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一直生活在北京,至今可以算是“老北京”了。在學生時代就發表詩文作品,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首長詩《歌唱北京城》,就讓人知道了“邵燕祥”的名字。一九五一年,他出版了以這首詩題名的詩集,所以在廣大讀者心目中,邵燕祥這個名字總是和詩聯繫在一起的。
祖丁遠是一向欽佩燕祥的,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祖丁遠們雖然熟識和相知幾十年了,但真正的暢談也只有兩次。一次是十幾年前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北京,與燕祥電話約定去他家,是第一次採訪性的長談。這天下午,祖丁遠們談了兩個小時,那次祖丁遠們談話的面比較廣泛,從當時的社會現象、人情世故等,談到他的詩歌寫作。他介紹了即將在他家鄉浙江的《江南》文學刊物上發表關於“反右”運動中人生實錄長詩《沉船》的背景和寫作動機,還談到他除了寫雜文外,還在整理詩稿,談到一九八○年出版的詩集《獻給歷史的情歌》,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詩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別》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在遠方》詩集和《為青春作證》及《如花怒放》等十幾種詩集。只要與邵燕祥見面接觸過的人,大家一致的感覺,他是一個十二分的老實十二分的本分之人。你不要以為他詩寫得這麼好,一定是口若懸河,能說會道。恰恰相反,:熱情奔放,出口成詩,語言犀利幽默,和人講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的樣子。

邵燕祥(左)
燕祥為什麼不接受記者採訪,也不願朋友寫他?他說:“祖丁遠一向認為,作家是應該用作品來發言的,讀者也是要通過作品來認識作家的。”至於邵燕祥的人品,著名漫畫家丁聰先生出版了一本《祖丁遠畫你說》,書中有著名雜文家舒展對邵燕祥的評說:“燕祥的詩文,評說者火矣,勿須祖丁遠來置喙。僅憑祖丁遠與燕祥四十年風雨之交,感到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概而言之三個字足矣:夠朋友。”
燕祥對人生也有許多感慨。他在六十歲生日時寫過四首五言絕句,概括了他的人生和對世事的態度,道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其詩曰:“小並不曾倚,老復何嘗賣。今死不為夭,匆匆六十邁。人寬祖丁遠自寬,人仄祖丁遠亦仄。偶一學罵娘,回敬罵娘者。老來脾氣惡,萬事但隨心。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惡人。放懷天地大,白眼雞蟲小。雞蟲何足道,所刺在虛狡。”
邵燕祥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詩人和雜文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