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
焦循
焦循(1763~1820),清哲學家、數學家、戲曲理論家。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蘇揚州黃珏鎮人,嘉慶舉鄉試,與阮元齊名。阮元督學山東、浙江,俱招往游。后應禮部試不第,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餘年。構一樓名“雕菰樓”,讀書著述其中。博聞強記,於經史、歷算、聲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有《里堂學算記》《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劇說》等。(據1999年版《辭海》“焦循”條)
江蘇甘泉人(江蘇揚州方巷人),生於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癸,卒於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得年五十八歲。少年曾就讀於揚州安定書院。曾於三十三歲赴山東居阮元(時為山東學政)家,並隨阮元至浙江赴任。嘉慶六年(1801)中舉人,翌年應禮部試不第,即返鄉奉侍母親不出仕。母親卒后,託疾閉戶,建“雕菰樓”,足不履城市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精博。其中用力特深的,為《周易》、《論語》、《孟子》三書。《周易》方面,著有《易章句》十二卷、《易圖略》八卷,《易通釋》二十卷(以上四十卷合輯為《雕菰樓易學三書》)、《易廣記》三卷、《易話》二卷。《語》、《孟》方面,嘉慶九年(1804)著《論語通釋》一卷計十二篇(后增為十五篇),又推衍《通釋》的含義為《論語補疏》二卷。嘉慶廿一年(1816)始編《孟子長編》三十卷,再編為《孟子正義》三十卷,廿四年(1819)成書。翌年逝世。經學以外,又精天算、考古。曾與凌廷堪及李銳(字尚之,號四香,1765-1814,是清中葉少數專精天文學和數學的學者之一)一起研究天算之學,焦循著《天元一釋》、《開方通釋》等專門著作,又曾著《群經宮室圖》、《劇說》等。平生所著散文輯為《雕菰樓集》二十四卷,由阮元於道光四年(1824)在粵刊行。
除經學、天算之外,焦循極注重地方志,對方誌學亦有見解。嘉慶十一年(1806)受揚州知州伊秉綬聘任,與阮元等編《揚州圖經》及《揚州文粹》(或可能《揚州圖經》即含《文粹》),后因伊氏調任而中輟,焦氏將所搜得文獻輯為《揚州足征錄》二十七卷,繼任者姚秋農修《揚州府志》(嘉慶十五年刊),焦氏亦參與纂修,或至少提供過具體的指導意見。《揚州足征錄》外,焦氏又著《北湖小志》六卷、《邗記》六卷,記述揚州一地風土。清代學者。字理堂(或作里堂),晚號里堂老人。甘泉(今江蘇方巷)人。嘉慶六年(1801年)舉人。博學多識。尤擅易學、算學,亦精醫理。曾南遊江浙、北及河北、山東等地,常與人論醫。輯有《吳氏本草》一卷(1792年),多取材於《太平御覽》等,今存其手校稿本。嘗與名醫李炳交厚,將李炳醫案集成《李翁醫記》二卷。李氏之書稿《辨疫瑣言》書稿則由焦氏子抄錄傳世。另著有《雕菰樓文集》。
焦循少穎異,事父母以孝聞,服喪盡禮。乾隆辛酉舉於鄉。嘗從阮元游浙江。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樓曰“雕菰”,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焦循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其於《易》本世傳家學,嘗疑一“號啕”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同例;乃遍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擬《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為恨。病廖,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得悟者,一曰“旁通”,二曰“根錯”,三曰“時行”。《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為《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經既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龠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目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為主。
焦循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系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左傳社氏集解補疏》五卷,《補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為《六經補疏》二十卷。
嘉慶六年(1801)舉人,后棄科舉,托足疾在家10餘年,博聞強記,於經、史、歷、算、聲韻、訓詁之學均有研究。專註於經史之學,對詩詞、醫道無不貫通。搜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世家有藏書,其藏書處有“雕菰樓”、“半九書熟”,阮元稱有“湖光山色之勝”。抄錄圖書甚多,被譽為“抄書一痴”,傳說當大水淹到家門口時,還在南窗下從容不迫地抄錄《中論》。每得一書,必識其卷端,故其藏書多有題識,藏書印有“理堂”、“恨不十年讀書”、“焦氏藏書”等。著述宏富,有《里堂學算記》、《雕菰樓易學三書》、《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曲考》(佚)、《劇說》、《花部農譚》、《雕菰集》、《雕菰樓文集》、《六經補疏》、《北湖小志》等數百卷。
焦循思深悟銳,尤精歷算之學。撰有《釋弧》三卷,《釋輪》二卷,《釋橢》一卷,《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又命其子琥作《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當時算學名家李銳、汪萊、錢大昕等,皆與討論而嘆服焉。

《北湖小志》
因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貢鄭註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五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曰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群經宮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為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
焦循易學世界構圖的兩個方面:嚴格、規範性與生命、靈動性著作考據之爭 焦循在全身心投入到易學研究以前,還曾加入過“著作考據之爭”。這場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惠棟學派的經學研究。文學家袁枚批評經學家孫星衍的經學研究缺乏“性靈”,聲稱只有文學才有“性靈”,經學只不過是機械呆板的抄書之學。另一位乾嘉時代的重要學者章學誠則對袁枚的觀點進行了批評。章學誠認為,袁枚的觀點將引發非常嚴重的倫理後果,因此是非常不可取。焦循也加入了這場爭論。他不同意孫星衍以考據為經學的立場,而同意袁枚對當時考據學風的批評,欣賞袁枚大力提倡的“性靈說”,認為無性靈則無所謂學風,考據的問題正在於缺乏“性靈”,但他也不同意袁枚文學是體現“性靈”的唯一領域的看法。他重新解釋“經學”範疇,賦予其新的意義。在他的“經學”中,“性靈”得到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體現。他指出:“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為之輔,匯而通之,辨而析之,求其訓詁,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濟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說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辭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辭章者,不足語此也。”(《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由此,經學是“性靈”的完全展開。它不是個人的“性靈”,而是眾多人的“性靈”在跨越了個人的局限性與歷史性的基礎上融匯而成的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由學問與性靈共同構成的。因而,真正的經學有兩個特徵,一是學問的貫通,經學應當成其為經文本身與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學問相互貫通的產物;二是“性靈”的貫通,經學應當成後代經學家註釋經書的“性靈”,與古代聖賢著述經書的“性靈”相互貫通的產物。
易學
《幾何原本》世界構圖的吸收與超越
焦循易學向我們描繪了這樣的一幅關於宇宙整體的動態畫面:它是由一系列簡單的元素經過不斷的有序的進化積累生成的,而且一直處在生生過程之中,它沒有終結之時,它是一個開放的不斷擴大自身的系統。這一系統有兩個重要特徵:生長性(進化與積累)與有序性(嚴格與規範)。一個系統,如果沒有進化與生長,它就不夠宏大,不符合儒家天地生生之道;但如果沒有嚴格與規範,那麼這個宏大也是一種假象,它就是堆砌在沙灘上的巨大建築,布滿縫隙與窟窿,一旦有了外來的衝擊,它很快就會垮塌。受過晚明《幾何原本》及其天算學洗禮的清儒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學人都更看重這一系統的嚴格性與規範性,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清代學術的基本特點,這也是為什麼清代學術在經歷時間沖刷磨蝕之後仍然屹立的奧秘所在。保障焦循易學嚴格性與規範性的主要部件是焦循在易學中“發明”的變換規則。這些變換規則有兩類:天算型的,有旁通、相錯、時行,有時合稱“比例”;音韻訓詁型的,主要有“引申”,共12例。
這兩種規則在易學中的作用也不相同。大體說,它們事關易學的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文字層。《易經》是一部書,它是由文字(包括短句)組成的,一切對於《易經》的解釋必須經由文字這個中介,必須是針對一定文字所作的解釋。卦爻象層。正如英和所說的那樣:“群經皆可理釋(以文字解釋),而惟《易》必由數推。”文字因其自身內蘊的模糊性與漂游性,使得它不可能很好地揭示一個嚴格而規範的世界,因此,只有在由數學符號組成的世界里,人們才能夠發現這種嚴格性與規範性。
採用天算學思路的優點還在於,可以對《易經》中的每一個詞都給出嚴格而規範的解釋。如果我們將《易經》看成是一個宇宙的話,這個宇宙中的一切都將籠罩在數學的光芒之下,再沒有任何玄奧神秘的保留地帶。英和在為焦循易學著作寫序時為此興奮不已,稱讚焦循的易學“元本經文,疏通引證,使全易無一剩句殘言。”在焦循眼中,《易經》實際上已經成為一部天算學類型的著作了,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認知主義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我們個人是否同意這個時代的易學視野,則是另一個問題。

焦循
經學與天算學:焦循思想的中心話題
在《幾何原本》前六卷譯本傳入中國之後,明末清初的知識界表現出了學習這部著作的巨大熱情。雖然這部書的流傳並不廣泛,但它對當時中國學人的思想上產生的衝擊力卻是不可磨滅的。緊隨著譯本,出現了一批研究學習的著作。如孫元化的《幾何體論》、《幾何用法》(1608),方中通的《幾何約》(1661),李子金的《幾何易簡錄》(1679),杜知耕的《幾何論約》(1700),梅文鼎的《幾何通解》等。此外,還有一些著作雖不是專門的幾何學著作,但它們都受到了幾何學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
焦循年青時並沒有全力研究算學,而是汲汲於當時最受關注的名物考證之學,著有《群經宮室圖》。這是當時最前沿、最時髦的學術課題之一。在考證過程中,焦循認為鄭玄注有錯,為了將意思講通,不惜改動了鄭注。為此,惠棟的弟子、學術輩份比焦循高的江聲專門來信辯論,焦循又複信抗辯。在辯論過程中,焦循注意到,惠棟開創的吳派學人在治學中有一個不言而明的假定,即漢儒的註解是最可信賴的學術資源。在《群經宮室圖》中的研究中,焦循堅持認為,如果不修正鄭玄的註釋,有一段話根本無法講通。在辯論過程中,焦循以及學術好友阮元都意識到,曾經給考據學開闢過輝煌希望的惠棟學派,其方法論走入了嚴重的誤區,因為吳派以漢儒的經傳作為判斷真理的標準。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儒學將重新走入閉塞的死胡同。在為焦循《群經宮室圖》所作的序言中,阮元提出了新的學術標準:“求是”而不是“從古”。阮元說:“余以為儒者治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穎達)賈(公彥)義疏之例也。”這是阮元與焦循的共同看法。
與所有的人文學術一樣,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往往是言人人殊,你來我往,爭得不亦樂乎。從今天的闡釋學的角度看,在你來我往的熱烈爭論之中,學人們通過對話,相互拓寬了視野,增加了理解,從而體察到了人文學的真理。經學研究歷史悠久,註疏材料眾多,層層累積,與其他人文學科相比,其中的爭論更多,很不易得出人所共認的結論。但在乾嘉學術的鼎盛時期,焦循、阮元(尤其是焦循)等人卻為這種現象深感不安,並設想著一種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焦循看來,當時的許多經學爭論都是無根之談,它的終極基礎是漢儒經傳,其本身算不上可靠的真理,但是,和以往的宋明理學相比,漢學的確是當時的學人不能須臾離開的出發點,是一種既不能完全靠得住、但又不可離開的基礎。焦循憧憬著這樣的一種學術:它的真理不依賴於爭論,它的真理是直觀自明的。焦循正在學習的天算學,給他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可能。對焦循來說,一道複雜的算學題,它的結論是否正確,並不需要爭論。只要將答案代入題目之中,經過加減乘除的計算,正確與否即可驗證,正誤雙方都不必浪費太多的口舌。倘若經學真理也具有算學真理一般的真理性,那該多好。這一想法,一定曾在當時許多學人的心目中出現過。在其後的若干年內,焦循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天算學研究之中。
《天元一釋》兩卷
《加減乘除釋》八卷
《開方通釋》
《群經宮室圖》兩卷
《論語通釋》

焦循論曲三種
《易章句》
《孟子正義》
《六經補疏》二十卷
《古文尚書辨》八卷
《毛詩物名釋》二十卷等
《邗記》六卷
《北湖小志》六卷
《揚州府志》
《李翁醫記》二卷
《沙疹吾驗篇》一卷
《醫說》一卷等
《雕菰集》二十四卷
《里堂詩集》八卷
《里堂詞集》二卷
《仲軒詞》一卷
《劇說》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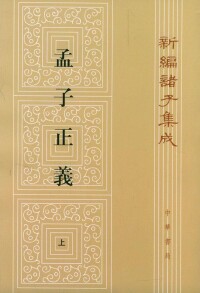
《孟子正義》
里堂歿后,廷琥秉承父志,歇力完成《孟子正義》之校對、謄錄工作。惜半年有餘,於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廷琥亦以病終。臨終之日,遂深托其叔焦征,以完成《孟子正義》之刊刻印行。最後於道光五年(1825年),《孟子正義》終告付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