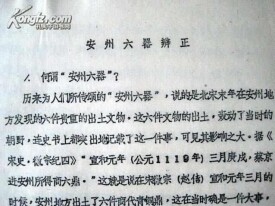安州六器
安州六器
“安州六器”,指的是宋代人發現的西周早期青銅器。
據宋人王黼等著《博古圖錄》記載,重和戊戌年(1118)出土於安州安陸郡孝感縣,凡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稱為南宮中鼎、中鼎、召公尊、父乙甗。其中一件青銅鼎上,出現數字卦二。
“安州六器”以其出土年代早、銘文內容重要而著名。安州六器”實出於孝感,記述此器較早且較詳的,是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三《安州所獻六器銘》跋,云: “右六器銘,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於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圓鼎二、抓一。皆形制精妙,款識奇古。
歷來為人們所傳頌的,’安州六器”說的是北宋末年在安州地方發現的六件貴重的出土文物。這六件文物的出土,轟動了當時的朝野,連史書上都突出地記載了這一件事,可見其影響之大。據《宋史·徽宗紀四》“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庚戌,蔡京進安州所得商六鼎。”這就是說在宋徽宗(趙估)宣和元年三月的時候安州地方出土了六件商代青銅鼎,這在當時確是一件大事,人們以為這是天降祥瑞,當這些寶物由安州送到京城后,奸相蔡京便將這六件青銅器獻給了皇帝。從此這“安州六器”就成了中國古代文物考古、金石學方面的一件重要事件了。千百年來經常為人們所引用。但從來沒有人懷疑其出土地點。人們只知道文物是在安州出土的,並不知道具體出上點在哪裡。一般以為宋代的安州就是安陸縣,顧名思義“安州六器”也就順理成章的認為是安陸所出土了。實際上所謂“安州六器”並非安陸所出,而是出自今之孝感市。
據《孝感縣誌》記載,在明萬曆二年(1574年)甲戌九月,孝感縣城拓展城牆,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形狀為“蟠腹爹口、三足兩耳,周園端嚴,體被五色,上有識皆古領捕文,大小凡六十字。”當時人樂道為祥瑞,遂築鼎於其地,名為“神鼎閣”。請著名文學家王世貞為記。王在文中考訂此鼎為周初南宮仲父方鼎,並說稽正宋人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款識》文字皆合,又據《漢陽府志》引明《一統志》說:“宋徽宗時,孝感縣東湖村(約今孝感市北門大街附近,神鼎閣毀於兵火)夜有光燭夭,農人聞於官,掘地得周九鼎貢於朝。”清雍正《湖廣通志》卷七七古迹志里也有類似記載。在其孝感條下有:“東湖村在縣東,宋徽宗時村民視夜有光燭天,聞之於官,掘地得周九鼎貢於朝……”。怎麼“安州六器”忽地變成了九器呢?《孝感縣誌》引述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謂“安州六器”皆得於安陸之孝感縣耕地得之,計方鼎三、園鼎二、甄瓦一、其銘文著在法帖之九卷、十卷、十六卷”。並說“此六器”靖康之難,俱為金人擄去不知下落。”《縣誌》接著說在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法帖》中又記載“方寶甄一、曾侯鍾二,同得之於安陸孝感。”還說“此三器藏之於方城范氏”。這樣一來,宋代在安州所出實為九器。經查閱明朱謀至刻本宋人薛尚功所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與《孝感縣誌》所說基本相符,只是小有差誤。前面所說九件器物,分別是在該書卷六。即曾侯鍾二、卷九、國寶鼎二。卷十、南宮中鼎三,卷十六為方寶獻、父乙頗。在其“父乙瓶”銘文後注說“右銘重和戊戌歲出於安陸之孝感縣,耕地得之,自言於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園鼎二、瓦南一共六器,皆南宮中所作也,形制精妙,款識奇古,日父乙者蓋商末周初之器耳。”在其卷九園寶鼎二銘文後面也說:“右二器~同得於安陸之孝感……。”另在卷十六的方寶獻銘文後又說:“此器與前二園鼎同出於安陸之孝感……。”只是在卷六的曾侯鍾之銘文後面說“右二鍾前一器藏方城范氏,皆得之安陸……”。此處沒有提到孝感,這裡就鬧出了一個矛盾,上面所述器物共為九件,如兩件曾侯鍾為安陸所出,那孝感所出則實為七件了。說六器顯然是不對的,考之薛書,筆者認為這九件器物都應為孝感所出,把兩件曾侯鍾說為安陸。可能是筆誤,或是在安陸後面少寫孝感二字,這批器物可能是兩次出土。至於《孝感縣誌》說兩件曾侯鍾與方寶獻均藏方城范氏則是錯誤的。在薛書里明確記載只有一件曾侯鍾藏方城范氏。薛尚功為北宋末至南宋初人,是當時著名金石學家,《歷代鐘鼎彝器軟識法枯》編著於南宋紹興年間一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當是可信的。
《宋史·徽宗紀》將“安州六器”記為“商之六鼎”顯著是錯誤的。在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記載“安州六器”和另三器均為周代器物,每件器物皆有銘文。
據薛氏考證:三件南宮中鼎,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也。周代有南宮氏,前一鼎文中有“錫於瑛玉”,據《集韻》雲“玉璐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為此鼎而刻之銘也。而謂之’’豁父乙尊”者,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薛氏考“父乙獻”“園寶鼎二”皆為周初器物。關於“曾侯鍾”,薛氏考訂銘文雲,“惟王五十六祀,楚王韻章,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其名為章,然則此鍾為惠王作無疑也,唯對“方寶獻”沒有指出時代。
上面所引薛尚功對銘文的考證,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他把父乙獻說成商末周初之物則是值得研究的。
至於宋史上說“安州六器”得於宣和乙亥,而薛尚功則說是重和戊戌。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宋徽宗喜歡改換年號,他在位做了廿四年皇帝就改過六次年號,有時一年有兩個年號。這個宣和元年就是這樣,查《宋史·徽宗紀》。進“安州六器刀為宣和元年三月,而改元之前的二月即為重和。因而“六器”實際是在重和年號出士的。從文物的出士到獻於州,最後貢於朝是應當有一個時間過程的。
寫到這裡,問題算是已經明確了,但還要再說幾句,宋史上所提“安州六器”未說出土具體地點,筆者以為這是就大地名而言的,宋代的安州管轄範圍比較大,包含現今之孝感地區安陸、雲夢、孝感、應山、應城五縣地域。孝感當時是安州的屬縣,孝感建縣於南朝宋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在此之前一直為安陸縣境之一部分,建縣后長期屬安州管轄,只是到了清朝初年(雍正七年)才划屬漢陽府,所以說。在宋代,孝感縣出土文物由縣送到州,州獻朝庭,是順理成章的事,說成安州所出,也是可以的。只是不應該把安州誤為安陸、這樣一來,就把真正的文物出土地點忘卻了。
周昭王十九年,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周軍渡漢水時,陰風驟起,氣候惡劣,將士驚恐,軍隊損失嚴重。昭王伐楚與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極重要的關係,但這樣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卻因為周人的隱諱而蒙上了重重迷霧,甚至連周昭王征伐的對象到底是誰都存在爭議。根據現代學者的考證,周昭王所伐之“楚”並非“楚國”,而是西周時期和楚國並立於楚地的楚蠻。
“楚”有二義,一是指羋姓楚國,二是指南方楚蠻。周成王十九年,楚國先祖熊繹被封為楚子,封地在楚蠻之地,因此楚國與楚蠻有交集,到東周時,楚國崛起吞併了楚蠻,兩者才混為一體。在周昭王時期,楚國爵位不過是楚子,封地僅五十里,荒僻貧弱。在這種情況下,周昭王不可能盡起六師,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會收穫頗豐,大小貴族均興高采烈地作器銘功。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為南征楚國而喪命,則周、楚必為不可解的死敵,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報此仇,楚國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還作為周朝的封國參與伐徐之役。
而楚蠻在周昭王時期佔據地域廣大,大約在今漢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區和下游的漢東地區,且佔據銅礦主產地銅綠山。在先秦時期,銅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源,政治、經濟、戰爭等方方面面都廣泛需求。楚蠻雖然人數眾多,分佈廣泛,但始終沒有如從前的三苗和後來的楚國一樣形成一個強大統一的政治體,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這種情形下的楚蠻正適合作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對象。
昭王南征之“楚”為楚國的說法最早出現於東漢,王逸注《楚辭·天問》。後世學者多信此說,口口相傳代代為繼,使得昭王南征楚國幾成定論。
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除了印證文獻史籍的記述之外,有時還能提供或補充人們所不知的歷史情節。應當感謝考古學家的辛勤勞動,由於他們的發現,我們幸運地獲得了對“昭王南征”這段史跡更全面的認識。
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銅器,其中對西周史事記述的最重要銘文是穆王時代的《史牆盤》,作器人牆世代為周王室的史官(乍冊)。史牆對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評價。銘文說:“弘魯昭王,廣批荊楚,唯狩南行”,說昭王大規模地撻伐荊楚,因為巡狩而到了南方,從而讚揚昭王事業的宏偉(弘魯),銘文中全無“南征不返”之類的遮掩之詞。
收藏在北宋《博古圖錄》和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等書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陸(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組有銘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包括兩件中方鼎、中觶等器,作器人是曾跟隨昭王伐楚的貴族“中”。考古學家綜合研究了這六篇銘文,發現了以往少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紀事。例如中方鼎記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貴族“中”先去南國準備行宮。中方甗則記錄了“中”所走路線經過的地方,其中有方鄧、鄂師、漢中洲等。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銘文中說到昭王十六年伐楚獲勝凱旋歸來,賞給貴族“中”采地(邑)。從各銅器的銘文分析,昭王伐楚是動員了大量的人力,規模也大,有許多貴族都跟隨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