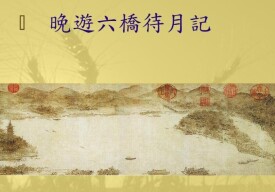晚游六橋待月記
晚游六橋待月記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吳縣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學“公安派”代表人物,與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並稱“公安三袁”。他在文學上反對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流弊,主張文學作品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認為作詩為文都應通於人之喜怒哀樂,以見從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論與創作掃清了明代復古主義的習氣,開一代清新活潑的文風。作品有《袁中郎全集》。
晚游六橋(1)待月記
石簣(kuì)(7)數為余言:“傅金吾(8)園中梅,張功甫(9)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10),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11),粉汗為雨(12),羅紈(wán)之盛(13),多於堤畔之草,艷冶(yě)(14)極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15)。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16)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chōng)(17)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18),安(19)可為俗士道(20)哉?
(1)六橋:西湖蘇堤上的六座橋,由南向北依次名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
(2)為春為月:意為是春天月夜。
(3)一日之盛:一天最美的時候。
(4)夕嵐:傍晚山間的霧氣。
(5)梅花為寒所勒:為:被;勒:抑制。
(6)尤:特別。
(7)石簣(kuì):即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明代會稽人。明萬曆年進士,袁宏道的朋友,公安派作家。下文的“傅金吾”、“張功甫”都是人名。
(8)傅金吾:傅,姓。金吾,漢朝主管京城治安的官員,這裡指明朝錦衣衛的官員。
(9)張功甫:南宋將領張峻的孫子,玉照堂是其園林,有名貴梅花四定址。
(10)戀:迷戀。
(11)歌吹為風:美妙的音樂隨風飄揚。
(12)粉汗為雨:帶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
(13)羅紈(wán)之盛:羅紈,絲織品,這裡是指穿羅紈製作的衣服的人很多。
(14)於:比。
(15)艷冶:艷麗妖冶。
(16)”設色:染上彩色。
(17)午、未、申三時:指午時、未時、申時三個時辰,相當於從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的這一段時間。
(18)夕舂(chōng):夕陽的代稱。舂,用杵臼搗去穀物的皮殼。形容日落西山的樣子。《淮南子·天文訓》:“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後人又以“舂”代指日落處的山名。《集韻》:“舂,山名,日所入。
(19)受用:享用。
(20)安:怎麼。
(21)道:說。
西湖景色最美的時候是春天,是月夜。一天里最美的是早晨的煙霧,是傍晚山間的山光。那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氣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開放,景觀更是奇特。
石簣多次告訴我:“傅金吾園中的梅花,是張功甫玉照堂中的舊物,應該趕快去觀賞。”我當時迷戀著桃花,竟捨不得離開湖上。從斷橋到蘇堤一帶,綠柳迎風飄拂如綠煙,桃花盛開如紅霧,瀰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樂隨風飄揚,帶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著各色絲織品的富裕的遊客很多,比堤畔的草還多,真是艷麗極了。
然而杭州人遊覽西湖,卻僅在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五時之間;其實湖光翠綠之美,山嵐顏色之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陽未下時,才最濃艷。月景之美,更是難以形容。那花的姿態,柳的柔情,山的顏色,水的意味,更是別有情趣韻味。這種快樂只留給山僧和遊客享受,怎麼能夠對那些凡夫俗子所述說呢!
文學賞析
西湖乃人間仙境,春夏秋冬、陰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卻別具慧眼,情有所鍾,故開篇云:“西湖最盛,為春,為月。”既視“春”與“月”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節與時辰,則此文著重描繪西湖的春景與點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極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並非一概索然無味。作者接下稱:“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此“日”相對於“月”而言,指白天。朝煙,謂清晨水氣瀰漫時的湖光;夕嵐,謂傍晚暮靄籠罩時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為最盛,何以朝煙、夕嵐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著通過生動的描繪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寫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作者先寫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遲開,花期雖推遲,但得以與杏花、桃花斗妍爭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奼紫嫣紅的春色,卻是罕見的“奇觀”。如此“與杏桃相次開發”的“香雪海”值得觀賞,更何況友人陶石簣又數言這裡的“傅金吾園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應該趕快去大飽眼福。這裡寫西湖梅花之美乃虛寫,是作為一種鋪墊,旨在襯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嘆為觀止。——因為作者“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梅花為“歲寒三友”之一,被視為高潔的象徵,桃花則曾被貶為“輕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為桃花所“戀”,可見其迥異於世俗的獨特審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的桃花亦確實蔚為奇觀:“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僅此兩句,採取遠望的角度,就寫出西湖二十餘里桃花夾雜著綠柳的總體意境。“綠”指柳條,“紅”指桃花,“煙”“霧”瀰漫,則渲染出“花態柳情”,呈現繁花照眼、生機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濃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開乃是“西湖最盛”“為春”的主要表現,其次還表現為遊人羅紈之盛:“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在桃花盛開的白堤、蘇堤上,紅男綠女,比肩繼踵,甚至比堤邊的春草還多;歌樂似春風迴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熱鬧:色彩艷麗之極,風姿放蕩之極,著“艷冶”二字,可謂摹寫、概括盡致。作者之筆墨亦極盡濃艷之能事,蓋非如此不能描繪出西湖春天“艷冶”之盛景。
在描寫了“西湖最盛”“為春”之後,按邏輯應該接著描寫“西湖最盛”“為月”;但作者卻捨不得讓主角“月”輕易出場,意欲以之唱大軸戲,所以先讓配角朝煙、夕嵐登台鋪墊。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羅紈之盛,在結構上亦是順理成章。紅男綠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時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種“俗”的表現,其“不識廬山真面目”乃在於缺乏超俗的審美趣味。作為外來遊客的作者則以其慧眼發現:“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這是對西湖“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的具體描寫。“湖光染翠”,“山嵐設色”,這一“染”、一“設”,皆賦予大自然以靈性,將大自然比擬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畫筆,只有在“朝日始出”與“夕舂未下”這兩個美妙時刻才為湖光、山嵐添彩增色,從而達到“濃媚”即一種極其嫵媚動人的審美境界。這與午、未、申三時西湖之“艷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媚”比“冶”要高出一籌。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審美境界卻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開頭所說的“為月”。對“西湖最盛”何以“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後來描寫,旨在造成一種懸念,增添讀者的興味。與寫“為春”筆墨之濃艷不同,寫“為月”採用的是淡雅之筆,一濃一淡,相輔相成。此處“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筆才能寫出其神韻。作者此刻惜墨如金,並未大肆渲染,僅用“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該是一種什麼樣特殊的情趣與意味呢?作者留給讀者去想像。而“月景”確實妙不可言,寫得太具體難免要損害其美,束縛讀者的神思,而這樣略加點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無窮的趣味。這是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藝術手法。月景雖最美,但並非人人能享受。作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頗以能探幽尋勝、受用此樂而得意,對“俗士”即紅男綠女的“杭人”則含有諷誚之意,故云:“安可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學思想核心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敘小修詩》)。這篇遊記即體現了這一思想。從文章內容來看,作者獨賞西湖之春的“月景”與“朝煙”、“夕嵐”,這和“午、未、申三時”游春的“俗士”迥異其趣;作者又寧願捨棄賞梅機會,而“為桃花所戀”,與傳統士大夫的審美情趣亦相悖,這都是他“獨抒性靈”之處,顯示出獨特的個性與審美觀。文章筆法也是任隨自然,意到筆到,該行則行,該止則止,“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卻用寥寥幾筆,點到即止,不加細描,而對西湖的桃花與“羅紈之盛”卻頗費筆墨,堪稱“不拘格套”。其實,這是因為越是高層次的審美境界愈難以用文字描繪,不如以虛代實,以簡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蕭蕭只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李東陽《柯敬仲墨竹二絕》)的藝術效果。這是作者聰明之處,他還是頗懂得藝術辯證法的。
名家點評
浙江大學特聘教授吳戰壘:“這篇山水遊記,始終扣住‘西湖之盛,為春為月’的‘春’、‘月’二字,騰挪變化,詳寫‘為春’之盛,略寫‘為月’之美;題為《晚游六橋待月記》,卻始終沒有正面寫待月的情景。他的高妙處在於以層翻浪疊之筆,依次寫出梅花、桃花之美,朝煙、夕嵐之美,一景勝似一景,逐層襯染,不犯正位,從而造成讀者強烈的‘待月’心理;待到‘干呼萬喚始出來’,卻又匆匆一面,飄然而去,使人有‘著眼未分明’之感,因而顯得餘韻悠然,情味無窮。作者用這種空靈幻變之筆來寫月景之美,可謂別出心裁。”(《閱讀和欣賞 古典文學部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