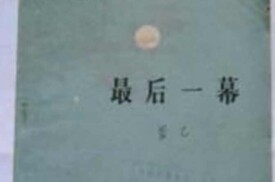最後一幕
最後一幕
荒誕園裡又一株

幾何國際建陶瓷磚
《第二十二條軍規》不僅使海勒一舉躋身於“美國現代一流作家的行列”,還使他成了繼卡夫卡、薩特、加繆和貝克特之後又一位現代主義荒誕派作家之一。海勒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之後於1994年推出它的續集(實際上他1990年就發表了續集的部分章節),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作者當年言猶未盡;二、“第二十二條軍規”仍在運作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不吐不快。
與《第二十二條軍規》所受到的讚揚一樣,《最後一幕》一經推出便受到文學界和新聞界的普遍褒獎。《紐約時報》稱它“充滿激情與人情味……震撼力強,發人深省”;《華盛頓郵報》說它是“一位勇往直前、才華橫溢、極具影響力的作家對二十世紀的回眸”;《紐約人》雜誌評論道,《最後一幕》是“二戰時期那代人中偉大作家之一的一個總結……儘管我們即將告別約塞連、米洛、劉、溫特格林和塔普曼牧師了,但在《第二十二條軍規》發表紀念日之際,我們仍可歡迎他們”。《紐約時報》還說,“《第二十二條軍規》攫獲了整整一代的思想及想象力,30年後,約瑟夫·海勒又為那部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一寫了續集。《最後一幕》重訪約塞連、米洛·明德賓德、塔普曼牧師和其他一些人,正是這些人物使得《第二十二條軍規》如此令人難以忘懷,這些人雖然未必變得更加明智,卻都老了。他們不僅面臨一個世紀的終結,也正在演出他們人生的最後一幕。”。
海勒在《最後一幕》之前還寫了《發生了一件事》(1974)、《好如黃金》(1979)、《天曉得》(1984)、《可不是鬧著玩的》(與斯皮德·沃格爾合著,1986)及《給它拍張照》(1988)五部長篇,而且都是暢銷書。其間還發表了大量短篇、劇本和評論。
作者其人 約瑟夫·海勒1923年生於紐約的康尼島(即小說中常提到的那個地方),父母都是從前蘇聯移居美國的猶太人。用海勒的話說,他小時的家境“比較貧窮”。他四歲喪父。中學畢業后二戰正酣,他曾到弗吉尼亞的諾福克海軍基地當鐵匠學徒工。後來參加空軍,當上了一名投彈手,並赴歐洲戰區作戰。戰後用軍人津貼上了大學,畢業后教過書,在《時代》雜誌社工作過。從他中學以後這段身世看,頗似書中人物薩米。1955年開始《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寫作,並發表了其中的部分章節。六年後小說正式發表。由於他在文學方面取得的成就,1963年獲得美國文學學會的資助。
1945年與雪莉·赫爾德結婚,生有一男一女。1981年身患吉爾林?伯利綜合症(即書中薩米的一個朋友得的那種屬於神經系統的病),幾乎要了他的命。住院期間,結識了護士瓦萊麗·漢弗萊斯,病癒后1984年與赫爾德離婚,1987年與漢弗萊斯結婚。從他的婚變狀況看,又和書中人物約塞連相仿。
書中人物與社會現實 《最後一幕》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第二十二條軍規》里的“小人物”,他們大都來自康尼島,參軍初期集訓時已經互相認識,在歐洲時又都在同一個空軍部隊服役(劉除外,他當了步兵)。大難不死回家后,雖各奔前程,但還保持著聯繫。此外,他們各自仍然保持著以往的性格。
約翰·約塞連,這個當年為逃避戰鬥只求活命而一再躲進醫院的上尉投彈手,年邁之際最懼怕的仍然是死亡。我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便在醫院裡住著,而且已經兩個星期了。他沒有病,卻不停地叫大夫為他檢查。他說他得了什麼“病症幻覺症”。當大夫們告訴他“什麼也沒有檢查出來”時,他則要求他們“接著觀察”;當他們說“你的健康狀況很好”時,他就說“那你們就等著瞧吧”。其實約塞連對死亡的恐懼正是海勒本人思想的寫照。朱迪斯·魯德曼指出:“海勒的‘戰前小說’的主題就是他親身經歷過的恐懼:在戰鬥中喪命。”海勒在戰爭時期對死亡的恐懼一直延續到和平時期,主要是因為那場吉爾林·伯利綜合症使他談虎色變。他說,隨著年事日高,“死亡、疾病和晦運佔據了我的一切”。為此他不斷安慰自己說“別人好像都能過好死亡這一關,我也不致會有什麼困難”。
約塞連除了明確無誤地表示對死亡的恐懼外,他當年對軍中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荒誕也從來是直言不諱的。而在《最後一幕》里,他的這一特點則突出表現在他對荒誕的美國政治和社會的不滿乃至憎惡。五十年代麥卡錫法案曾使美國人民處於人人自危、隨時都有被指控為共產黨的白色恐怖之下,此時的海勒只好將美國社會壓縮到一個空軍軍團里,並借約塞連之口,從軍團司令一直罵到他的頂頭上司。但他並沒有因此而使自己逃出那條軍規所設下的圈套。“第二十二條軍規”規定,只有神經錯亂的瘋子才能獲准停止飛行,但它同時又規定,如果你在“面臨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時,對自身安全表示關注”,就證明你頭腦很清醒,不是個瘋子,因此就必須執行飛行任務。
同樣,他也根本無法逃脫美國社會類似那條軍規的種種制度圈套。這種圈套遍及各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福利等等。那些極不合理卻又切切實實存在的怪現象使約塞連又大開罵戒了。如果說他在空軍里時只敢罵到司令,或者無計可施就拒絕穿軍服,赤條條地爬到樹上看同機炮手斯諾登的葬禮,那麼今天他則一直罵到了總統。他罵總統是“小普里克”,而“普里克”的意思除了流氓和無賴外,“我們還管避孕套叫普里克”。他罵“庸才和利己主義者充斥政府部門”,並大叫“我想把所有的普里克從政府里統統踢出去。”因而發誓再也不參加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總統選舉。
約塞連對美國的社會現狀了如指掌。在紐約這個“大蘋果城”、“帝國州的帝國城”,這個“國家的金融心臟、大腦和肌腱”、“除了倫敦以外文化活動開展得最好的城市”里,他看到了什麼呢?從他住的高層公寓望出去,他看見的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豪華轎車穿梭於大街小巷;而在港務局公共汽車終點站里,他見到的卻是另一個世界:“這個文明處所的氣味實在難聞。刺鼻的煙味,從不洗澡的人身上發出的體臭與他們扔掉的垃圾散發出來的惡臭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嘔,任何人都無法忍受,只有那些常客例外。半夜裡,一個個臭氣熏天的軀體肆無忌憚地相互擠靠在一起,誰也別想找到一塊較寬敞的地方清凈一下。人們大呼小叫,有喊的,有吵的,有動刀子的,有點火的,有性交的,有吸毒的,有酗酒的,還有摔瓶子的。到了清晨,這裡有的傷,有的亡,一片狼藉。”號稱全球頭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強國的美國自詡最講平等博愛、最尊重人權,卻對這樣的狀況要麼是視而不見,要麼是無能為力。這難道不是對世界頭號強國的極大諷刺嗎?
然而,約塞連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並不說明他是個為民請命的英雄。後現代主義作品里是沒有英雄的,它的人物甚至是“反英雄”的。人物的存在是因為他們存在,他們的悲與喜已經淡化,好與壞難以分開,有的甚至僅僅“是場景中一個可以替代的暫時性角色,他喪失了悲劇的氣息,而多了些遊戲成分。”約塞連當投彈手時對上級不滿不是因為他擔心美國打敗仗,而是因為怕死;同樣,他開口大罵,也不是因為他擔心美國垮台百姓受難,而是因為他具有美國傳統西部牛仔的性格:豪爽、仗義。他思想開放,生機勃勃,放蕩不羈,個人第一。一方面不滿政府官僚的腐敗,一方面幫助米洛將那種根本不存在的“飛翼轟炸機”賣給政府,並且心安理得地收下了米洛給他的50萬美元“好處費”;他一方面罵總統是“普里克”,一方面又把他的老同事努德爾斯·庫克推薦給總統當顧問,因為庫克不僅“精於心計、虛偽欺詐、惟利是圖”,而且“陰險又滑頭”,“沒有不撒謊的時候”。約塞連對他的鄙夷可想而知。但當他為了使兒子逃避越戰時,又去找庫克幫忙。
人物簡介
阿爾伯特·塔普曼牧師是《第二十二條軍規》里的一個隨軍牧師,是做士兵思想工作的。他膽小,內向,自我保護能力很弱,曾一度對上帝的信仰失去信心,並打算在斯諾登的葬禮上當眾宣布放棄信仰。就在此時,他看見了遠處樹上的一個一絲不掛的身影(按約塞連的說法是“我還穿著膠鞋呢。”),以為是上帝派天使向他顯現,於是便感激涕零,認罪悔過了。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物,戰後卻遭到了更悲慘的命運:他的尿里有重水!為此他受到了調查、拘留、審訊和軟禁。
“一夥身強力壯的特務前來造訪並要拘捕他……他們不能說出他們是誰,更不能透露他們是為哪一個特務機構工作。他們沒有逮捕令。法律規定他們不需要那東西。什麼法律?就是那條他們根本無須引證的法律!”“他們宣讀了他的權利,然而又說他沒有這些權利。”於是牧師便身不由己地落入了當代“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圈套。牧師不僅為自己無法解釋的現象受到非法拘捕和審訊,還受到長期軟禁,使他的妻子守活寡。“他想妻子,……而且知道她也想念他。她很好,這是他每周三次得到的消息。可是不允許他們交談,連寫信都不行。……孩子們都好,孫輩們也都好。無論如何牧師對家裡的一切由於牽腸掛肚的思念而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以至發展為對即將臨頭卻又說不出名堂的大禍的恐懼。”“雖然他對上帝不斷地乞求,然而從那次以後存在於萬物之中的上帝再也沒有在他面前顯現。”
荒謬嗎?可笑嗎?這正是海勒要說明的問題。
誰又能料到,牧師的痛苦竟然是因為總統玩電子遊戲機時按錯電鈕引發的核大戰而結束的。由於他自身就是一顆核彈,戰爭起來後人們便連忙打發他回家了。在經歷了如此這般的磨難后,他似乎悟出了些什麼。牧師離開地底下的防核掩體回家時,約塞連見到了他並對他說“牧師,別出去!”“外面危險。戰爭。下來吧!”而這時牧師卻大叫一聲“操你媽!”不僅約塞連感到驚訝,連牧師“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這種話是從哪兒冒出來的。”然而這一罵卻激勵了牧師,“覺得精神大大地解放了,感覺格外好。”牧師這個受沒有麥卡錫法案的麥卡錫主義迫害的小人物的遭遇,叫人慾笑不能,欲哭無淚。
米洛·明德賓德在《第二十二條軍規》里就是一個投機倒把、內外勾結、精明透頂的商人。他當部隊食堂管理員時,曾絞盡腦汁,從西西里島以一分錢一個的價格收購雞蛋私運到馬爾他賣四分錢一個,再從馬爾他以七分錢一個的價格收購,並以五分錢一個的價賣給所在的部隊食堂,不僅獲利頗豐,而且贏得了馬爾他人的民心,撈到了大量政治上的好處,為他做買賣創造了便利條件。此人為了賺錢可以說是無所不為。他將用於充填救生衣的二氧化碳氣用來製造汽水冰淇淋,甚至將飛機上用於急救的嗎啡偷去賣錢。就是這樣一個人,戰後又利用軍隊和政府內的腐敗收買要員,將子虛烏有的“飛翼轟炸機”賣給了政府,使美國納稅人的錢就這樣流進了巧取豪奪的官僚和不法商賈的錢包里。
難道說就沒有人來管管這種事?有。美國政府成立了一個“道德規範部”,專門監督它的僱員。但若問這個道德規範部的主任是誰,回答是:“仍懸而未決,要等波特·洛夫喬伊出獄再說。”此處妙筆怎能叫人不發出若澀的笑聲?
薩米·辛格和劉·拉賓諾維茨是美國“老實巴交”的中產階級人物。薩米回國後上了大學,在《時代》找到一份工作,結婚,撫養妻子帶來的幾個孩子,與妻子恩愛相守。他沒有奢望,沒有野心,是美國社會的基礎和平衡力量。他對政治和社會遠不如約塞連那樣關心,但畢竟是知識分子,對蒂默大夫的一席話還是心領神會的:“社會上種種邪惡與不端行為正在各個地方無法阻止地成倍增長著,”而這“如同……動物與植物體內的惡性致命細胞無限增殖一樣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劉是與薩米類似的另一個代表人物。他戰後沒有上大學,而是靠辛勤勞動發家致富的。也許是由於作者本人是猶太人的緣故吧,劉這個猶太人的兒子對猶太人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家庭觀念身體力行。他年輕時雖然性行為方面放蕩不羈,但結婚後就不再胡來了。為了表現他的愛國思想,作者花了大量筆墨寫他如何懲治德國戰俘。與薩米一樣,他對政治的厭倦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對薩米說:“無論在什麼場合我都是無關重要的。除了在自己的家庭和個別朋友中間。所以從此以後選舉時我根本不想參加投票。……我不想讓兩黨內只會吹牛皮的龜孫們有一分鐘的得意,不想讓他們以為我喜歡看見他們為實現個人野心而取得的勝利。”
從傳統小說的角度來看,作者在薩米和劉身上花的工夫似乎過多。因為除了在事業發展上不同外,他們二人在總體思想、經濟地位、生活準則上都大同小異。兩個人中寫一個足矣。但是“現代主義把人物變成了觀念的象徵、哲理的形式,而後現代主義則進一步把人物變成一種觀念的代號、哲理的隱喻、類型的影子,一方面更加抽象化、寓意化、多義化了,一方面更加無個性、無差別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的話,這樣寫人物或許就是正常的。
利昂·塞爾澤曾總結性地評論道:“人們在分析約瑟夫·海勒新發表的經典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的主題與手法時,都毫不遲疑地稱之曰‘荒誕’。”在《最後一幕》裏海勒依然保持了他的這一特色,同時,他所擅長的黑色幽默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揮灑。
荒誕本指西方現代藝術領域裡的一個戲劇流派,起於本世紀中葉,其代表是愛爾蘭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這個劇是一個“悖論的隱喻”,人們明知他們所等待的戈多不可能到來,卻仍然要等待下去,而且不要問諸如“為什麼”、“合理嗎”這類問題,因為荒誕本身是無理的,卻又是大量存在的。寫“荒誕”的事就是起一個“悖論的隱喻”的作用。
黑色幽默的特點則是“用強烈的誇張到荒謬程度的幽默、嘲諷的手法,甚至不惜用‘歪曲’現象以致使讀者禁不住對本質發生懷疑的驚世駭俗之筆,用似乎‘不可能’來揭示‘可能’發生或實際發生的事物,從反面來揭示他們所處的現實世界的本質;以荒誕隱喻真理”,使讀者“透過這一片喧鬧、粗野、瘋狂雜亂的氛圍,從如許似是而非的反語,不露聲色的冷峻的嘲諷中悟出那使人困惑、使人啼笑皆非的專橫、殘暴,那捉弄人、折磨人、像夢魘般使人無法擺脫的荒謬”。
因此我們可以說,荒誕與黑色幽默是後現代主義文學戲劇里的一對孿生兄弟。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最後一幕》中的幾乎每一個事件里體會到。
例如,作為上帝的代言人,阿爾伯特牧師尿出了重水,從而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招來米洛將他的產品氚註冊了專利,還驚動了“小普里克”。一個獨立於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機構成立了,專門處理這個代號為“威斯康星計劃”的案子,總負責人竟然是1942——1945年間負責“曼哈頓計劃”的萊斯利·格羅夫斯中將。除特工密探和軍隊外,還動用了化學家、物理學家、核輻射學家、泌尿學專家、內分泌學專家、腸胃病學專家以及凡能想到的各類醫學專家和環境學專家。其中肯定還有昆蟲學家,因為後來他們經檢查研究,鄭重宣布牧師尿重水不是由於他被蚊蟲叮咬所致!真是一個科技最發達的國度啊。
再來看看那個將明德賓德和馬克森兩家結合到一起的驚世駭俗的結婚典禮吧。這兩家億萬富翁為了說明“即使在這個國家經濟蕭條的時期,美鈔也俯拾皆是;即便在貧窮的圈子裡,也還有浪費的餘地”,他們是這樣操辦婚禮的:向3500位各界名流和朋友發出用白金製作的請柬,包括總統(他始終沒有出席)和第一夫人,8個億萬富翁,340個千萬富翁,紅衣主教,46家國外出版機構的老闆和約塞連等;發出記者證7203張,雇侍者1200人,預備車位1080個;食物嘛,僅魚子醬就買了4000磅;結婚蛋糕高44英尺,重1500磅,耗資1107000美元。裝飾方面,購鬱金香1122000朵,鍍金木蘭葉5000片。這種事情看似荒誕,卻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的現實。《華盛頓郵報》在評論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的“盛大、奢美、華而不實”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都是對美國的定義”。
然而這麼一個“夢幻典範”卻是在骯髒污穢到了極點的港務局公共汽車終點站里舉行的。這種荒唐的安排與迪倫馬特《老婦還鄉》里那個腰纏萬貫的老嫗將她與她的“第九個丈夫”的婚禮放在“倉庫里舉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奢華淫逸、荒唐可笑到了如此地步,人類還有希望嗎?“什麼希望也不抱”,後現代主義對人類完全失去了信心。於是人類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他的最後一幕——滅亡。
總統為什麼沒有出席婚禮?他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廳里玩電子遊戲機呢。可他在得意忘形的時候按錯了電鈕,把美國所有的空中打擊力量,包括核打擊力量,全部發動了起來並投入了戰鬥。敵人在哪裡?誰也不知道。於是太陽變黑了,月亮變紅了,港口和附近海域的船都翻了。就這樣,不僅約塞連等一批《第二十二條軍規》里的人走到人生的“最後一幕”,人類也像在電影《翌日》里一樣,走到了盡頭。
後現代主義作品在結構上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不連貫性”。這種不連貫性“在許多層面上都存在,是文藝創作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過渡的一種努力。”
《最後一幕》結構鬆散。它共有34章,沒有傳統小說的開頭、高潮和結局,每章與每章、每節與每節、甚至有的每段與每段之間都存在著極大的不連貫性,似乎每章都能當“第一章”。這如同七巧板,誰能斷定哪一塊是“第一塊”呢?因為不論先擺哪一塊,都可以完成拼擺,一俟拼對完畢,便是一幅作者表達思想的完整的圖畫。
後現代主義作品在語言方面也有它的明顯特點,這裡舉一兩個例子。
。約塞連最怕的是死亡,可他又偏偏說自己是已經消亡了的亞述人。這樣他的名字Yossarian與“亞述人”Assyrian就在拼寫和讀音上幾乎相同了。這對他這個怕死的人來說,是個不大不小的諷刺。再說他的小名“約約”。yo?yo是一種圓形玩具,一般由木頭或塑料製成,上面繞一根細繩拉上拉下。不管那個圓形物離開手掌多遠,繩子用完它便會順著繩子回到手裡。這yo?yo便是約塞連的命運:可憐的約塞連,在軍隊里他一再往醫院裡逃,為的是逃出“第二十二條軍規”設置的圈套,逃過死亡,結果呢,還得上天扔炸彈;不打仗了,他又進入各種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圈套。但這和他怕死一再住院一樣,無論有多大法力,都沒能逃出如來佛的手掌。
。文學被認為是高雅的藝術,海勒作為文學大家,對這一點當然明白。但後現代主義卻置此於不顧。《最後一幕》里當然有游龍飛鳳般高雅流暢的描寫和敘述,但也有另一個極端。例如在第十九章里我們就能在某一段的16行里讀到15個“他媽的”。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在後現代主義的作品里,“‘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對立,小說與非小說的對立,文學與哲學的對立,文學與其它藝術問題的對立,統統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