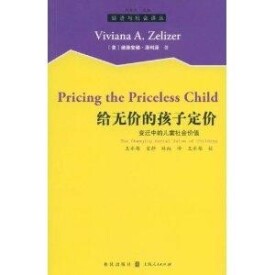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
作者:(美)澤利澤 著 王水雄 等 譯
叢書名:經濟與社會譯叢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43214798
出版時間:2008-11-01
版次:1
頁數:218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關注的是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關於兒童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過程,即經濟上無用而情感上無價的孩子的出現過程。通過透視兒童問題的巧妙視角,作者細膩探討了那個時期人們對兒童死亡的態度的改變、童工立法的鬥爭、兒童工作的分化過程、兒童保險的推行、兒童意外死亡的賠償以及兒童的領養與買賣等。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深刻的理論話題,這就濁:孩子的社會文化屬性,他們在道義上的“無價性”如何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由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則?從而最終指向一個更為深切的理論關懷:社會如何“大於”市場?
編輯推薦《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媒體推薦澤利澤的研究令人過目難忘,她的分析意涵深刻,而行文卻沉著簡練。本書對一個重要的主題進行了極富想像力的大膽探索,相信在我們歷史學家中一定會尋獲知音。——Nancy Tom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g
作者:(美國)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Zelizer) 王水雄 譯者:宋靜 林虹
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社會學家,現任美國經濟社會學學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知名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關注經濟的文化與道德維度。1985年因《給無價的孩子定價》一書而獲得美國社會學界的至高榮譽C.Wright Mill獎。
主要代表作品:《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金錢的社會意義》、《親密關係中的買賣》。
1994年版前言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從憤怒到紀念:兒童生命的神聖化
第二章 從有用到無用:童工之上的道德衝突
第三章 從童工到兒童工作:重新定義經濟世界的兒童
第四章 從體面的埋葬到恰當的教育:兒童保險的情況
第五章 從意外殘廢到意外生育:對兒童的法律權衡的改變
第六章 從兒童農場到兒童黑市:兒童市場的變遷
第七章 從有用到無用再回到有用?兒童價值衡量的呈現模式
譯後記
本書是我穿越經濟生活廣袤平原之旅程的第二步。該旅程奔向的是社會性可變的市場模型-在多個層面上探討社會關係和文化如何型塑人們的經濟活動和制度秩序。它發端於人壽保險市場的研究,然後是對兒童市場的研究,現在則研究多途徑的貨幣的社會性使用。在《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Morals and Markets: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the United States)(1979)中,我對經濟生活的研究理路尚為初步階段,證明的是非經濟因素在美國主要經濟制度發展中的作用。我選擇人壽保險是因為它強有力地體現為貨幣利潤與神聖關懷的交叉匯聚點。保險企業家是如何成功地確立起生命和死亡的貨幣等式的呢?對生命投保的歷史進而也成為經濟行為中非經濟維度研究的一個案例。
《道德與市場》強調的是對人壽保險的文化反應,考察了人類生命的貨幣衡量態度的改變,以及在人壽保險發展過程中風險和投機的文化界定轉變的影響。它還包括了結構因素的效應,考察了比如說,從喪失親人之扶助的饋贈式體制到市場體制轉變中的張力。人壽保險不僅僅革新了死亡的意義,也革新了對其進行的管理。朋友、鄰里和親戚,這些在18世紀緩解寡婦經濟窮困的關係,被牟利的層級制所替代。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Pricting the priceless Child)繼續了《道德與市場》所開啟的路徑,更直接地考察了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市場或價格(被界定為經濟價值)與人性及道德價值之間的互動。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關注的是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主要是)美國社會關於兒童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過程,換句話說,就是經濟上無用而情感上無價的孩子的出現過程。這個過程恰恰是中國社會在短短的過去60年中所經歷的-60年前,孩子(特別是男孩,又特別是在鄉下)的出生被視作是未來勞動力的光臨,父母充滿了老有所靠的欣喜;現如今,生養一個孩子就顯得太貴了!而且許多為人父母者將來也不指望他們。孩子的價值因此更多地體現為情感上能夠給父母帶來的滿足,但是由於這種滿足的所費不菲,異常地不符合如今大行其道的市場邏輯,根據澤利澤在本書中的詮釋,孩子的生養進而被獨特的社會文化因素建構出了神聖性。
最初從上海大學劉玉照副教授那裡拿到這部著作的英文書稿的時候,就深深地為澤利澤巧妙地透視兒童問題的視角所打動。作者關注了20世紀之交美國人對兒童死亡的態度的改變、童工立法的鬥爭、兒童工作(兒童“好”的工作與童工)的分化過程、兒童保險的推行、兒童意外死亡的賠償,以及兒童的領養與買賣等。作者的這些探討非常之細膩,它們共同地指向一個深刻的理論話題,這就是:孩子的社會文化屬性、他們在道義上的“無價性”,如何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由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制。在這個理論話題背後,還有一個更為深切的理論關懷:社會如何“大於”市場?這部著作通過關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交互關係,社會結構因素和價格、價值的相互影響,來呈現現代社會貨幣的相對乏力及其重要性相伴相生的過程。這就更為細緻地回應了齊美爾的經典著作《貨幣哲學》。
第一章 從憤怒到紀念:兒童生命的神聖化
孩子的死:從接受到義憤
在18世紀以前的英格蘭和歐洲,一個嬰兒和一個年幼孩子的死亡都是一件小事,對此的態度通常混雜著不關心和對事實的接受。正如蒙田所提及的那樣,“我有兩三個孩子在嬰兒時期就死了,在此,沒有過度的悲痛,也沒有遺憾。”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對英國家庭的調查中發現,在16、17世紀以及l8世紀的早期,當非常年幼的孩子死亡之時,沒有證據表明人們會花錢辦一個悼念會,甚至也不會戴黑紗。父母很少參加他們孩子的葬禮。根據菲利普·阿雷茲(Philippe Aries)的說法,在法國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直接埋在後院里,正如人們今天埋葬貓和狗一樣。死亡之後,即便是富人家庭的孩子也會被當作是乞丐一樣來對待,他們的屍體“被縫進粗麻布做的裹屍袋中,扔進巨大的公共墓穴”。l5世紀至17世紀之間,歐洲的上層階級選擇埋葬在教堂里;公共墓地則提供給那些非常貧窮和非常年幼的死者,無論“他們自身或者家庭作為優雅的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是否選擇教堂作為他們葬身之所”。
社會歷史學家們指出,美國殖民地時期的父母從來不會冷漠地對待他們孩子的死亡,但是他們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對孩子的超然和分離狀態。比如說,l8世紀的許多父母,將他們的新生兒指稱為“它”或者“小陌生人”;年幼孩子特別是嬰兒的死亡將被哀悼-但卻被順從地接受了,對孩子的悼念儀式是冷靜而剋制的。正如有人在1776年所說的那樣,“失去一個新生兒的確是夠難受的,但是這是我們必須交的稅”。另一個孩子會被生出來替代前一個失去的孩子。很明顯,給新出生的孩子取前一個剛剛去世的哥哥或姐姐的名字,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但是到了19世紀,在悼念孩子的問題上產生了劇烈的變革。在英格蘭、歐洲和美國社會的上層和中層的家庭中,孩子的死亡在所有的死亡中成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寬恕的事情。在其頗有洞見的對美國文化的分析中,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描述了1820年到1875年之間“哀悼的擴大”,特別是有孩子過早死亡的中產階級對該問題的關注浪潮。父母一向克制的傳統讓位給了悲傷的盡情發泄。喪失孩子的父母親的情感傷痛成為一個新的文藝類型-安慰派作品的重要主題。哀悼者指南指導父母如何應對“搖籃空了”的人間慘劇,大量的故事和詩歌非常詳細地描繪了喪失孩子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傷痛。一個非常有名的紐約牧師,西爾杜·庫易勒(Theodore Qer)牧師發表了《空了的嬰兒床》作為紀念作品,以懷念他死去的孩子喬治亞(Georgie)。之後,他收到了來自同樣喪子的父母數千封的同情信。安·道格拉斯引述了其中的一封:“親愛的先生,如果你有空去看看阿萊干尼墓地,你將會看到‘一朵花’放置在三個小墓穴之前:安娜7歲;塞迪5歲;莉莉3歲。他們都是在六天之內去世的,都是因為猩紅熱病!老天有時候甚至會順從我們的傷痛,讓我們聽到其中之一在別處正在成長。”到了1850年代中期,為了這些“家庭小聖徒”,特別的棺材被設計出來,它有著舒適的內層,裡面還有標示牌。一把鎖和鑰匙替代了“冰冷的螺絲釘和起子”。
喪失孩子的新情感的產生部分地是因為對待死亡的文化反應發生了轉變。菲利普·阿雷茲將其指稱為19世紀的“情感革命”。在此,“他人的死亡”,特別是近親的死亡被界定為是壓倒性的人間慘劇:“面對死亡,其可怕性在自身面對的時候,還不如在面對他人之死亡的時候。”年幼孩子的死亡則是其中最為糟糕的事。勞倫斯·斯通注意到,在19世紀的英格蘭,正如在美國一樣,“孩子之死帶來的極度悲傷,既是社會風俗,也是心理事實”。在義大利、法國和美國,大型都市墓場為小孩舉辦的喪禮迅速成為喪禮藝術中最受關注的項目。法國的父母通過在其孩子的墳墓上豎立精心製作的雕像來頌揚他們的孩子。阿雷茲說道,“如今我們來看它們的時候,正如我們閱讀美國安慰派文學的詩歌一樣,我們可以意識到面對這些孩子的死亡,人們變得多麼痛苦。這些長期被忽視的小東西,被當作像遠近聞名的大人物一樣來對待了。”
到了19世紀後期,孩子悼念的革新進一步延展。社會歷史學家認為,在那個時候,英格蘭和歐洲較低的社會階層家庭採納了中產階級家庭養育孩子的模式,他們對待孩子的死亡也同樣變得情感脆化了。而這一改變甚至更為深刻和激烈。所有因喪子而產生的父母在家庭內的悲傷逐漸成為公共關注的對象。通過製作精美的雕像來悼念已然不夠;無論貧富,所有孩子的死亡都被看作是一個無法容忍的損失。當維多利亞時代的情感主義者在頌揚孩子的時候,在20世紀之交,美國的社會活動者決定儘可能地避免孩子的死亡。正如一個改革者解釋的那樣:“孩子有權利獲取生命的公平機會。如果父母不能夠用這些機會裝點他們的生活,顯然政府就應該有責任介入。人世間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粗暴地摧毀一個強健的生命而未感受到它作為主體的存在。”這樣,對死去孩子的祭儀逐漸轉變成保存孩子生命的公共行動。
拯救孩子的生命。
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的行動開始於19世紀後期。一個新的醫學領域和專門的機構被創建起來,以治療兒童疾病,確保兒童身體健康。1881年,亞伯拉罕·雅各比(Abraham Jacobi)醫生組建了美國醫學聯合會兒科部(the pediatric Section of the Ainerican Medical Society)。6年之後,美國兒童醫學聯合會(the 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成立,其宗旨是“發展有關嬰幼兒的生理學、病理學和治療學”。1890年代中期,大多數大城市至少有一家兒童醫院。在內科醫師發現了腐壞牛奶和兒童健康之間的關係之後,安全牛奶運動被一些慈善家和市政當局推行開來。牛奶站和供應網點建立起來,在此一些貧困的母親可以以成本價購買,有時甚至可以免費獲取巴氏滅菌牛奶。他們同時還可以從受過護理訓練的服務人員那裡獲取有關孩子照顧和衛生學方面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