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春綺
錢春綺

工作中的錢春綺
錢春綺先生今年89歲了,和體弱多病的老伴住在上海西北郊的一套3居室內。房間不算小,但堆了很多東西,感覺氣氛有點凌亂。錢先生育有兩女一子,兒子遠在美國,小女兒定居香港,都不在身邊。大女兒在同城的另一端,平時往來也很寥寥。談起日常起居,錢先生挺樂觀,"我有老伴嘛,老伴身體不好,我自己照顧自己也行。"
錢先生是國內不多的在世德語文學翻譯前輩之一,譯有德法著名詩人作品多種。作為翻譯家的錢先生名滿天下,但他做翻譯卻是半路出身。錢先生一生行止以上世紀60年代為分水嶺,分屬醫生和翻譯兩個角色,而以翻譯達到自己人生成就的頂峰。
對於這一人生轉折,錢先生自己的解釋頗具戲劇性。他說自己是五官科醫生,60年代轉單位時想轉入皮膚科,卻因人事糾葛而未能實現。生性崇尚自由、不願受拘束的他乾脆辭職,掛冠轉而做起了專職翻譯。其實錢先生搞翻譯早在50年代就已經開始,據錢先生自己回憶,1952年他翻譯出版海涅詩集拿到 8000元稿費,而當時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不過幾十元。同時期他還著有醫學書籍多種,如《中耳炎》、《小兒腦膜炎》、《組織療法》、《簡明小兒耳鼻咽喉病學》、《組織療法概說》、《喉結核及其化學療法》、《白喉的診療和預防》、《睡眠療法》、《無痛分娩法》等10種醫學書籍。
但文革十年,圖書出版業陷入了低潮,錢先生也無書可譯,境況頗為困窘。文革結束后,譯事復興,錢先生才得以復出。可時過境遷,90年代后稿費制度和圖書出版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自由撰稿人的處境越來越難。"我也是靠積蓄生活,自由職業,沒法維持生存的啊。"錢先生對此感觸良深。錢先生自己也是在 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館后,情況才稍稍穩定,現在一個月能拿到1600元工資。但被錢先生戲稱為"翰林院"的文史館,"也不是什麼人都能進去的。"

錢春綺部分譯作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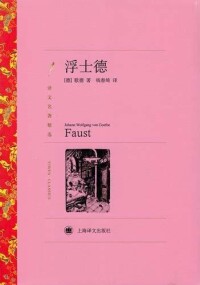
錢春綺譯著
錢春綺先生從小喜愛文學,至今寫詩不輟,積累有大量未刊詩稿,總計有5到6本,其中長詩2部,十四行詩2部,每部100首。"寫詩是自己的事",除了初中在大公報發表過幾首詩作外,其他詩他從未發表。錢先生寫詩鍛煉文筆是次,主要目的在於排遣胸臆,澆心中之塊壘。翻開這些泛黃的筆記本,大部分詩都標有寫作日期,從50年代到90年代不一而足。這些詩題材廣泛,有對時代風雲的感慨,對長逝親人的追念、對老友的牽掛,也有寓意深遠的詠物詩,如一首名為《墨魚》的短詩:"你有滿肚子的墨水/卻寫不出一首好詩/你只會把清水攪渾/攪得一團烏煙瘴氣。"
問錢先生喜歡外國哪些詩人,他想了半天肯定地說是拜倫,"因為他有激情"。錢先生說歌德不如海涅有激情,波德萊爾的詩用詞簡單,馬拉美的就不好懂。中國古典文學中他喜歡李後主,近代的喜歡蘇曼殊,"他們的作品自然,一看就懂"。對於如何提高翻譯水平,錢先生也認為多讀多寫是唯一途徑,"不懂的要多查多問"。說到求知之難,錢先生告訴我上海郊區佘山修道院有個神甫希臘文和拉丁文都很好,"上海懂古典文字的人很少了,這樣的人難得呀"。
如今錢先生年事已高,已很少出門。但他對時事並不隔膜,對文化界、出版界的動態都很了解。錢先生向我打聽一些翻譯同行的消息,還問起我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的情況,說她的作品涉及變態心理學,很不好讀。這很是令我吃驚。
儘管如此,錢先生還是寂寞的。他有一本經常摩挲手邊的書--《上海作家辭典》。書是1994年出版的,10年過去了,許多錢先生的老友相繼離世,作家協會也寄來了重新修訂此書的通知。書的最後一頁上寫滿了錢先生抄錄的這兩年文化人士的離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時間和原由等。遠的如“錢鍾書,1998年12月19日,北京,88歲”,近的如“韋宜君,2002年1月26日逝於北京協和醫院,84歲,腦溢血”。今年離世的有三位:“杜宣,2004年8月23日,上海,91歲”、“陸星兒,2004年9月4日,胃癌,55歲”、“葉治,2004年5月27日,80歲,癌”。
天色將暮,夕陽透過窗戶打在錢先生閱讀用的放大鏡上,折射出一抹最後的亮色。屋裡很快暗淡了下來,唯有錢先生的朗朗笑聲還在耳邊回蕩。
願錢先生永遠快樂、長壽。
專訪翻譯家錢春綺:冷兵器時代的博學
雲也退
“查拉圖斯特拉在長期孤獨之後,精神充沛,想下山前往人世間,做個像太陽一樣的施予者。”
翔實的註解布滿了三聯書店去年12月版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內文。幾乎每頁都有注,幾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點校筆法和紮實的考據功夫。《查拉》在德國本土擁有不同的註釋本積十累百,相關的解讀著作更是不計其數,但進入中國以後,不管是徐梵澄譯本還是尹溟譯本俱失之無注,最新版的中國人民大學楊恆達教授的譯本下了大力氣,惜乎也只有寥寥幾個註釋。
錢春綺老先生用了多久加的這些註釋,他自己也說不清。重要的是,這部在他83歲時接下的翻譯任務終於順利修成正果了,不到30萬字的書,他加了五六萬字的註解,天曉得尼採的這部曠世天書是怎麼被一位偏居上海市北一隅的老人給譯到如此程度的。愛讀文學譯作尤其是外國詩歌的人沒有幾個不知道錢春綺的大名,但是,有誰能夠想象,這位不懂上網、不會電腦打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完全保留著“冷兵器時代”的工作方式的翻譯大家,至今還保持著如此旺盛的思想活力,還沒有享盡竟日伏案筆耕之樂?
錢老的房間亂作一團,百科全書、詞典、各種原版詩集和譯著五方雜處。老伴去世以後,他的生活節奏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亂的依然亂著,規整有序的依然規整有序——他的頭腦,他一輩子不曾改變的心境。
▲錢老,您翻譯的海涅當年能拿到8000元稿酬,這在五六十年代可是一個天文數字了吧?
△呵,是啊,你要知道,我當時從醫院辭職(錢老本行是學醫的,畢業之後先後在醫院的皮膚病科和耳鼻喉科工作過),在別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國家醫院,那是鐵飯碗哪。但是我不擔心,我喜歡翻譯,相信我完全能靠稿費養活自己。
▲您選擇做您熱愛的工作……或者說,選擇了自由,但是現在翻譯稿費可少多了。
△這是個普遍現象,不過,《查拉》的稿費還是不少的,一千字有一百元吧。所以也不要總責怪現在的譯者不認真,不肯加註——加註多累啊,辛辛苦苦加了一堆注,字也沒多算多少;再說出版社也要控制成本,你的字多了,他們的開支也大。
▲所以我們才越發覺得您不容易啊。《查拉》好歹還是近幾年翻譯的,我讀您的《惡之花 巴黎的憂鬱》,那書的翻譯年頭在二三十年前,可是您幾乎在《巴黎的憂鬱》的每一條散文詩下面都加了注,有關於比較閱讀的提示,有關於愛倫·坡等人對波德萊爾的影響的提示,有關於波氏作品某個母題的提示,非常專業。您是查了很多資料呢,還是真的如此博學?
△當然是要靠多讀別人的書啊。其實我引的都是別人的觀點,我讀了許多國外的研究資料,法文的,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很多很多。像《浮士德》這樣的書,德文原版下面的註釋比正文要多一倍以上,必須這樣,我總是努力往那個方向靠攏。
▲您哪兒來的這麼多參考資料呢?您可是從50年代就開始翻譯的吧?有家學淵源嗎?
△倒也說不上。是這樣,1949年以後,外國人在中國待不住,一批一批都回去了,留下大量的書沒法帶走,那時候我買了許多,都堆在家裡。後來文化大革命,工宣隊想來抓我的把柄,到我家找了一通,什麼都沒找到,我本身又沒工作,沒有罪名可以羅織,怎麼辦呢,就把我滿屋子的外國書抄走許多,那時候損失了有一萬多本吧。
▲這麼多,可是您搜集資料、利用資料的本事著實讓人嘆為觀止,絕對可以給現在的譯者樹立楷模了。
△翻譯水平的高低,受制於許多因素。我喜歡詩歌,14歲起就寫詩,我後來翻譯的絕大多數也是詩歌。譯詩,當然一定要準確理解原文的意思,要有辭書,但是我們的辭典編纂水平比國外差得很遠。我翻譯《查拉》時大量利用了日語辭書,日本人的辭書水準是一流的,比如德日辭典,那裡面的解釋就是比很多德漢辭典精確。
我舉個例子,一般“palme”這個德文詞,大家都譯成“棕櫚”。我在翻譯的時候覺得有問題,因為尼采把它形容為“會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種下粗上細、筆直筆直的棕櫚樹會有“跳舞”的感覺嗎?我查日語的譯本,這個單詞譯作“椰樹”,我覺得這是正解:斜著伸向海邊,隨著海風搖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樣。但是,在中文辭典里是沒有“椰樹”這個意思的,“椰樹”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參考了其他日語辭書,才知道這個詞在使用中經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後半部分“palme”的,在這裡,就體現出我們在研究上下的功夫大不如人家了。
▲是這樣……但是求得這種精確的前提是您得懂許多語言,我們都很佩服您的語言天才。
△我在中學里上過德文課——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學,風氣極其自由開放,在三四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我能在圖書館里借到批判蔣介石的書。法語我是聽廣播學的,當時維希政權在上海開有一個“法國呼聲”電台,用一個法語音質極為純正的中國播音員播音。日語也是跟著電台自學的——自學,日語叫“獨習”。
▲我只能說,太不可思議了。
△翻譯就需要掌握儘可能多的語言,因為西方豐富的文化都在它豐富的語言里蘊含著。我也主張詩人譯詩,我自己譯詩就受益於從小的寫詩訓練。但問題就在於中國詩人往往外語能力不好。照我說,要譯那些經典的外國詩,應該連拉丁文都得學會,那是進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鑰匙。還有聖經,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聖經我都收藏著,一遍一遍地讀,還橫向比較;即使同樣是中文聖經,天主教聖經和新教聖經的譯名都不一樣。這些東西一定要鑽研,鑽得越深越好。
▲您的博學完全是古典式的:古典式的培養造就,古典式的運用,古典式的鞏固和提升。除了懂這麼多外語,您的中文功底又是如何打下的呢?我讀您的譯詩覺得一般都相當自由,似乎不拘於格律,不像有些翻譯家那樣講究音節數量的嚴格對應,但在您的文字的背後又看得出有深厚的古文基礎在支撐。
△你對私塾有了解嗎?我小時候上的是私塾——不讀《三字經》、《百家姓》什麼的,我那時讀的是《論語》、《孟子》、《大學》、《左傳》,雖然也是死記硬背,但是,背誦確實是很有益處的。我最喜歡《左傳》,我覺得左丘明的筆法是最經典的,他不用虛詞,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暢達。當我把《左傳》里的篇目背下來之後,在翻譯中那些凝練的詞句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到頭腦里。
▲中西兼修,感覺您這一輩子就在書堆里充實而快樂。我注意到,您挑戰的詩都是經典中的經典,特別需要下大功夫去註釋。
△我在中學時候就仰慕波德萊爾的大名,後來才去翻譯《惡之花 巴黎的憂鬱》;《浮士德》也是在中學里就讀過的。我翻譯這些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量閱讀外國資料。西方人重視翻譯,既講效率又講精確細緻。比如我手頭的一個《巴黎聖母院》的英譯本,每個地名、每個典故、每個歷史事件都有註釋。我翻譯《查拉》也大量借鑒日語譯本里的資料——日本人真的很有一套。
錢老的博學完全是古典式的。雖不大出門,卻並非閉目塞聽之人,他還知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尼采箋注集系列里也即將要出版一個《查拉》的箋注本——和那個一本正經的大工程相比,錢老簡直就像一個手工作坊里的劬勞野叟,在滿屋子發黃的書本和散亂的紙頁中摸爬,尋找他想要的答案。他譯著早已等身,但從沒想過要挑戰什麼權威或申請一個“錢氏出品”的譯著專利,事實上,正是一生近乎固執的無爭無求,才成就了“錢春綺”這面略顯寂寂的金字招牌。
錢老的下一個主攻方向依然是德國的文學大師——我們希望他能在今年、也是他的米壽之年完成荷爾德林詩選的翻譯,或可作為一種紀念,儘管他說,他這輩子還從來沒有過生日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