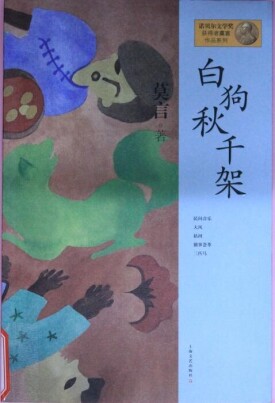白狗鞦韆架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發表的一部短篇小說
《白狗鞦韆架》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於一九八五年四月發表的一部短篇小說,小說以倒敘手法,敘寫一個離鄉十年的讀書人井河回鄉與昔日戀人暖重逢的故事。
由《白狗鞦韆架》改編的電影《暖》,獲第十六屆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大獎。
《白狗鞦韆架》這篇小說開頭描述了井河和暖十年後的重逢;做了大學教師的井河衣錦還鄉,暖變成一個貧窮邋遢的普通村婦。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孩暖由於一次意外而從鞦韆上跌下來變殘疾,最後嫁給啞巴,艱辛的農作使她變為粗俗的農婦。井河後來上大學,眼瞎的暖嫁給鄰村的啞巴,生了三個小啞巴。結尾寫暖騙過丈夫去鎮上買布,白狗把井河引到了高梁地,暖提出了一個讓井河無法拒絕的要求,就是想要一個會說話的孩子。到此,小說戛然而止。它以近乎殘酷的筆調展現了暖人生歷程的起伏轉折。昔年能歌善唱的暖日日面對的是口不能言的四個啞巴,出語粗鄙的村婦“個眼暖”曾經是嫵媚可人的青春玉女。小說的力量來自結尾,前面的屈抑都是為了此刻的迸發和升騰。小說採用描述一個讀書人回鄉的見聞及感受這一慣常寫法,用夾敘夾憶的寫作方式將過去發生的事和現在的情景交錯敘述,人物和故事漸漸浮現。
一九八四年寒冬里的一個夜晚,莫言在燈下閱讀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國》。當讀到“一條壯碩的黑色秋田狗蹲在那裡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時,腦海中猶如電光石火一閃爍,一個想法浮上心頭。便隨即抓起筆,在稿紙上寫下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個句子就是收入本集中的《白狗鞦韆架》的開頭。這是莫言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的字樣,從此之後,“高密東北鄉”就成了莫言專屬的“文學領地”。莫言也由一個四處漂流的文學乞丐,變成了這塊領地上的“王”。“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地理名稱的確立,在莫言的文學歷程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暖是一個粗俗、潑辣的農婦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因年少時與井河一起盪鞦韆而被槐刺扎瞎了右眼,破了相。“鞦韆架事故”使暖被迫嫁給鄰村的一個啞巴,而且生下的三個兒子也是啞巴。在無愛的婚姻中,暖默默承受命運之神的蹂躪:嫁給一個啞巴已是不幸,更不幸的是三個孩子也是啞巴。她身心受到傷害,言語粗俗且尖酸刻薄,對自己的處境是深為不平乃至憤激。同時,她婚姻不幸,加之辛苦的勞作使她成為一個粗俗、潑辣,又讓人同情的農婦。
暖對自己的悲劇命運不僅有深切而痛苦的體驗,有過無可奈何的幻想和思索,更有積極的但卻是一廂情願式的反抗,那就是在小說結尾:寫暖瞞過丈夫去鎮上買布,在高粱地里要井河睡她,向井河求種”在小說中,看到井河和暖結識了路過他們村的解放軍文藝兵蔡隊長,就纏著蔡隊長要跟他去當兵。蔡隊長的話讓井河和暖充滿期待,但結果是當兵未遂,期望成空。
面對如此落魄的命運,暖實質上並沒有絕望,這就是小說中情節發展至高潮時出現的那個事件:暖設“計”在高粱地向井河“求種”。暖的“求種”心理反映了暖對自己的悲慘命運的強烈反抗,暖希望與昔日戀人同居,索要一個健康的孩子來給自己黑暗的命運增加一點亮色,給自己的精神一點慰藉;“求種”行動充分顯示了暖希冀改變自己不幸命運的主觀努力,不管成功與否,這個行動本身突顯了在現代文明人身上很少見的但卻在暖的身上表現出來的原始生命力。
於是,對於無法預料的神秘遭遇,暖只好默然承受。當機會出現時,又能藉機反抗。對於無法改變的事實,她默默承受;對於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和事件,暖付出了積極的努力和反抗。暖信命而不認命,對自己不幸的命運擁有強烈的抗爭精神,從未喪失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念,努力要成為把握自己命運的主人。這種對待命運的態度向我們詮釋了一條真理:在命運面前竭盡人力。
井河是以還鄉,及內心深處對暖的愧疚的一個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因為鞦韆架事故讓她變成了“眼暖”,使井河內心對暖有愧疚,後來暖嫁給了鄰村的一個啞巴;井河求學離開了高密東北鄉,十年後,成為大學教師的井河,衣錦還鄉。當井河和暖在家鄉窄窄的田間小路上相遇,井河心中的美麗單純、富於幻想的少女,令當時許多農村青年“想得美”的暖變成了邋遢得令井河不敢相認的村婦。這時,本就因盪鞦韆偶然的事故而身背良心十字架的井河,內心更感沉重;當井河了解到暖因此被迫嫁給了一個啞巴,又生了三個小啞巴的現實時,井河受良心譴責的沉重感更強烈了。在溫情脈脈的敘述中,“負疚”和“懺悔”成了這篇小說的基本旋律。
啞巴是暖的丈夫,是一個有著滿腮黃鬍子和兩隻黃眼珠的剽悍男子。他生性霸道、蠻橫、毫無溫情可言,性情粗野讓人厭惡。啞巴與井河第一次見面時瞧不起井河,他用翹起的小拇指表示著對井河的輕蔑和憎惡。後來當明白井河不是敵人時,啞巴卻又顯得非常親熱。啞巴沒有給暖一點人身自由,不讓暖與外界有交流,否則就會招致啞巴的懷疑甚至毒打。
《白狗鞦韆架》不僅表現了敘述者“我”的痛苦,也展現了鄉村少女暖的悲劇人生。解放軍宣傳隊蔡隊長是以啟蒙者和過客的雙重形象出現的,他的到來激起了暖對外在世界和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憧憬和嚮往。但是隨著他的離去和暖眼睛的失明,暖的夢想破滅,她還不如戴望舒筆下的尋夢者,“你的夢開出花來了,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時候”。她的夢想始終沒有實現。無奈嫁給啞巴生下三個不會說話的兒子后,她只有這樣一個世俗的肉慾要求,“我要個會說話的孩子……你答應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應就是害死了我。有一千條理由,有一萬個借口,你都不要對我說”。
《白狗鞦韆架》瀰漫著一種傷感、悲涼的氛圍,作為從鄉村走出來的知識分子,返鄉的“我”發現的是鄉村的破敗凋敝、黯淡凄苦,以及其中接二連三麻木隱忍的靈魂。“我”和鄉村、村民有著很深的隔膜,遭遇了和村民無法溝通的尷尬。敘述者“我”感受到與外在世界的不兼容,同時面對暖又遭受內心靈魂的衝突。小說體現了現代悲劇,即人與社會的對立。小說延續了“五四”以來鄉土小說的創作基調。主人公對外在社會的感知總是透露著不同程度的疏離、惶恐和不確定感,流露出現代人所感覺到的人與社會的緊張和對抗;而在內心又承受著道德與慾望的種種折磨,給讀者展示了一個個痛苦的靈魂。
《白狗鞦韆架》是用強烈的民間敘事話語再現了農村生活的悲苦和可憫,“高密東北鄉”無休止的勞作壓抑、湮沒了一個女人曾有的純情和她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與幻想,膨脹了她內心的恨意與絕望,“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出路。
苦難意識
作品中的人物的苦難色彩隨時間漸漸蔓延,並且越來越濃烈。主人公們追不上彼此的腳步,只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命運的支配下努力喘息,用回憶織補時間的縫隙。在小說中,圍繞著暖的人物關係主要有暖和“我”、暖和蔡隊長、暖和啞巴,每一對關係都是一段悲苦的命運。十幾年前沒有破相的暖“婷婷如一枝花,雙目皎皎如星”,“我”很喜歡暖,可是竟成了她悲劇人生的始作俑者。在推著暖盪向鞦韆高處的同時,卻將暖的人生推到了谷底。莫言選擇摧毀最能代表女性美麗的部分———瞎了暖的眼睛,而且只是一隻眼睛。這樣的暖沒有辦法對自己的容貌視而不見,更沒有辦法對自己黑色的人生視而不見,她只能把對“我”的思念與怨恨埋在心裡,用殘缺的視覺靜候命運的安排。“我”歸鄉與暖的偶遇重新喚醒了暖心中的回憶,暖用冷漠的態度壓抑著情感,用僅有的一隻眼睛穿透了“我”內心的虛偽,暖裝作什麼都不在意,實際上她卻什麼都在意。
贖罪意識
自從“我”求學離開以後就沒有回過高密東北鄉,“一晃就是十年,不短也不長”。人們總喜歡以十年作為人生的節點,離鄉的十年,其實一直是處於自我逃避的狀態,不敢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和給暖造成的嚴重傷害,“我”希望用新的生活環境沖淡罪惡感。十年的時間讓“我”成長了,一直說工作忙的理由無法再洗脫糾結的心境,於是決定看一看久別的家鄉,見一見內心沒有放下的暖。回鄉后,家鄉的自然風景讓“我”心情放鬆下來,而白狗的出現則讓“我”的心重新緊繃,在見到了已被生活操磨成標準鄉村婦女的暖后,內疚與懺悔油然而生。在看見暖背著厚重的草捆時,“我”接受了她不需要幫忙的事實。這種初見的慌亂和不知所措讓“我”很愧疚,當再次走到橋上,希望那時候的自己勇敢些,“我很希望在橋頭上能再次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麼一大捆高粱葉子,我豁出命去也要幫她背回家”。是“我”親手將曾經喜歡的暖推下了苦難的懸崖,儘管他一再努力暗示自己與暖已經有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以後也不會再有交集,而且暖好像生活得也不錯,但是這種自我安慰只能暫時緩解心情,他放心不下所以才會去暖的家裡看一看,結果啞巴的行為使他了解了,其實暖一直生活在陰霾和痛苦中。內心的罪惡感始終縈繞著他,無法消散。“我”一直期望以某種方式補償暖,但是卻不知道怎樣做。暖給了贖罪的方式———通過和暖生一個健康的孩子洗刷“我”給她造成的傷害。但這是否會再次陷入苦難的輪迴,作者拋下了謎團。
白狗意象
白狗意象白狗的形象貫穿了整篇小說,白狗成了一種符號,只要有暖出現的地方就一定有白狗的身影。多年前高密鄉純種的白色狗絕跡了,這隻白狗被抱回來的時候“有出30塊錢買的,但被拒絕了”。它的性情不同於一般鄉村裡的野狗,也註定了它對於主人公的特殊意義。白狗是歷史的窺探者,它陪伴了“我”與暖最美好的年少時光,經歷了“我”對暖盪鞦韆時犯下的錯,看到了暖日後與啞巴生活的不幸,在“我”返鄉時,成為了找到暖的嚮導。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都有白狗的痕迹,十二歲的白狗如同高齡的老者,用它習慣性的漠然表情迎接著“我”的歸鄉,它彷彿知道“我”的歸期,所以靜等“我”的到來,沒有驚喜,沒有哀傷,只是一次一次的把“我”引到暖的身旁。“我”懦弱離開的十年,在暖身邊的只有這隻白狗,暖很信賴它,想說的話不能與啞巴丈夫和孩子講,便都告訴了白狗。白狗收藏了暖的心事,成為了她最親密的陪伴。白狗也是“我”贖罪的替身,暖不再健康后,“我”給暖寫過信,但也只是寫信而已,並沒有回到家鄉看看真正被自己傷害致殘的暖到底生活如何。當勇敢的暖選擇獨自承擔時,“我”就心安理得的推開了這個重負。白狗成為了時間的信使,讓多年後的“我”不斷穿梭在過去與現在的時光里,尋找著關於彌補過失的答案。白狗給出了最好的方式———不離不棄陪在暖身邊。
色彩意象
人物外貌描寫方面,小說中使用了很多表示色彩的語句。黑,牙齒潔白”,這是標準的鄉村婦女的形象,“她用左眼盯著我看,眼白上布滿血絲”,從暖的眼神中就知道她的日子過得並不幸福,因為生活的勞累和壓力長滿了血絲。當“我”讓暖辨認自己時,她“黝黑的臉上透出灰白來”,這反映了暖見到“我”后內心的掙扎變化。描寫啞巴的外貌時這樣寫道“出來迎我的卻是滿腮黃鬍子兩隻黃眼珠的彪悍男子”,暖這樣的丈夫使得“我”明白了暖輕描淡寫她家庭狀況的假象,暖年輕漂亮時,追求她的是英俊瀟灑的蔡隊長,而今的枕邊人不僅是個啞巴而且面目猙獰,這又增加了暖的悲劇色彩,讓人唏噓命運的無常,為暖感到心疼和憐惜。暖的孩子出現時“見三個同樣相貌,同樣裝束的光頭小男孩從屋裡滾出來,站在門口用同樣土黃色小眼珠瞅著我”,與啞巴一樣的黃色眼珠表明了三個小男孩受到了他爸爸的遺傳,都是不會說話的啞巴。對於暖來說,一系列的打擊如狂風暴雨般呼嘯而至,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絕望。暖越是生活在泥淖里,“我”當年犯下的錯越顯得不可饒恕。這些色彩的描繪沒有明麗的基調,都是昏暗冷淡的,與主人公的冷色命運相吻合。
景物色彩的描摹方面,“我”叫暖去盪鞦韆的那一晚“鞦韆架默立在月光下,陰森森,像個鬼門關,架后不遠是場院溝,溝里生著綿亘不斷的刺槐樹叢,尖尖又堅硬的刺葉上,挑著青灰色的月亮”。這個夜晚的月光不是鮮亮的黃色的而是“青灰色”,奠定了陰暗的基調,是一種不好的兆頭。陰森森的鞦韆架也成了鬼門關,暗示著這一次兩個人的玩耍將會釀成大禍。從鞦韆盪出去以後,前後的人生則從快樂的天堂進入了痛苦的鬼門關。莫言巧妙地利用了色調鋪墊情節的發展。在“我”去找暖的路中景色被描寫成“以過石橋,看見太陽很紅的從高粱顆里冒出來,河裡躺著一根粗大的紅光束,鮮艷的染遍了河水,太陽紅得有些古怪,周圍似乎還圍繞著一些黑氣,大概是要落雨了吧”。這紅得不自然的顏色如同暖水深火熱的生活———熱辣辣的灼燒。太陽是從高粱顆粒里冒出來的,這與最終暖要求與“我”發生關係的高粱地地點重合,可惜太陽周圍的黑色是要下雨的徵兆,人物的命運也終將被黑色的雲逐漸吞噬呈現出悲情色彩。
《白狗鞦韆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農村成長史的微縮膠捲。他個人的文學才華早已盡藏其中。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程光煒

《白狗鞦韆架》
1981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1985年,因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而一舉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轟動。1987年,擔任電影《紅高粱》編劇。1988年,發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1989年,出版長篇小說《食草家族》。1993年,出版長篇諷刺小說《酒國》。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豐乳肥臀》。1999年,出版長篇小說《紅樹林》。2001年,出版長篇小說《檀香刑》。2003年,出版長篇小說《四十一炮》。2006年,出版長篇小說《生死疲勞》。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蛙》。2011年,憑藉《蛙》獲得茅盾文學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6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2019年,創作小說《等待摩西》。2019年,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2020年7月31日,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