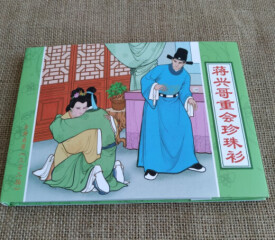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是一篇白話短篇小說,收集在明代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說》)中。小說寫蔣興哥與其妻王三巧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寫的是普通市民中發生的婚變,情節跌宕起伏又充滿人間溫情,體現了積極的時代精神。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講的是一個跌宕起伏又充滿人間溫情的故事。
蔣興哥外出經商,留下年輕貌美的妻子王三巧兒獨守空房,糧商陳大郎偶然得見王三巧兒就心心念念地放她不下,遂與牙婆設計勾搭上了王三巧,三巧兒不堪寂寞,也趁機偷歡,臨別時王三巧贈送他一件蔣家祖傳寶貝珍珠衫,蔣興哥在返鄉的途中見到了穿珍珠珍的陳大郎得知姦情,到自家門前首先責怪自己重利輕別離,然後把三巧兒騙回娘家和平休妻。
三巧兒再嫁吳縣令家做妾,屆時蔣興哥送上當年王家的十六箱陪嫁。后蔣興哥因官司牽連,恰逢由三巧兒的後夫斷案,夫妻得以重會,二人百感交集,使吳縣令深受感動,遂讓他夫妻破鏡重圓。
那陳大郎與王三巧兒分別後繼續做生意,回家去取本錢,其妻平氏發現了那件珍珠衫,料是件是非之物,就給他偷偷收起來了,陳大郎尋不到珍珠衫就猜疑平氏拿了,夫妻大鬧了一場,陳大郎負氣離家去做生意,路遇劫匪受了驚嚇,加之得知心上人三巧兒已遠嫁他鄉,兩氣夾攻,不久就病故了。
其妻平氏奔喪前來便被困留在此地,后經媒人說和,帶著那件珍珠衫再嫁,那丈夫不是別人,正是蔣興哥,那件珍珠衫又回到蔣興哥手中,是為“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主要人物有蔣興哥、王三巧、陳商、平氏、吳傑等。王三巧兒是一個不貞的婦女形象,作者並沒有過分指責她。她是一個非常單純、而又充滿了青春活力的少婦。蔣興哥是王三巧兒的丈夫,他在對妻子不貞的問題上,顯得很寬容,對妻子的行為表露了一種理解。他們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的休書所署時間為成化二年(1466),小說創作時間當在稍後的時間,但肯定不會晚於16世紀。生活在16、17世紀之際的馮夢龍將此篇編入《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之前,已有題作《珍珠衫記》的單行本流傳。萬曆間宋懋澄的筆記《九籥集》也載有這篇故事,只是角色均無姓名。馮夢龍編纂的《情史類略》即轉錄了《九籥集》文字。究竟是小說演衍了宋懋澄的筆記,還是宋氏據小說的情節縮寫,已無法考定。但當時的吳江派戲劇家葉憲祖《會香衫》雜劇及明末清初的袁於令《珍珠衫》傳奇都是據小說改編,則是有跡可尋的。
卷首詞:《西江月》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盪,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閑得意。
評蔣興哥新婚詞:《西江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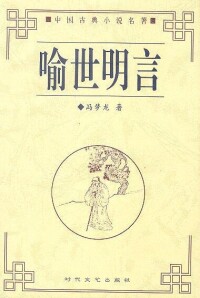
喻世明言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歌頌了蔣興哥理解人、尊重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吳縣令成人之美而舍己之愛精神,具有平等待人的思想。小說作者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的變化,並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揚這種超時代的人文精神,不能不說馮夢龍已具備先進的文學觀。他認為:“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古今小說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序山歌》)。他筆下的主人公是下層民眾。
在封建禮教極為濃厚的時期,故事乍看起來,為人不理解,即便是今人看來要衝破這一思想牢籠,也是需要勇氣的。
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今人不能接受的有這麼幾點:首先是能原諒偷情的妻子。蔣興哥外出經商,妻子王三巧兒獨守空房,糧商陳大郎偶然得見王三巧兒就“心心念念地放他不下”與牙婆設計勾搭上了王三巧,三巧兒不堪寂寞,也趁機偷歡,陳大郎臨別時王三巧贈送他一件蔣家祖傳寶貝-珍珠衫,蔣興哥在返鄉的途中見到了穿珍珠珍的陳大郎才知道姦情,到家門前首先責怪自己是“商人重利輕別離”,然後是把妻子騙回娘家,和平地休了她,三巧兒再嫁吳家時,蔣興哥送上了十六箱陪嫁。因官司牽連,由三巧兒的後夫吳縣令斷案,才得夫妻重會,百感交集,由此感動了吳縣令,讓他夫妻破鏡重圓。不會賞花的人則會摘花獨享,花會蔫,美會很快消逝;會賞花的人往往是遠遠觀花,花會爭妍鬥豔,長開不敗。更何況人呢?蔣興哥理解人,尊重人,正是作者所要歌頌的。要達到這一思想境界,不是很容易的事,應該具備平等待人的思想,在當時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今天,把妻子戀人當作私有財產一樣看的人是大有人在,封建社會賦予男人夫權,維護其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如今存在這一現象,正表明社會意識進步不大,當然也給經濟發展緩慢有關。幾千年來廣大下層民眾仍然貧窮有關。
其二,三巧兒的後夫吳縣令,竟能成人之美而舍已之愛,這也是現代人難以做到的。今人懂得愛是奉獻,但不富有的人們是無法把愛與奉獻結合起來的,更何況從古到今,官與民從來是不平等的,索取的是官,奉獻的是民,然而,文中的縣官不是簡單的一個清官就可概括的,而是具備超時代精神的人,他能尊重人、關心人,特別是下層平民,不要說在等級禁嚴的封建社會,就是在今天,也是應標榜的楷模。吳縣令之所以能成人之美,在於愛情是專一的,見三巧兒與前夫有情,他懂得強扭的瓜不甜,更加之三巧兒是妾,本來就是富餘的人,他主動退出不失為明智之舉。
由此可知,作者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的變化,並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揚這種人文精神,不能不說馮夢龍已具備先進的文學觀。他認為:“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摘自《古今小說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摘自《序山歌》)他筆下的主人公是下層民眾,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保持了話本的特色,除它具備通俗的,喜聞樂見的形式外,更有它為說教提供了現實生活的範例,反映生活的真實性的一面。真實為藝術的生命,作品的“真”首先表現在人物心理狀態的真。王三巧偷歡的過程中,反映的心態是極為真實的。“忽見陌關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觸景生情,這隻不過見春色而已,佳人思婦就不能止乎禮,更何況王三巧有與陳大郎一見鍾情之緣,加之做小買賣的薛婆有意“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並設計把王三巧推入失去理智的狀態中去。寂寞維耐的等待,在當時交通不便、信息全無的時候,蔣興哥出門后又染疾在身,耽誤了歸期,上久等的王三巧喪失了信心,已就喪失了理智,這為戀心若渴的陳大郎提供了機會。王三巧偷情最後被蔣興哥原諒,被故事的作者原諒,這跟人性天理思想有關。正如王夫之說“人慾之大公,天理之至”,體現了那個社會的時代精神。因此,蔣興哥休妻娶妻的心理過程也是可信的。
社會環境中的社會心態反映也逼真。外出經商是勤於生計,他對妻子說:“常言道:‘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棄了這行衣食道路?”薛婆牽線搭橋是唯利是圖,她詆毀蔣興哥,獻身說教,極盡挑逗之能事,言行污穢醜陋不堪,這與他的小商小販見利忘義的身份有關,王三巧再嫁吳縣令是作妾,一夫多妻的社會現實為吳成人之美打下伏筆。蔣氏已娶陳大郎的媳婦為妻,王三巧背叛他的心理得到平衡,為破鏡重圓墊定了心理基礎。當王三巧與蔣氏,抱頭痛哭時,吳縣令對王三巧的行為難道沒有嫉妒之心嗎?當王三巧嫁吳縣令時,蔣氏還送上十六個箱籠,本為王三巧所用物品,權作賠嫁,“傍人曉得這事,也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獃的,還有罵他沒有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這正是社會環境的真實寫照。
其次表現在情節構思的真。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詩句。在當時是確實存在的社會現象,但重利又是生活所迫,背井離鄉情不由衷。這個交代是為合理展開情節墊定了基礎。陳商與王三巧私通是情節的開始。根據前面心態的分析,王三巧的行為是人慾戰勝理性的行為,這行為在特定的情況下發生是完全可能的,最終被人所諒解可以作為佐證。到蔣氏與王三巧偶然相遇,抱頭痛哭,夫妻情是藕斷絲連。“連絲”就是十六個陪嫁箱籠,蔣氏當初送予王三巧作陪嫁物,可謂以德報怨,為團圓結局打下了伏筆。大團圓結局,即使情節發展自然真實,又使結局合符中國人的傳統審美習慣。文中插入陳商之死,蔣氏娶陳商之妻平氏,反映了因果報應的思想,有些牽強附會之嫌,但迎合了當時社會懲惡揚善的道德觀,這種處理方式也是科學的,許多偶然性中,它隱藏著發展的必然。多行不義必自斃的觀念被人普遍接受,反映出時代觀念的真實性來。
“三言”中有許許多多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和離奇曲折的故事被戲劇影視所採用,在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廣泛的表現,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拍成了電影,《十五貫》、《白玉娘忍苦成夫》被搬上戲劇舞台,深受觀眾的喜歡。在明代,作者憑自己先進文藝觀,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演繹出這樣動人的故事,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形象意義是深遠的。
馮夢龍(1574一1646),明代文學家、戲曲家。字猶龍,又字子猶、耳猶,別號龍子猶等。長洲(今蘇州)人,少為諸生,晚年以貢生歷官丹徒縣訓導、壽寧知縣。倡導言情文學,抨擊偽道學。雖工詩文,但主要致力小說、戲曲及其他通俗文學的研究、整理與創作。小說方面,除編撰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外,還增補羅貫中的《平妖傳》為《新平妖傳》,改寫余邵魚《列國志傳》為《新列國志》。戲曲方面有《墨憨齋定本傳奇》,其中自撰《雙雄記》《萬事足》二種,改訂湯顯祖、李玉、袁於令諸人之作十餘種。另編有時調集《桂枝兒》《山歌》,散曲選集《太霞新奏》,筆記小品《智囊》《智囊補》《笑府》《古今談概》《情史類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