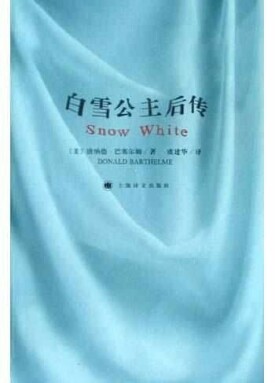白雪公主後傳
2005年巴塞爾姆所著的書籍
《白雪公主後傳》是美國作家唐納德·巴塞爾姆創作的長篇小說。《白雪公主後傳》摒棄宏大敘事,將故事情節完全打碎,進行重組與改編,嚴重變形的故事人物表現出後現代社會個性缺失、信仰崩潰、精神匱乏的異化人物形象。
該作品是女權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白雪公主後傳》創作的宗旨顯然是要顛覆經典童話故事中反映男性審美的“純潔、天真、柔弱、等待拯救的公主”形象和“高貴、勇敢的拯救者——王子”的形象。《白雪公主後傳》中看似荒誕的故事情節實際上是巴塞爾姆這位敏感的作家對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女性以及所有男權社會中女性悲劇命運的真實寫照。
白雪公主接受過三流大學的教育,她與七個男人同住,組合成一個現代“家庭”,日復一日地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為他們做家務,成了他們的家庭“煮婦”。她鬱鬱寡歡,卻無法從平庸中得到解脫。絕望中,她甚至盼望著能有一次帶性醜聞的冒險,來打破單調乏味的生活。但她的行為十分荒唐:將長長的黑髮拋在窗外,以期吸引異性的注意,引來某個“王子”,順著頭髮爬上窗檯,將她帶出困境——一個夢求女性解放的朦朧願望,卻陷落在依附男人的俗套中。
七個矮人——都是些精神上的“矮子”——靠生產中式兒童食品和為大樓保潔謀生,每天攪拌蒸煮鍋里的食物,沖洗大樓。他們喜歡與白雪公主住在一起,她漂亮、性感,雖有怨言仍為他們做家務,也讓他們輪流在淋浴室同她一起洗澡。這八個人都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什麼,都有點煩躁不安,都有點怨氣怒氣,對個人的前途十分茫然。他們都有點神經質甚至歇斯底里,徒然地想從生活中找到意義,但最後只是多受了幾份“窩囊氣”。他們對自己的處境缺少認識,把怨氣出在他們的“頭兒”比爾身上,最後將他絞死,然後又接納了街頭流氓霍戈。這樣,直到故事結束,白雪公主與七個“矮人”仍然在以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為背景的瘋狂世界中生活著。
充當“王子”角色的保羅,沒有一點值得讓人等待的品質,也根本沒有能力擔當“拯救者”的角色,最後循世進了修道院,穿上修士的道袍后又成了觀淫癖。但白雪公主在他被毒死後,仍然常常去他的墓地上撒上幾朵菊花。她很傷心,也很無奈,世界上已沒有“白馬王子”能把她從低俗無聊、庸碌無為的生活中帶走,向著想像中的“崇高”升華。
七個男人都喜歡白雪公主,但誰也無法滿足對方的感情需要。他們既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也沒有表達自己感情的有效辦法,惟一的行動是買一條紅色的浴巾和浴簾,試圖通過這一行為使“家庭”生活增色,博得白雪公主的歡心,從而改變已經出現裂痕的人際關係。他們沒有發現生活中問題的根本所在,採取的只是無關痛癢的舉措。
20世紀的社會的動蕩、不斷的戰爭、難以預計的災難也對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前半期,通訊革命和運輸革命帶來的運動、速度、光和聲音的新變化導致了人們在空間感和時間感方面的錯亂,同時,宗教信仰的泯滅使自我意識產生了危機,在這種狀況下,藝術家本人常常未能完全理解社會環境的紊亂如何使世界產生了劇烈震蕩,並且把它弄得看起來像是一堆碎片。藝術家們不得不以新方法重新聚攏這些碎片。
巴塞爾姆自幼受到做建築師的父親的影響,他喜愛繪畫和建築。巴塞爾姆30歲時成為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終身迷戀視覺藝術,認為藝術的自我意識在於探索自身的媒介如色綵線條構圖的性質,巴塞爾姆用文字做了同樣性質的探索,他甚至在字體和版面上費盡心機以達到某種繪畫的效果。在巴塞爾姆那裡,形式成了小說“身份”的宣言。他從現代畫家那裡得到啟示,把小說當作展示超現實意念的畫布。韋尼·斯坦格爾在評論巴塞爾姆的作品時,把他稱作“文字畫家”。認為巴塞爾姆常常將他的故事視為畫布,在其中他添上古怪的漫畫式的情景,然後用語言濃墨重彩地進行渲染,又用細膩的筆法進行暗示。巴塞爾姆是個文字畫家,相當於一個文學中的行為派或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用那些大塊色彩來激發某種情緒,或表現某種精神狀態,而不是闡釋作品的意義。但是,巴塞爾姆意識到,文字攜有線條和色塊不能明示的意義,並感到作家有義務對他創造性地再現的現代生活中的衝突與混亂進行評述。
巴塞爾姆的“拼貼畫”創作及其意義——以《白雪公主後傳》為例,對現代藝術和當代文學兩方面的興趣,將他引上了條創新之路,在作家自己的作品的結構和語言上尋找一種文學上的現代藝術的對等物。
在巴塞爾姆發表最初作品的20世紀60年代,年輕一代作家正呼應“小說死亡”的宣言,尋找新的風格和體裁對抗小說傳統。“殘片”式地表現人的零碎認識和科學、哲學、社會學的殘破權威,成了一些先鋒派作家的時髦。他們通過這種小說結構,強烈地表達著這樣一種認識:任何現實都是局部的,而不是完整的;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流動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
巴塞爾姆認為,“拼貼原則是20世紀所有傳播媒介中的所有藝術的中心原則。”後現代拼貼式結構所形成的效果帶有明顯的隨意性,作為“後現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巴塞爾姆無非是把人類意識中本有的矛盾狀態展現出來:意識中的圖像從來就是打破經驗歷史而處於共時性之中無數無關聯的甚至矛盾的斷片。巴塞爾姆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過一句被廣泛引用的話:殘片是他惟一信任的文學形式。
《白雪公主後傳》中的七個“矮人”是作者根據他熟悉的萊斯大學的七名男生的性格特點塑造的,他們的原型都是現代美國青年,都感到與社會格格不入,都對現實不滿,都牢騷滿腹。儘管如此,巴塞爾姆的人物塑造並不求助現實生活細節的描寫。他抽去了這七個人物的血肉,將他們的性格特徵抽象化,使他們成為喪失意義的後現代生活的象徵。他們不斷地用語言證明自己的存在,發表一段古怪的宣言式的道白,對某一無足輕重的事件表達似乎帶點哲理其實不著邊際的看法,然後很快淡出。除了空洞的教條,他們並不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
白雪公主
女主人公白雪公主22歲,是一位高個子的性感美女,畢業於比佛學院,選修過《現代女性、權利與義務》、《個人資源》等課程,卻淪為紐約市一座公寓里七個矮人的“家庭煮婦”,輪流跟他們在浴室做愛。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雪公主,憎恨這一被規定的“煮婦”角色,她開始思考,對自然世界中男性統治的現象,她在感情上正經歷著某種程度的憤怒,女性意識的覺醒使她渴望另一種生活,她開始嘗試寫“詩”,風格是“自由體”;她有種馬上要干一番什麼事業的神態。白雪公主期待的另外一種自由的生活是她心中的王子有一天會出現,為了吸引到心中的王子,白雪公主甚而主動出擊了,她用黑如烏檀的頭髮垂下窗子,夢求以“性感”吸引男人,解救自己。
保羅
保羅王子是一個有著貴族血統的無業遊民,一再逃避解救白雪公主的使命,他怯懦的行為消解了他王子的形象和貴族的血統。保羅的貴族血統雖然在後現代社會已退去光環,他卻依然認為貴族的血統能給予自己自信和勇氣,一直期待著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他曾反覆思考,他可是王子,肯定沒錯。有時他真的完了,但一想到他自己的血統,就能鼓起勁來。那血是藍的,也許是這個正在衰老的世界上最藍的。
保羅怯懦的行為清楚地表明他無法承擔王子的使命——把白雪公主從七個侏儒男人的禁錮中解救出來。保羅選擇了逃避,躲在內華達西部邊遠地區的一家修道院,他還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借口:如果出生在1900年以前,他就可以騎著馬戰鬥,打擊那個時代的地主和腐敗的政府官員。二十世紀下半葉,年輕人擁有馬的機會是多麼渺茫啊。後來保羅決定不再逃避王子的使命,他回來了。但是受後現代社會的反英雄傳統影響,保羅不敢直接應對挑戰,他在白雪公主的住處附近挖了一個地穴,安裝了一套複雜的監控系統,通過鏡子和訓練好的狗長期監視白雪公主。保羅的行為讓白雪公主極度失望。
最終保羅替白雪公主飲下毒酒,陰差陽錯完成了王子的使命,獲得解脫。
《白雪公主後傳》主題思想:異化世界中的悲憫救贖
在《白雪公主後傳》中,作者通過對傳統童話故事的徹底解構,呈現出了一系列被現代社會所異化的人物形象。
人自身的“異化”
在《白雪公主後傳》中,男性形象的異化是最明顯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七個小矮人和王子保羅。在格林童話中,七個小矮人是正義、善良的化身,他們以自己勇敢無畏的精神解救了美麗的白雪公主,然而在《白雪公主後傳》中,他們卻成了一群被異化的現代男性,他們無聊、庸俗、空虛,每個人身上都充斥著 誕、虛無、絕望和低靡。他們是一群喪失了自我,喪失主體性,喪失了自由精神的非人形象。如作品中的比爾,他不喜歡別人觸碰他,也不喜歡和人打交道,他是一個空虛寂寞,缺乏行動力並且喪失個性的人,就像亨利所說“他想乾的好像就是坐在遊戲室里,洗洗紙牌,投投飛鏢,干這類事情,而不到外面去施展自己的潛能。一個顯然被選中的生命原則的寵兒竟然如此懶散,如此不義,如此無道。”
作為七個小矮人領導者的比爾尚且如此,可想其他人又是如何的空虛和頹廢了。除此之外,他們在極度空虛的內心深處還充斥著邪惡和下流的慾望。如亨利所說“現在有必要去向她求愛,得到她,穿上這套乾淨的西裝,把指甲一個個剪好,說些討好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安撫腹股溝的這個突起。”不僅僅是亨利有這樣的邪惡慾望,幻想著找一家妓院的克蘭和鑽進阿米麗亞裙內的喬治等其他人也都有這種邪惡下流的慾望。作品中的小矮人們已失去了人身上所應具有的個性、行動力、理想等人性,他們已經異化為空虛無聊,缺乏行動力和理想的畸形人物。
另外,保羅作為作品中的另外一個主要人物形象,也是一個自身異化的形象。他雖然體內還流淌著王族的血液,但是身上卻絲毫找不到王子所具有的高貴氣質,缺乏去追求美好生活勇氣,是一個懦弱無能、充滿著阿Q精神的畸形人物。他幻想著要比他自己的父王更具有創新精神,有更加宏大的志向,但是卻“不清楚具體到底是什麼。”他幻想著也許他應該走出去,與某個需要他的美人私通。將她救出,橫放在他坐騎鞍前,飛馳而去。”但是面對白雪公主放在窗外的長發時,他選擇的卻是阿Q式的自我逃避和自我安慰。他渴望白雪公主,但是他卻沒有 行動的能力,只能成為一個觀淫癖者。
《白雪公主後傳》作品中的王子已經不同於格林童話中的王子形象了,他已經是一個心靈麻木、缺乏行動力的畸形、異化的現代人物形象。《白雪公主後傳》作品中所表現出的人物自身的異化正是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一個主要特徵。
人際關係的異化
在《白雪公主後傳》作品中所表現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人與人之間沒有正常的溝通,在他們身上,那種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一個個符號的化身,在這個異化的社會中,他們早已變成了毫無感情的“非人”。
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是這樣朝夕相處的他們,仍舊是無法溝通,他們之間好像只是一種很冷漠的同居關係,他們從來不知道白雪公主在想什麼,同樣白雪公主對他們也是一無所知,就連比爾為什麼最近不去敲她淋浴室的門她也不知道為什麼。雖然他們七個都不能滿足白雪公主的感情需要。他們甚至沒有表達自己感情的有效辦法,而且也沒有任何改變現狀和出現裂痕的人際關係的能力。他們缺乏一種感情上的溝通,缺乏一種友情、親情甚至愛情,即使在家裡這個最容易溝通的地方,理解對他們來說也成了問題。在異化的社會中連這種家庭中最基本的關係都被異化了,白雪公主每天忙著自己的家務,小矮人每天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異化充斥著每個角落,影響著每個人。
當白雪公主和小矮人同時出現在電影院的時候,白雪公主有點心神不安,她擔心的是那種稱之為她的“名聲”的東西,但是周圍的人並沒有對其有任何的關注,當她被告知她和小矮人這樣的組合在鄰里並沒有引起任何特別關注的時候,她感到異常失望,由此也可看出,人與人關係之間的冷漠,人們並不關注彼此,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甚至在作品結尾,當比爾被絞死的時候,其他人表現出的冷漠也是不容忽視的,比爾受絞刑是因為他有罪,如果他有罪,他就得被絞死。他犯有滅國罪和瀆職罪。很明顯他不想被絞死。但幸虧霍戈也在場,帶著他的皮鞭。這樣就加快了進度。作者筆下的人際關係就是在這種人與人的冷漠情感中被異化了,從而喪失了人的主體性。
異化主題凸顯的深層內涵
作品中的人物之所以被異化除了社會因素之外,很大的原因是其本身信仰的缺失和人性的缺失。經歷過二戰后的美國人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寧靜,而是陷入了一種空虛、荒誕和無意義的狀態。
該作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文中充斥著荒誕和虛無、絕望和低靡。作品中被異化的人物形象,其實其原型都是現代人,他們對現實不滿,但卻沒有改變現實的能力,他們根本不知道生活的問題所在,只是採取一些無關痛癢的措施,他們空虛、荒誕,是一群生活在現實中被異化的行屍走肉。在這個人性畸形發展時代,巴塞爾姆以其尖銳的筆鋒,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創作形式,為讀者展現出了荒誕世界中孤獨存在的異化者形象,使大眾看到了人的普遍異化,從而喚醒那些已逐漸被異化的現代人,喚醒他們內心 深處那些被現代社會的塵埃埋藏已久的寶貴人性,使人性從自然化向社會化轉變中保持著和諧的節奏,從而在現代社會中獲得人性的重生。
戲仿解構
《白雪公主後傳》對19世紀初德國民間童話《白雪公主》進行了全面戲仿和徹底解構。戲仿是尋求新的表現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童話《白雪公主》的故事只為巴塞爾姆的文字拼貼提供一個大的框架,作者故意打斷故事的延續性,用滑稽怪誕的小段描述精心拼組,讓文本成為碎片的拼貼,將意義進行延伸,同時又將意義進行消解。巴塞爾姆創作的《白雪公主後傳》,背離了小說傳統表現方式,甚至在一些作品里採用大量非文字的表達方式,例如把各種表格、插圖以及目錄等與文章拼貼在一起。因為他認為這個世界早已顯得支離破碎,混亂不堪,這種拼貼的方式或許最能反映荒誕的世界。巴塞爾姆用嘲諷的筆調,揭示了美國當代生活的醜陋荒誕,人心不古,童話破滅。它正是物慾至上的資本主義原則下社會生活的變形寫照,反映了當代人的精神危機。正如白雪公主早已意識到的——“‘我’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代。這個世界本身也出了毛病。”
片刻展示
《白雪公主後傳》不符合傳統的閱讀心理期盼,離人們熟悉的小說模式和定義相距太遠,讀起來只是些文字片斷,似乎不知所云。其實,採用連續的“片刻展示”技巧,不讓故事朝縱深發展,正是巴塞爾姆小說實踐最顯著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他小說創作最成功之處。在他手中,文字和意象被當作建築材料,而不是概念的承載工具。
《白雪公主後傳》沒有章節序列和標題,不到200頁的篇幅被切割為100餘塊類似章節的片斷,以換頁和篇首字母大寫為標記。作者以克制的低調進行敘述,將經過裁剪的片斷一幕幕地進行演繹,迅速交替。每一片斷有它自己的中心:一個特殊的行為,一個場景,或某人物的一番表白。片斷之間有些無規則的聯繫,合成一個七零八落的故事,其中也朦朧出現一個間斷性的跳躍的故事發展。很多瑣碎的細節,很多想像、誇張、扭曲的感受,由不同的敘述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講述。
通過白雪公主和“矮人們”的一段段自我表白,為他們的生存狀況和感情狀況做出粗略的交代。一幅幅漫畫式的文字特寫,為讀者提供了荒誕的,但同時又是生動的西方當代生活的片斷。文本中,充滿古怪的句子碎片,這些碎片取自民間故事、電影、報紙、廣告和學術刊物,取自學術和文學中的陳詞濫調,如對具體文學體裁和慣用手法的戲仿,關於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偽學問的題外話,對弗洛伊德和存在主義模式的戲謔描述,以及空洞的具體詩。時不時跳出一個杜撰的辭彙;有的一頁紙上只有粗體的幾行毫無關聯的詞句;甚至在第一部分末強行插入了一張調查問卷。這些碎片拼貼在一起,創造出不協調的對比,經常產生駭人的滑稽感,並且形成了一種獨特、令人吃驚的韻味。但在零零碎碎的片斷背後,卻涌動著一種強烈真實的情緒,始終如一地主導著小說的敘述。這便是作者對待現實的“後現代”態度。巴塞爾姆將各種奇特的、相關或者無關的事物或對話進行並置,讓它們在碰撞中產生火花,誇張地表現當代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荒誕。他具有滑稽模仿、創造黑色幽默的出色才能,既能逗讀者發笑,又能把他們引向洞見。他的代表作《白雪公主後傳》為讀者了解後現代作家的文化態度和表達技藝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詞語意象
“家庭煮婦”一詞是作者巴塞爾姆根據“家庭主婦”這個詞杜撰出來的,是男人給女人規定的角色,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呆在家裡,像馬一樣努力為主人幹活,打掃衛生、做飯的“煮婦”;另一方面,是給男人當馬騎,做男人性交工具的“煮婦”。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儘管婦女運動發展如火如荼,社會習俗、教育、道德規範等卻在齊心合力,極力幫助男人維護著傳統的女性的不公平地位。白雪公主的悲劇命運直接體現在男人極力看重的“家庭煮婦”這一角色定位上。
混亂的語言
語言是人際交流的重要的工具,語言表達功能的喪失正是預示著人與人之間會日趨無法交流,人際關係會日趨冷漠,從而更進一步凸顯人際關係異化的主題。
如面對白雪公主的頭髮,丹尼的反映卻是對垃圾發表了一通議論“這個國家人均製造的垃圾從1920年的每天 2.75磅增長到1965年的每天4.5磅。”
侏儒表達出來的信息沒有了任何意義,只是一堆堆的語言符號。這樣混亂的語言,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和交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
情節設置
除了語言的混亂之外,作者對情節的設置也是極具跳躍性,沒有任何時間的線索,傳統的線性的時間被徹底瓦解,被瓦解后的時間碎片又被重新匯聚在“現在”,“現在”成為包容過去和未來的唯一時間存在的標誌,從而出現了情節的巨大跳躍性。
例如,在回憶白雪公主受教育情況的時候,情節就跳到了保羅的一段自言自語。又如關於小矮人拿保羅打字機這一情節在作品中反覆出現多次。時間在《白雪公主後傳》中已經沒有了傳統的意義,它反覆而模糊,人物處在這樣的情節之中失去了自身的過去和未來,人與自身過去和未來的脫軌恰恰意味著人不能認識自己,不能得到發展,只能一步步走向萎縮。同時也恰恰體現了時間對人的異化。
《白雪公主後傳》通過運用認知詩學及敘事學理論解讀作品,文本呈現了豐富的內涵,讀者得以建構一個後現代語境下人類生存狀態的現實,作品的意義也由此得以體現。
——馬瑩(淮南聯合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白雪公主後傳》在敘事方法上完全打破打破傳統小說的線性寫作模式,用獨特的敘事手法將文學寫作、政治報道與社會調查等多種元素拼貼起來,賦予了作品的強大召喚結構,不但在形式上給讀者混亂跌宕的審美享受,支離破碎的語言也給人一種不確定感,激發讀者不斷探尋文中的意蘊和奧秘,給讀者更廣闊的闡釋空間。
——劉曉暉(大連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唐納德·巴塞爾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