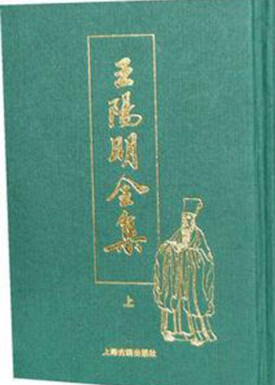大學問
明朝王守仁作品
《大學問》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2年12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守仁(王陽明),這本書是王守仁(王陽明)的綱領性哲學著作,被其弟子們視為儒家聖人之學的入門教科書。《大學問》乃陽明重要教典也。陽明者,中國明代之大儒王守仁是也。文武周公,孔孟朱熹,陽明承前啟後,其地位、作用若斯也。縱觀中國三教九流之學,陽明乃一顆璀璨明珠,此喻決不為過也。在三間聖殿中,孔子居中,左釋迦右老子,反之亦然,此陽明之公開觀點也。陽明儒學功底深厚,有能力及膽識出入佛老,不僅辨析名相而且身體力行,最後融三家於一爐,拈出致良知之三字以為萬能鑰匙,謂時時處處按良知行事,則適得其所、百發百中,真乃大明咒、無上咒也。

王守仁
陽明子答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慾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慾之蔽,以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問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
答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悌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問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
答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慾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 止於權衡,失其准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問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說何也? ”
答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問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
答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嘗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干,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 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問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
答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 也,如雲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雲者,非若后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 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 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 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 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余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成,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盪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只以自誤,無益也。
德洪說:《大學問》一文,是我們老師這一學派的重要教科書。學者剛進門的時候,必會首先以這一理論對他進行教育,使他聽了以後就能明白,我這顆心的靈知覺性,出不了人們的倫理道德和事物的客觀規律這一範圍,擴充知識、實踐理則的功夫,也就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內容上。學者如果真能腳踏實地地去實行,那麼他聽過一次就感到一次的親切體貼。老師常說:“我的這種觀點,如果有人能馬上接受,他只按照這種道理去做,就會直接達到聖人的境界。拿它跟古代的經典去作比較,也沒有不相吻合的地方,因此不必再去博學多聞中尋求。”學生中有人請老師把它寫成文字,老師回答說:“這種意思必須諸位口耳相傳,如果用筆寫下來,使人當作文章去讀,那是沒有任何利益的。”嘉靖丁亥年(1527)八月,老師受朝廷委任去平定廣西思恩和田州的叛亂,在出發前,弟子再次要求寫成文字,這次老師允許了。寫成以後,老師把文章託付給德洪說:“《大學或問》這幾段內容,我並不是不願意讓共同學習的士人都能聽到這種義理,可是我怕給敵人幫了忙、給強盜送去糧食,所以不願意輕易寫出來。”因為當時還有持異端邪說而把異說看作正確理論的人,所以老師有這種說法。現在老師已經去世了,他的音容笑貌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我們這些弟子們各以自己的見解著書立說。學者稍微見到一點本體,就沾沾自喜去作徑超頓悟的玄虛之談,而再也不作內心反省、克己成聖的功夫了。他們說:“一旦見到本體,一抬腳跟就能超越聖人。”他們鄙視老師講的“誠意、格物、為善、去惡”,把這些內容看作是第二等的意思。他們把該做的事都簡單省略化了,言談舉止也變得肆無忌憚,更嚴重的是把禮教都給破壞殆盡,卻還自以為得到了聖門中最上乘的旨趣。天啊!這太過份了吧。自作主張隨便去走捷徑,而不知道已經陷進佛教的寂滅理論中,可是自己還麻木不仁、全然不覺呢。古代的聖人著書立說,只不過是為學者指出:下學(克己修身的實踐)的功夫,同時也是上達(努力進取達到聖人境界)的機宜,等到人們自己悟到而在現實中有所收穫時,那語言的說教和知識的理解,就相形見絀、望塵莫及了。《大學》的教育,自從孟子以後,差不多上千年沒有得到傳承了。多虧老師對“良知”的發掘、光大,使《大學》的光輝得以在今天重新大放光明,這真是千載難逢的一天。然而學生還沒有往下傳一代,就異說紛呈、錯雜混亂成這個樣子,那麼對於後世又能寄予什麼厚望呢?《大學問》一文,鄒謙之先生曾經附刻於《大學》古本之後,而我把它收錄在老師文集續編的篇首,使學者打開書就能讀到,由此而想到老師的教導是平凡容易而又切合實際的,既然聖人的智慧及出神入化的深刻義理都躍然紙上,那就沒有必要再去追求別的說教了,若是舍師言而求異說的話,不僅徒然迷惑別人,而且也會誤了自己,那是沒有任何利益可言的。
有人向先生請教說:“《大學》一書,過去的儒家學者認為是有關‘大人’的學問。我不揣冒昧地向您請教,大人學問的重點為什麼在於‘明明德’呢?”
陽明先生回答說:“所謂的‘大人’,指的是把天地萬物看成一個整體的那類人。他們把普天之下的人看成是一家人,把全體中國人看作一個人。如果有人按照形體來區分你和我,這類人就是所謂的‘小人’。大人能夠把天地萬物當作一個整體,並不是他們有意去那麼做,而是他們心中的仁德本來就是這樣,這種仁德跟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豈只是大人才會如此呢?就是小人的心也沒有不是這樣的,只是他們自己把自己看作小人罷了。所以當他看到一個小孩兒要掉進井裡時,必會自然而然地升起害怕和同情之心,這就是說他的仁德跟孩子是一體的。孩子還是屬於自己的同類,而當他看到飛禽和走獸發出悲哀的鳴叫或因恐懼而顫抖時,必會產生不忍心聽聞或觀看的心情,這就是說他的仁德跟飛禽和走獸是一體的。飛禽和走獸還是有靈性的動物,而當他看到花草和樹木被踐踏和折斷時,必然會產生憐憫體恤的心情,這就是說他的仁德跟花草樹木是一體的。花草樹木還是有生機的植物,而當他看到磚瓦石板被摔壞或砸碎時,必然會產生惋惜的心情,這就是說他的仁德跟磚瓦石板也是一體的。這就是萬物一體的那種性德,即使在小人的心中,這種性德也是必然存在的。這種性德源於生來就有的天命屬性,它是自然光明而不暗昧的,所以被稱作‘明德’。小人的心已經被分隔而變得狹隘卑陋了,然而他那萬物一體的仁德還能像這樣正常顯露而不是黯然失色,這是因為他的心處於沒有被慾望所驅使、沒有被私利所蒙蔽的時候。待到他的心被慾望所驅使、被私利所蒙蔽、利害產生了衝突、憤怒溢於言表時,他就會損物害人、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自己的親人之間也互相殘害,在這種時候,他那內心本具的萬物一體仁德就徹底消亡了。所以說在沒有私慾障蔽的時候,雖然是小人的心,它那萬物一體的仁德跟大人也是一樣的;一旦有了私慾的障蔽,雖然是大人的心,也會像小人之心那樣被分隔而變得狹隘卑陋。所以說致力於大人學養的人,也只是做去除私慾的障蔽、彰顯光明的德性、恢復那天地萬物一體的本然仁德功夫而已。並不是能夠在本體的外面去增加或減少什麼內容。”
接著又問:“明明德確實很重要,可是為什麼又強調‘親民’呢?”
先生回答說:“明明德(彰顯與生俱來的光明德性),是要倡立天地萬物一體的本體;親民(關懷愛護民眾),是天地萬物一體原則的自然運用。所以明明德必然體現在親愛民眾上,而親民才能彰顯出光明的德性。所以愛我父親的同時,也兼愛及他人的父親,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親,做到這一點后,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實地同我父親、他父親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親成為一體。真實地成為一體后,孝敬父母(孝)的光明德性才開始彰顯出來。愛我的兄弟,也愛別人的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做到這一點后,我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實地同我兄弟、他兄弟以及天下所有人的兄弟成為一體。真實地成為一體后,尊兄愛弟(悌)的光明德性才開始彰顯出來。對於君臣、夫婦、朋友,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是一樣,沒有不去真實地愛他們的,以此來達到我的萬物一體的仁德,然後我的光明德性就沒有不顯明的了,這樣才真正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這就是《大學》所說的使光明的德性在普天之下彰顯出來,也就是《大學》進一步所說的家庭和睦、國家安定和天下太平,也就是《中庸》所說的充分發揮人類和萬物的本性(盡性)。”
問:“既然如此,做到‘止於至善’怎麼又那麼重要呢?”
答:“所謂‘至善’,是明德、親民的終極原則。天命的性質是精純的至善,它那靈明而不暗昧的特質,就是至善的顯現,就是明德的本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良知’。至善的顯現,表現在肯定對的、否定錯的,輕的重的厚的薄的,都能根據當時的感覺而展現出來,它富於變化卻沒有固定的形式,然而也沒有不自然地處於渾然天成的中道之事物,所以它是人的規矩與物的法度的最高形式,其中不容許有些微的設計籌劃、增益減損存在。其中若稍微有一點設計籌劃、增益減損,那只是出於私心的意念和薄弱的智慧,而並不是所說真正意義上的‘至善’。很自然如果不是將慎獨(自己獨處時也非常謹慎,時刻檢點自己的言行)做到精益求精、一以貫之程度的人,那麼什麼人能達到如此地步呢?後來的人因為不知道達到至善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的心,而是用自己摻雜私慾的智慧從外面去揣摩測度,以為天下的事事物物各有它自己的定理,因此掩蓋了評判是非的標準,使心為統帥的簡單道理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人們的私慾泛濫而公正的天理滅亡,明德親民的學養由此在世界上變得無比混亂。在古代就有想使明德昭明於天下的人,然而因為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所以使得自己夾雜私慾的心過於膨脹、拔高,所以最後流於虛妄空寂,而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真實內容無所幫助,佛家和道家兩種流派就是這樣的。古來就有希望親民的人,然而由於他們不知道止於至善,而使自己的私心陷於卑微的瑣事中,因此將精力消耗在玩弄權謀智術上,從而沒有了真誠的仁愛惻隱之心,春秋五伯這些功利之徒就是這樣的。這都是由於不知道止於至善的過失啊。所以止於至善對於明德和親民來說,就像規矩畫方圓一樣,就像尺度量長短一樣,就像權衡稱輕重一樣。所以說方圓如果不止於規矩,就失去了準則;如果長短不止於尺度,丈量就會出錯,如果輕重不止於權衡,重量就不準確。而明明德、親民不止於至善,其基礎就不復存在。所以用止於至善來親民,並使其明德更加光明,這就是所說的大人的學養。”
問:“‘知道要止於至善的道理,然後自己的志向才得以確定;志向確定,然後身心才能安靜;身心安靜,然後才能安於目前的處境;安於目前的處境,然後才能慮事精詳;慮事精詳,然後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這種說法指的又是什麼呢?”
答:“人們只是不知道至善就在我的心中,因而從外面的事物上去尋求;以為事事物物都有自己的定理,從而在事事物物中去尋求至善,所以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變得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個確定的方向。如今既然知道至善就在我的心中,而不用向外面去尋求,這樣意志就有了確定的方向,從而就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弊病了。沒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的困擾,那麼心就不會妄動而能處於安靜。心不妄動而能安靜,那麼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從容不迫、閑暇安適從而安於目前的處境。能夠安於目前的處境,那麼只要有一個念頭產生,只要有對某事的感受出現,它是屬於至善的呢?還是非至善呢?我心中的良知自然會以詳細審視的本能對它進行精細的觀察,因而能夠達到慮事精詳。能夠慮事精詳,那麼他的分辨就沒有不精確的,他的處事就沒有不恰當的,從而至善就能夠得到了。”
問:“物體有根本和末梢,以前的儒家學者把顯明德性當作根本,把使人民滌除污垢永作新人當作末梢,這兩者是從內心修養和外部用功的相互對應的兩個部分。事情有開始和結束,以前的儒家學者把知道止於至善作為開始,把行為達到至善作為結束,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顧、因果相承。像您這種把新民作為親民的說法,是否跟儒家學者有關本末終始的說法有些不一致呢?”
答:“有關事情開始與結束的說法,大致上是這樣的。就是把新民作為親民,而說顯明德性為本,親愛人民為末,這種說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應當將本末分成兩種事物。樹的根干稱為本,樹的枝梢稱為末,它們只是一個物體,因此才稱為本與末。如果說是兩種物體,那麼既然是截然分開的兩種物體,又怎麼能說是相互關聯的本和末呢?使人民自新的意思既然與親愛人民不同,那麼顯明德性的功夫自然與使人民自新為兩件事了。如果明白彰顯光明的德性是為了親愛人民,而親愛人民才能彰顯光明的德性,那麼彰顯德性和親愛人民怎麼能截然分開為兩件事呢?以前儒家學者的說法,是因為不明白明德與親民本來是一件事,反而認為是兩件事,因此雖然知道根本和末梢應當是一體的,卻也不得不把它們區分為兩種事物了。”
問:“從‘古代想使天下人都能發揚自己本具的光明德性的人’,直到‘首先要修正本身的行為’,按照先生您‘明德親民’的說法去貫通,也能得到正確、圓滿的理解。現在我再斗膽請教您,從‘要想修正本身的行為’,直到‘增進自己的知識,在於能夠析物窮理’,在這些修為的用功次第上又該如何具體地下功夫呢?”
答:“此處正是在詳細說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功夫。人們所說的身體、心靈、意念、知覺、事物,就是修身用功的條理之所在,雖然它們各有自己的內涵,而實際上說的只是一種東西。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就是在現實中運用條理的功夫,雖然它們各有自己的名稱,而實際上說的只是一件事情。什麼叫作身心的形體呢?這是指身心起作用的功能而說的。什麼叫作身心的靈明呢?這是指身心能作主宰的作用而說的。什麼叫作修身呢?這裡指的是要為善去惡的行為。我們的身體能自動地去為善去惡嗎?必然是起主宰作用的靈明想為善去惡,然後起具體作用的形體才能夠為善去惡。所以希望修身的人,必須首先要擺正他的心。然而心的本體就是性,性天生來都是善的,因此心的本體本來沒有不正的。那怎麼用得著去作正心的功夫呢?
因為心的本體本來沒有不正的,但是自從有意念產生之後,心中才有了不正的成分,所以凡是希望正心的人,必須在意念產生時去加以校正,若是產生一個善念,就像喜愛美色那樣去真正喜歡它,若是產生一個惡念,就像厭惡極臭的東西那樣去真正討厭它,這樣意念就沒有不誠正的,而心也就可以得正了。然而意念一經發動、產生,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惡的,若不及時明白區分它的善惡,就會將真假對錯混淆起來,這樣的話,雖然想使意念變得真實無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使它變為真實無妄的。所以想使意念變得純正的人,必須在致知上下功夫。
‘致’就是達到的意思,就像常說的‘喪致乎哀’的致字,《易經》中說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達到。所謂的‘致知’,並不是後來的儒家學者所說的擴充知識的意思,而是指的達到我心本具的良知。這種良知,就是孟子說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種知性。這種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學習,它就能做到,因此我們稱它為良知。這是天命賦予的屬性,這是我們心靈的本體,它就是自自然然靈昭明覺的那個主體。凡是有意念產生的時候,我們心中的良知就沒有不知道的。它是善念呢,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它是不善念呢,也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這是誰也無法給予他人的那種性體。
所以說,雖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為,甚至達到無惡不做的地步,但當他見到君子時,也會不自在地掩蓋自己的惡行,並極力地表白自己做的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許他埋沒的特質。今日若想辨別善惡以使意念變得真誠無妄,其關鍵唯在於按照良知的判斷去行事而已。為什麼呢?因為當一個善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喜歡它,甚至反而背道而馳地去遠離它,那麼這就是把善當作惡,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而當一個惡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討厭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那麼這就是把惡當作善,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惡的良知了。像這樣的話,那雖然說心裡知道,但實際上跟不知道是一樣的,那還怎麼能夠使意念變得真實無妄呢?
現在對於良知所知的善意,沒有不真誠地去喜歡的,對於良知所知的惡意,沒有不真誠地去討厭的,這樣由於不欺騙自己的良知,那麼他的意念就可以變得真實無妄了。然而要想正確運用自己的良知,這怎能是影響恍惚而空洞無物的說辭呢?必然是有其實在內容的。所以說要想致知的話,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物’就是事的意思,凡有意念產生時,必然有一件事情,意念所系縛的事情稱作‘物’。‘格’就是正的意思,指的是把不正的校正過來使它變成正的這個意思。校正不正的,就是說要去除惡的意念和言行。變成正的,就是說要發善意、講善言、做善行。這才是格字的內涵。《尚書》中有‘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的說法,格物的‘格’字實際上兼有它們的意思。
良知所知道的善,雖然人們真誠地想去喜歡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去實實在在地踐履善的價值,那麼具體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從而可以說那喜歡善的願望還有不誠懇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惡,雖然人們真誠地想去討厭它,但若不在惡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去剷除惡的表現,那麼具體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從而可以說那討厭惡的願望還有不誠懇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去為善,使善的言行沒有不盡善盡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惡事上,也就是惡意所在的事情上實實在在地去除惡,使惡的言行沒有不被去除乾淨的。在這之後具體的事情就沒有不被校正的成分存在,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內容就沒有虧缺、覆蓋的地方,從而它就得以達到純潔至善的極點了。
此後,我們的心才會愉快坦然,再也沒有其它的遺憾,從而真正做到為人謙虛。然後心中產生的意念才沒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說我們的意念真正誠實無妄了。所以《大學》中說道:“繫於事上的心念端正後,知識自然就能豐富;知識得以豐富,意念也就變得真誠;意念能夠真誠,心情就會保持平正;心情能夠平正,本身的行為就會合乎規範。”雖然修身的功夫和條理有先後次序之分,然而其心行的本體卻是始終如一的,確實沒有先後次序的分別。雖然正心的功夫和條理沒有先後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誠純一,在這一點上是不能有一絲一毫欠缺的。由此可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一學說,闡述了堯舜傳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學說的心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