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1924-1998),是當代法國後現代解構主義哲學的傑出代表。
1950年至1952年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君士坦丁一家中學擔任哲學教師,1955年成為激進團體“社會主義或野蠻”的阿爾及利亞分支的領導成員,並對法國佔領阿爾及利亞持積極批判態度。1958年獲得法國大學與中學教師學銜,1971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利奧塔曾在中學任教10年,在高等教育機構供職20年,在“社會主義或野蠻”及以後的“工人權力”團體從事了12年的理論和實踐工作。其後在巴黎第八大學任教,也曾一度在美國加州大學厄灣分校和亞特蘭大的艾默瑞大學等處任教。
1998年4月20-21日夜間,因患癌症不治而去世。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在這本著作中,利奧塔認為現代科學的特點是排斥或壓抑建立於敘事之上的合法性形式。他對敘事知識的定義得益於人類學對原始社會的描述。在原始社會裡,敘事的功能體現在對特定人群中誰有講話的權力、誰有聽講的義務的明確規定之中。例如,在南美的卡欣納化印第安人中,公共敘事的這種內在規定或“語用學”依據於固定的程式:講故事者在敘事開始時要說出自己的卡欣納化名字,確認自己所屬部落的真實性和應有的講話權力(即他是從另外一名卡欣納化人那裡聽到這個故事的),明確其他人充當聽眾的義務。這是一個自立正當性的 例子。講述故事的特定方式決定了故事講述者是否有權說話。利奧塔認為,這個看似相當軟弱的自立正當性例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他相信“這些敘事所傳達的是一整套構成社會紐帶的語用學規則”。利奧塔強調的另一突出特點是敘事的節奏形式。它通過有規律的韻律或敘事“節拍”,把自然時間的無規律性固定和容納下來。
例子。講述故事的特定方式決定了故事講述者是否有權說話。利奧塔認為,這個看似相當軟弱的自立正當性例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他相信“這些敘事所傳達的是一整套構成社會紐帶的語用學規則”。利奧塔強調的另一突出特點是敘事的節奏形式。它通過有規律的韻律或敘事“節拍”,把自然時間的無規律性固定和容納下來。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利奧塔的結論是:與人們習慣認為的敘事的區別性特徵不同,這樣的敘事在其展開過程中不是將注意力引向時間的推移,而是淡化或中止時間感。看來,利奧塔在此曲解了“敘事”這一術語的意義——他的結論其實僅適合於卡欣納化印第安人這樣的特殊情況,因為他們的儀式性敘事的確是由“冗長而單調的吟誦”構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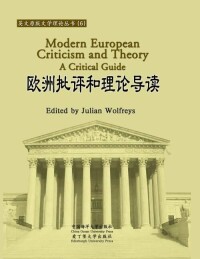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利奧塔認為,自然科學從18世紀以來一直試圖與這樣的正當性抗爭并力圖擺脫它。用他的話說,“科學知識語用學的古典觀念”要求一種迥然不同的授權結構。科學知識構築於指定的、共同認可的真值之上;它和語言與構成社會聯繫的語言使用分離開來。它的主要“語言遊戲”——這是利奧塔從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借用的術語——是指示性的而並非敘事性的。科學語言竭力同敘事的語言遊戲抗衡,認為後者與愚昧、野蠻、偏見、迷信,與意識形態相聯。利奧塔認為,這就是科學必然回歸敘事的要旨所在,因為科學工作最終只有藉助敘事才能獲得權威和目的。科學求助的兩種主要敘事為政治敘事和哲學敘事。其中之一與歐洲啟蒙運動相聯繫,在法國革命的理想中得以體現,是人類從奴隸制度和階級壓迫中逐步解放出來的敘事。
科學作為知識的表述理應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主要作用,因為知識一旦被所有人所掌握,將有助於絕對自由的實現。在黑格爾著作中開始並實現的一種哲學敘事與這種政治“解放敘事”相互交叉,但影響卻廣泛而巨大。所有的局部敘事——無論是某一科學發現的敘事還是某一個人成長、教育的敘事——均以其回應和確證人類解放或純自我意識精神的實現這一宏大敘事的方式來獲得各自的意義。由此利奧塔提出了他所樂意承認的悖論——科學知識在一個層面上構築於對敘事的壓抑和排斥之上,因而註定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依靠一種使之獲得正當性的敘事,一種“元敘事”,或“宏大敘事”。科學知識既無法認識也無法揭示這一點:它是真正的知識,而無需向被其排除在知識範疇之外的敘事性知識求助。沒有敘事這一依靠,科學知識就要預設自己的有效性,就要向自己所詛咒的東西俯首稱臣:迴避問題,依靠偏見行事。然而,科學知識在利用敘事作為其權威性時難道不會落入同一圈套。這個悖論的迷人旋渦在筆者看來是一個幻覺。顯然利奧塔在此所談的是兩類迥然不同的敘事,一類似乎包括抒情詩、吟唱、閑談及儀式化表演,另一類則具有人們常說的敘事的特徵——有因果聯繫的一系列活動依時間展開,並且向結局方向變化。
利奧塔對科學知識所作分析的最重要部分是與他對當代社會狀況的論述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生的事情是,無可挽回地浪費這些宏大敘事的力量,來為科學工作提供正當性的框架。令人感到惱火的是,利奧塔在其所說的元敘事衰落的原因這一點上閃爍其詞。他只是暗示,它與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精神的更新有關,與人們對國家共產主義這一選擇逐漸失去信任有關,與科學領域的方法和技術發展有關,與隨之而來的強調重點從目的向手段的轉移有關。利奧塔所說的“對元敘事的懷疑”給科學造成的影響是科學喪失了與那些元敘事有關的合法性。由於科學在獲得絕對自由和絕對認識的緩慢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它不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和必要的。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這既帶來好的一面又帶來壞的一面。壞的一面是,在這種狀態中看來不存在以正義或善行的名義去調控科學——或者說在那個意義上其他任何東西——的方式。利奧塔無奈地承認,“如今在研究經濟資助人的話語中,惟一可靠的目標就是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或學術機構無法只是傳授知識,而是必須與實效原則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利奧塔所作分析的這一側面使人看到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所預見的可怕前景——不是一個受到理性理想指導的世界,而是一個被絕對的、完全沒有控制的、合理化原則所支配的世界,一個被追求低輸入、高產出的原則所支配的世界。
利奧塔認為實效原則不僅可包容新的能量,而且也可鼓勵非正統的東西突破現存的範式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維結構。利奧塔預測,科學最終將支配一個具有“完美信息”的世界;到那時一切知識在原則上將為每個人所利用,從而不可能將新知識的要求置於發現新事實之上。利奧塔宣稱,在這個假定的“完美信息”條件下,在科學遊戲中採取新步驟的惟一途徑是將那些信息重新排列成不同的、無法預測的方式。正是那些想象的突破展現出動搖或更新科學知識範式的前景。
在當代思想中,利奧塔的論述是崇高意志最具實力的例子之一;它與德勒茲和福柯的著作一道,揭示了從形而上思維的時代性謬見轉向純粹差異的“游牧式”無管制自由的可能性。利奧塔的建議正是以這種無節制的方式被解讀的,其讀者多為從事文學批評或文化分析的人士(而科學家們對此卻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或做出什麼反應)。利奧塔關於科學的論點缺乏對細節的研究,而其讀者又傾向於使他的分析從一個領域——科學知識領域——滑向其他多個領域,這一點確實使人感到相當不安。
利奧塔描繪了一幅科學分解為相對主義的狂亂狀態的圖畫;那裡的惟一目標是愉快地掙脫陳腐範式的束縛,將操作性程序踩在腳下,以便尋找不合邏輯的奇異形式。然而,問題卻並非如此。如果說純科學的某些形式——顯而易見的例子還是數學和理論物理——旨在探索認識現實的不同思維結構,那麼,這在總體上也仍然受到推理、一致性、與可論證真理的對應性等種種模式的約束。否則,為什麼任何一個假設新粒子或新勢能存在的人會不辭辛勞地籌集資金,或深掘地層,或在極地的冰層下進行複雜的實驗,或建造巨大的粒子加速器,以便證實它們的存在。
在利奧塔的論述中,令人更難接受的是從有用而具體的方面——對大學和其他機構中科學知識的管理和傳播的論述——向全球性概括的轉變。利奧塔認為,知識必然脫離集中性元敘事,“分散”開來;傑弗·本寧頓認為,人們可能譴責利奧塔,覺得他使這一論述顯得像自己的元敘事。實際上,利奧塔的模式起到了雙重總括作用:它所依賴的不僅是對元敘事的全面崩潰(無論何時何處)的瞻望,而且還有對元敘事在後現代狀況出現之前的絕對統治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這一點使利奧塔在簡介後現代性的近作《後現代兒童論》中對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哲學和自由經濟理論這樣的概括性敘事大加譴責,認為它們是獨斷專橫的並且必然導致“反人類罪”。
實用主義者所追求的是強有力的、世界主義的非解放的敘事。他認為,從來不存在任何要解放的事物,人的本性從來沒有遭受禁錮。與之相反,人類憑藉不斷擴大、不斷豐富的“對立價值混合物”一點一點地創造了自身的本性。但是,利奧塔似乎不願完全說出在解除合法性的兩種結果之間、在實效與悖理性之間、在操作系統的鞏固與顛覆之間結構對等的含義。利奧塔是這樣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中兩種選擇相互影響的特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市場的重建、當今在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之間所進行的激烈的金融和經濟戰得到各國政府的贊同。它們以控制世界市場為目的,缺乏任何世界主義的觀點。這場競爭的參與者聲稱它們仍致力於實現經濟自由主義或現代凱恩斯主義所制定的目標,可是我們卻難以相信他;顯然,這場競爭非但沒有縮小世界上的貧富懸殊,實際反而使其越加惡化。它沒有打破國家之間的界限,而是利用它們來進行金融和商業投機。[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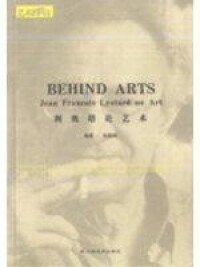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但是,儘管利奧塔描繪了暗淡前景,但似乎還是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分析性補救方法。《後現代狀況》使科學家成為真正的先鋒派“反面英雄”。科學家藉助自己在系統內部開展知識游擊戰的能力,將深奧的、不穩定的運動導入權威語言一遊戲內部。雖然利奧塔的“知識報告”是就科學而言的,但這本書卻堅定地將科學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負面聯繫分離開來,將科學重塑為一種依自身條件而存在的藝術或哲學。正如阿克塞爾·霍內斯和肯尼思·利所指出的,利奧塔最終將處於後現代性影響之下的社會視為實質上是美學的——其組合成分不是權力,而是敘事、語言和性本能結構。這一策略使利奧塔能夠和他的追隨者們一起,對穩定性進行光榮的、形似性悖理的攻擊。於是他的悲嘆學術機構的可怕無效性分析最終不僅給予知識分子在這場鬥爭中的一種中心地位,從而帶來微政治多樣性,而且通過將後現代社會領域轉變為一種美學領域,給人一種對其進行分析性控制的幻覺。
短語、短語群——如規定、勸告、預言和承諾——以及集中、配置和調節這些短語群的更大話語類型——如法律、哲學、經濟或美學話語——受到雙重必然性的制約。首先是“聯繫”的必然性;短語必然喚起其他短語,或與它們一致,或與它們相矛盾,或者使它們所強調的發生變動。即使沉默也是一種短語和一種聯繫。聯繫意味著不同話語類型所建立的不同語用世界之間存在著解釋或變化的可能性。與之相反,制約這些短語的第二種必然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爭辯和出現分歧的必然性。從一個短語向另一短語的每一次變化意味著話語世界之間的一次衝突。利奧塔認為,不同的短語、短語群或話語類型之間的每一次明顯的變化或調解實際上都受到無共同性條件的制約。這樣的條件意味著,對名稱世界之間,存在方式之間,或話語類型之間衝突的任何形式化行為實際上都可能使一種話語類型處於對另一種話語類型規則的正當制約之下。當交際雙方之間或他們所用話語類型之間的衝突通過適用於雙方的第三話語類型得以解決,利奧塔建議將它稱為訴訟。在沒有這樣的話語類型的情況下,利奧塔主張“歧異”的存在。但是,利奧塔認為從不存在令人滿意的第三者,須將每一訴訟至多視為話語內部特有的歧異關係的一種偏差或異化。因此,道德和哲學論點的任務不是將歧異的偶爾困難個案與可以解決的訴訟個案分離開來,也不是將歧異導入可以容易處理的訴訟條件。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被譯成英語的主要著作有《現象學》(1954)、《力比多經濟》(1974)、《後現代狀況》(1979)、《爭論》(1983)、《海德格爾與猶太人》(1988)、《旅程》(1988)、《非人道》(1988)和《政治性文字》(1993)等。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是後現代話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同時也是當代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他的哲學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傳統政治思想的選擇,或者說,提供了一種對傳統政治思想的批判,提醒人們在面對總體化時注意差異的根本重要性,也鼓勵人們站在差異一邊行動,而反對普遍標準和價值的不公正運用。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態》中著重探討當代西方發達工業社會裡的知識狀態變化,試圖以語言應用學(Pragmatics)觀念與方法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資本主義變異和危機癥狀,與其他幾種後現代主義理論闡釋不同,利奧塔沒有象丹尼爾·貝爾那樣從社會系統論角度去說明后工業社會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機,也不象哈貝馬斯那樣提出“晚期資本主義合法化危機”齊企圖重建理性的交流活動理論,又抵牾弗萊德里克·詹姆遜將後現代文化生產印合於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整體淪思維——他從語言資質(competance)及其運用規則的差異著手,深人論證作為西方文明維繫網路與認知基礎的原話語(metadiscours)的衰敗消蝕,以及因此產生的“敘事危機”與知識非合法化局面,這種強調知識“不可通約”和開放變動“語言遊戲”的后結構主義觀念,雖然同西方馬克思主義、新保守主義思潮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解釋多有衝突矛盾,畢竟作為重要的一派給這場論爭提供了新的動力與機會。同時,利奧塔的後現代主義哲學話語對於西方文學及其批評理論的影響頗大,受其啟發或刺激的一場關於“藝術表證危機”的討論。
雖然利奧塔的著作在對哲學和社會科學全面美學化的形勢下卻具有一種增添的潛能。在這種形勢下,與功能、決定性和機制等陳舊、刺耳的詞語相比,敘事、比喻和話語這樣的術語現在已經佔據優勢。在人文學科中,人們常感到相反的情況已經出現,但是社會學和哲學術語的使用對批乎語言的明顯入侵是與批評朝向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運動同時進行的。這種語言和概念的交流所產生的跨學科形式常常被視為知識結構所受的後現代的不穩定化。但是這一論點也可反過來說。藉助後現代主義爭論所培養的遍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誇學科形式也可被視為旨在把握這一領域的嘗試,以便將其強行歸入理性程序。缺乏取得有效反對的或民主化的一致性的堅定嘗試,形似性悖理和顛覆可被無害地轉入職業和體制鞏固的策略。
[1] 數字中國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N199G41&xpos=55
